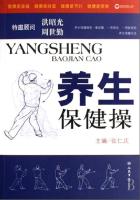皇帝跟段弘拧上了,其结果就是段南歌和秦渊跟着遭殃,皇帝非要秦渊带他跟段弘去天香楼,连御书房里的奏折都不管了,谁劝都没用,而秦渊说要去天香楼就得带上段南歌,不然他不去,段弘自然是不肯应允,四个人在广陵郡王府里僵持好久,闹到最后连苏和都不爱劝了,就百无聊赖地站在一旁看热闹,直到皇帝搬出君主命令,苏和才打着哈欠出去准备车马。
换上一身男装,段南歌却因为先前那一场僵持太久的胡搅蛮缠而没了最开始搅混水时的兴致,撑着下巴懒洋洋地坐在段弘和秦渊中间,不感兴趣地看着天香楼里受人追捧的歌舞。
秦渊也是有些头疼。
方才父皇和国公爷在他那郡王府里吵得好不热闹,可真到了这天香楼里、真把姑娘们请出来了,这两个人却都虎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他们几万两银子似的,瞧瞧,把人家姑娘给吓得舞步都跳错了。
哀叹一声,秦渊也懒得去缓和气氛,身子一歪就没骨头似的靠在了段南歌身上。
先前跟皇帝和段弘歪缠太久,他是真的头疼了。
而碰上这种情况,最慌张的莫过于宛凝。
听下面的人禀报说秦渊来了天香楼,宛凝还觉得诧异,可等见着那阵仗时,宛凝是真的傻了眼,自打接管天香楼以后,大大小小的场面宛凝都是见过的,却已经许多没被吓成这样了。
天宋最英明神武、洁身自好的陛下、和最痴心痴情、寡情淡泊的段国公、由各自的儿女领着来逛青楼,这能不吓人吗?这能不傻眼吗?父子、翁婿结伴逛青楼的事情常见,可这父女、未婚夫妻一同逛青楼的景象她还当真是没见过,她更是没见过哪个女人是笑意盈盈地陪着男人逛青楼的。
不管心里存了多少好奇和疑惑,宛凝都不能问,只照秦渊的吩咐将天香楼里最好的姑娘和最好的茶杯备齐,一股脑儿地送去了天香楼里最好的厢房,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厢房里的气氛却怎么都不像是青楼里该有的气氛,偏坐在这厢房里的两尊大佛是谁都惹不起的,宛凝不管随便开口,可不开口这气氛又太不像样子,宛凝频频使眼色向秦渊求助,秦渊却只软趴趴地靠在段南歌身上,没了半条命的模样。
最后还是段南歌可怜那些尴尬得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摆的舞伎,开口解了围。
“留几个乐伶在这儿,其余人都退下吧,有劳宛凝姑娘把这酒也换了,梅花酒就好。”
不知道是不是见着了国公爷,秦渊一说端好酒来,宛凝姑娘就让人端了一水儿的烈酒,这酒她跟国公爷喝着是没事儿,秦渊喝个醉也没事儿,可陛下待会儿还要回宫批阅奏折,哪能喝这么烈的酒?
一听段南歌这话,宛凝应了一声就连忙安排,而段弘一听到“梅花酒”这三个字,顿时就不满地看向段南歌。
“这酒就挺好,换了梅花酒还不如端白水上来。”
瞟一眼段弘,段南歌柔声细语道:“宛凝姑娘记得给国公爷端一壶白水上来,国公爷今儿想喝清淡的。”
把眼睛一瞪,段弘却是没说什么,兴许是瞧见了段南歌的那副神色而没敢说什么。
待姑娘们一走,皇帝和段弘同时松了一口气,一直端坐着的身板也略略放松了一些,而察觉到对方与自己状态相同时,两个人又互相瞪了一眼,惹得秦渊和段南歌齐齐翻了个白眼。
有这么重要的人在这里,宛凝这个天香楼的主事自是不敢离开,见乐伶们一听到段国公的名号就频频弹错,宛凝只得亲身上阵。
耳边的乐声一变,段南歌不由转头看向宛凝。
“不愧是天香楼的头牌,宛凝姑娘这琴音袅袅靡靡、缠缠绵绵,却又清清净净、不染尘俗,妙极!”
眼神一闪,宛凝柔声道:“段大小姐谬赞,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只是素闻段大小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却不知段大小姐也懂音律。”
瞥了秦渊一眼,段南歌浅笑道:“算不得懂,只不过身边多了一位高人,受了些熏陶,让宛凝姑娘见笑了。”
高人?秦渊挑眉。说他吗?
宛凝会意,垂眼道:“郡王的确精于音律,这样说来郡王和段大小姐倒是互补长短,天生一对。”
眉眼一亮,秦渊颇有些得意地睨着段南歌:“这话说得爷爱听,赏!”
段南歌白了秦渊一眼。
瞥一眼段弘不怎么好看的脸色,皇帝也笑着说道:“嗯,这话朕也爱听,确实该赏。”
端起酒杯猛灌一口,段弘懒得理会这对父子。
突然有人敲响了厢房的门,惹得宛凝蹙眉。
她方才送姑娘们出门的时候已经嘱咐过不许任何人再接近这里,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连她的话都不听了?
而秦渊只当是宛凝忘了嘱咐,有些不满地斜了宛凝一眼。
敲门声止,娇柔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奴婢温月,听说郡王来了,特来给郡王请安。”
指名是来见秦渊的?
段南歌、段弘和皇帝齐齐看向秦渊,而秦渊整个人僵住,突然生出一种跳窗逃走的冲动。
宛凝的手也是一抖,赶忙起身快步向门口走去:“是奴婢忘了吩咐她们不得随意打扰几位贵人,奴婢这就去让她离开。”
“站住!”段弘低喝一声,又看一眼急忙露出谄媚笑容的秦渊,沉声道,“让她进来。”
宛凝恨恨地咬牙,壮着胆子说道:“启禀国公爷,门外来的是个舞伎,段大小姐方才不是说不想看舞吗?”
“让她进来,”段弘只铿锵有力地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别让我说第三遍。”
武将宛凝见过不少,可不管是在战场上多英勇的武将,到了这天香楼里都是一副轻挑嬉笑的模样,宛凝哪里听过这样肃杀的声音?
被吓得心脏砰砰直跳,宛凝不敢违背段弘的意思,只得前去开门。
宛凝刚要推开门,段弘又补了一句:“不准多话,不然……”
“奴婢不敢!”
秦渊扭身趴在了地上,绝望地将脸整个埋了起来。
完蛋了!若这里只有南歌,他倒是不怕,他的事情南歌都是知道的,可偏偏国公爷在……天要亡他啊!
段南歌心觉好笑,安慰似的摸了摸秦渊的头。
他可真倒霉。
秦渊一把抓住了段南歌的手,将段南歌的手垫在了脑门下面。
拉开厢房的门,宛凝背对着段弘,一个劲儿地给温月使眼色,说话时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思:“你怎么来了?郡王今日不想看舞,其他人没与你说吗?”
宛凝一边说一边忐忑。
这应该不算是多话吧?
可温月哪管这些:“姑娘,奴婢只是听说郡王来了,就想着来给郡王请个安,郡王许久没来,理应问候一声。”
说着,温月就一步跨过宛凝,踏进了厢房,眉开眼笑地望向秦渊:“郡王,您来了怎么也让人去与奴婢说一声?若不是奴婢的耳朵灵,今日可见不着郡王了。”
话音未落,温月已经花蝴蝶似的扑到了秦渊旁边:“郡王您怎么趴在这儿呢?不舒服吗?”
温月是天香楼里的寻常舞伎,因为家境贫寒,所以被父母给卖了进来,才来一年,还在宛凝和秦渊的考察期内,未被收做廖氏属下,因而只知道这天香楼是青楼,却并不知道这天香楼与广陵郡王、与廖五爷之间的关系。
秦渊先前是天香楼的常客,又听宛凝说这温月聪慧,说不定可以收为己用,于是每次来时都会喊温月作陪,也会跟温月多说几句话,岂料这温月不知内情会错了意,竟还生出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对秦渊也越发殷勤。
温月本是在待客,出门帮客人拿东西的时候就听见其他舞伎说秦渊带了奇怪的客人来,温月的心里顿时就是一咯噔,怕秦渊是把她给忘了,温月立刻就跑来了,连自己的客人和天香楼的规矩都顾不上了。
此时温月一脸担忧地跪坐在秦渊身旁,当注意到秦渊的手里还抓着一只手时,温月不由地就顺着那条胳膊看向段南歌,仔细打量着段南歌的那张脸。
被人盯着打量了,段南歌的眼神一闪,扬起嘴角浅笑着问道:“你叫温月?”
“是,”温月柔声答道,“奴婢温月,见过公子。奴婢瞧公子眼生,今儿是第一次来吗?”
眉眼一动,段南歌点头:“嗯,的确是第一次来。姑娘跟郡王很熟?”
这话说完,段南歌就觉得自己的手被人狠狠捏了一下。想抽回手,却没能成功。
“是啊,”温月展颜一笑,又转眼看向装死的秦渊,眉眼间尽是情谊,“以前郡王每次来都会要奴婢作陪,郡王最是喜欢奴婢的舞姿了。”
“每次来都会要你作陪?那姑娘岂不是天天都陪在郡王身边?”段南歌这话问完,手就又被捏了一下。
脸颊一红,温月娇羞地点头:“公子这样说……也对。”
“郡王可真是好福气啊!”重重地冷哼一声,段弘咬牙切齿地瞪着秦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