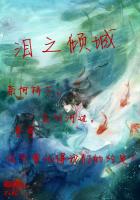赵汝愚长叹一声,从小几上拿起了圣谕,薄薄的一张麻黄纸,在他手中竟似有千钧之重。
李仲飞急不可耐,乍着两手道:“相爷,在下所言句句属实,还请相爷为在下释惑。”
“老夫相信你毫不知情。”赵汝愚叹道,“唉,这封圣谕本由老夫私自截留,想托小友从中斡旋,使圣上回心转意,谁知今日早朝散后,竟被沈继祖送去了元晦兄府上。木已成舟,元晦兄只得遵从圣意,辞官归乡了。”
“什么?竟有此事!”李仲飞脸色大变,失声叫道,“可韩大人与在下说他已劝过圣上,圣上也已收回成命,对先生犯颜进谏之过不予追究了啊!”
赵汝愚双眉紧缩,一字一顿地问道:“韩侂胄,他真这么说的?”
李仲飞想了想,垂头丧气道:“没有,确实没有,这些话只是在下自己认为的。”
“那他是如何向小友解释的?”赵汝愚坐直了身子,眼中闪过一丝玩味。
李仲飞垂首道:“在下问起结果时,韩大人只是笑了笑,很开心的样子,在下以为事情办成,他才如此高兴。”
“韩侂胄并没有作假,在他看来,确是事情办成了。”赵汝愚苦笑道,“此事因他而起,罢黜元晦兄乃他本意,被老夫私自截留的圣谕又重回他的手中,并没有横生枝节,若小友是他,能不开心么?”
李仲飞一愣,勃然怒道:“他竟敢骗我?我这便去找他理论!”说罢就要起身。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朱熹突然叹道:“仲飞,无用的,为除掉老夫,韩侂胄蓄谋已久,断不会因你更改初衷。他刻意相瞒,又费尽心机从你那里骗去圣谕,只不过不想与你公然翻脸罢了。”
“他不想与学生翻脸,学生倒想撕破他那张丑陋的嘴脸!”李仲飞气急败坏,哪里再听的进一句话,当即打马返回京城去找韩侂胄兴师问罪,连朱熹是否即刻南渡也不管不顾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到韩府时已近黄昏,李仲飞远远看见韩福正站在台阶上左顾右盼,好似等着什么人。他当即飞身跃起,凌空掠至韩福身前道:“你家老爷在吗?”
韩福也不作答,只是笑着做了个请的姿势。
李仲飞冷哼一声,将马鞭甩在韩福怀里,怒气冲冲道:“这马还给你家老爷了!”
看着李仲飞风一般掠进府中,韩福捋须微笑,喃喃道:“老爷果真料事如神啊!”
旁边一个家丁凑过来小声道:“老总管,听说这李将军武功盖世,老爷不会有什么危险吧?要不要小的们……”
“真打起来,你们去了也是白费。”韩福摆手笑道,“放心吧,一切尽在老爷掌握之中。”
李仲飞先去了前厅,没找到韩侂胄便又奔向后堂,但凡来往的丫鬟家丁看见他,无不像遇到瘟神一般远远躲开,唯恐避之不及。李仲飞目不斜视,大踏步冲到后堂廊下,不由分说,抬脚将房门踹了个四分五裂。
韩侂胄果然在此,但让李仲飞意想不到的是,堂中竟然摆好了一桌酒宴,而韩侂胄独自坐在主位上,正笑吟吟地看着他。
香气扑鼻,李仲飞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就想掀了桌子:“好啊,这就准备和你的同党庆祝呢?吃,我他娘的让你们吃!”
手刚碰到桌沿,便听韩侂胄笑道:“听我一言,小友再怒不迟。”
李仲飞一愣,又听韩侂胄不紧不慢道:“小友,你回来的要比韩某预料的快了些,你先坐,还有几道菜未上,都是你爱吃的。韩某俸禄微薄,浪费了可就太可惜啦。”
“你究竟耍什么花样?”李仲飞手上加力,竟硬生生将桌面掰下了一块,怒道,“你以为小爷与你们一丘之貉?沈继祖呢?叫他出来!他帮你逼走先生,定会来此表功吧!”
韩侂胄摇摇头,示意李仲飞坐下:“今晚只有你我二人,也并非什么庆功宴。小友若是还念旧情,不妨先听听韩某的肺腑之言,如有一字不入耳,小友尽管将这满桌酒菜尽数扣于韩某头上。”
李仲飞见桌上果然只摆了两副碗筷,稍作犹豫在下首坐了,撇嘴道:“暂且依你又如何?反正小爷也饿了,就不信你能吐出朵莲花来。”说罢,兀自撕下一只肥腻的鸡腿,塞在嘴里大嚼起来。
“小友,那句应该是舌灿莲花。”韩侂胄起身替李仲飞斟满酒,轻叹道,“老夫子走了?”
李仲飞瞪了他一眼,恨声道:“明知故问!”
见他情绪稍显稳定,韩侂胄招手叫过一个门外守立的家丁,耳语了几句,又冲李仲飞道:“长夜漫漫,枯饮乏味,韩某有一曲目可助酒兴。”
家丁走后不久便进来两个人,在桌旁站了,一齐向韩侂胄行礼。
李仲飞见是两个戏子,厌烦道:“净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你觉得小爷我现在有心情看戏吗?”
“小友勿燥,观之再言。”韩侂胄笑笑,对两个戏子道,“你们可以开始了。”
两个戏子再施一礼,也不用琴瑟伴奏,就在桌旁相向而立,只听一人捻指清唱道:“兄台请了,要知道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料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
另一人摇头晃脑,作吟和道:“兄台所言非虚啊!且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啊……”
李仲飞听不几句,感觉这二人口音奇特,语调滑稽,唱词却似乎有所耳闻。再看二人打扮,峨冠宽袖,白粉涂面,唇下三缕山羊胡子将尾端上翘,一副尖酸之相。
他略作沉吟,不由拍案怒道:“姓韩的,你这是何意?令戏子伶人作鸿儒打扮,偏又丑态毕露,是有意在小爷面前侮辱先生吗!”
杯盘震颤,汤汁四溅,韩侂胄不动声色道:“小友不愧为朱熹学生,不错,这二人所唱正是朱熹词赋,所扮也正是儒生服饰。不过小友可知,他们为何如此?又有何来历?”
李仲飞制止戏子再唱下去,冷冷道:“小爷若识得这二人,早将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岂容他们肆意侮辱先生?”
韩侂胄哈哈大笑,摆手令戏子退下,捋须道:“小友有所不知,这二人乃圣上所赐,为的便是让韩某找机会与小友共赏。”
李仲飞撇撇嘴,冷哼不语,韩侂胄面露讥讽道:“小友不信?嘿嘿……情理之中。圣上素来不喜伶乐,却极爱看这个曲目,尤其近来,更是每日必观,小友可知为何?”
“小爷又不是圣上,怎知圣上所想?”李仲飞心中愤懑,将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韩侂胄故作不察,突然加重了语气,沉声道:“只因在圣上心中,朱熹犹如此样!”
“一派胡言!”李仲飞忿忿道,“先生博学大儒,平生忧国忧民,为大宋殚精竭虑,所讲也皆乃治国良策,圣上英明,必不会如此看待先生!”
他越说越气愤,戟指韩侂胄道:“姓韩的,你还自认是条汉子便明刀明枪的干一场,躲在背后阴人算怎么回事?小爷知你与先生不睦,也无须假借圣上之口如此诋毁先生!”
韩侂胄一摊手道:“朱元晦忧国忧民不假,但所献之策无不迂腐不化、拘泥陈旧,其行与误国误民何异?”
“你还敢说!”李仲飞暴跳如雷,一双铁拳瞬间聚满了内力,“信不信现在小爷就废了你!”
韩侂胄为自己倒满酒,端着酒杯道,“小友,你恨不恨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