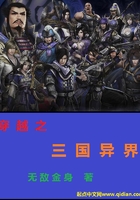“你这副身子,要我这无关的人见了都心怜,你家中人就不知你病到如此,还舍得你入宫为侍吗?”暮西暇替她将裙袖套在手臂关切絮语。
而木苍儿却不放在心上,苦笑道:“你这副身子又好到哪里去?还不是与我一般。”
她周身无力,将腿抬起置于床榻之下,而暮西暇下榻替她穿好鞋袜,“我与你总不同,至少从前我从未感到疲乏,也只是昨夜执勤累了一时而已,你……”说到此处住口,已听她说起她家境难处,再想来她今日所苦挨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了。
她二人都为小小女子,却都不怜自身,相反却为对方思虑许多,如此心性相似,暮西暇更是对这木苍儿心中钦佩。
若是她没有生在这时代,若是她能够与从前的自己一般,靠着苦学便能改变命运,而当此时空是绝无可能,所以只有心中怜她罢了。
至于自身,暮西暇这生来好命,除非这生来痴呆一面不幸之外,她已是太幸福的人。
“唉。”无奈叹了声,暮西暇起身将木苍儿由床榻扶起,一面往外面走去,要她倚着自己的身子慢慢道:“不说了,你我都是身不由己之人。”
她二人互相懂得,又何须多言,暮西暇扶她出了内寝,二人在尚寝局宫廊之内行过,见人人皆是行色匆忙。
也幸得昨夜她二人至东宫当差,不然今日只怕更累。
“你二人往何处去?”一女官正于前方指使宫人做事,见她二人似要出去,便挡在之前问了句。
她眼光于暮西暇二人身上转过,瞧她二人皆是苍白面色,“怎昨日执勤一次,便成这副模样?”
“姑姑,我二人身子不快,想前往太医院去求副药来。”暮西暇俯首谦声道。
见她二人似是真的有疾,那女官瞧了眼也未多言,只道了声,“去罢。”便继续去差使宫侍去了。
暮西暇于木苍儿俯首一拜,而后便出了尚寝局朝太医院而去。
行步在宫廊之间,今日处处冷寂非常,宫中大丧,清早起礼监四处传旨,掖庭宫众人不得喧哗胡乱出行,所以便是如此景况,人人都如过街老鼠一般,只俯首行步。
“你所说那位太医,他会理会你我这小小宫婢?”木苍儿才走几步便微喘起来,与暮西暇轻声问道。
那人是四皇子提起,四皇子所言总不会有假,他说只要提起四皇子那人便会答允。
“四皇子的名号总好用,他何必诓我一小女子。”平声答应。
听她提起四皇子之名,木苍儿愣了一愣,接着问道:“你与四皇子曾有交情?”
而再想来,她出身亲王之家,与皇亲交往也是自然的吧。
“我只是与他几面之缘,不过因家中关联而已,你不要多想,我此时不过宫中一小小女侍。”暮西暇小心打量木苍儿神情。
她极是怕因了这暮西暇的显赫出身再与木苍儿她之间生分,那是傻女暮西暇的生来好运,却并非当下她的。
“我知道了。”木苍儿虚弱一笑,而后她两人不再多言,渐渐的便行至太医院之前了。
她两人立于太医院门檐之下,仰头看去,这处地方可比起宫中其他各处要简陋许多。
想来这宫中,除非锦衣侍卫,与太医院众人之外,便再无其他男子,而男子所持职位,竟也如此低微。
在唐宫当中唯有皇家子弟才可享有显赫,算来这宫婢与太医,也皆是殿下之奴罢了。
“你我便如此进去?只怕不妥。”木苍儿怯生生问话。
而暮西暇却未思虑这许多,淡淡道:“不然如何呢?你我求问太医,又无人传话。”
“可我不敢擅闯。”木苍儿立住静静一笑。
她可真是谨慎心思,而暮西暇却管不了这许多,她浅浅笑着,才要开口拉木苍儿与她进门,只见她脚下踉跄几步,忙扶住她身子,“好了。”扶她至一旁一株梧桐树之下靠坐下来,“苍儿小姐体力不支,那还是我一人前去问个究竟好了。”
与她一笑,将她衣襟拉紧,“你便好生等我,去去就来。”而后便起身直入太医院殿门而去。
她才行至殿前,便嗅到浓重草药味道,这古医所用药剂,与她专业相差甚远,而她所提炼药剂便是草本木本当中那单一精华。
古医治疗见效甚慢,这大概也与药物纯度有关,暮西暇并不十分通晓古医,只在王府之中,闲来无事翻过几本医书罢了,而古人用词也是晦涩难懂,她至今日对许多医道更是一知半解。
正凝神想着,这殿外空无一人,想来此时御医人人正于殿中做事,果真贸然闯入不妥。
就在此时一位御医手提药箱自殿中走出,暮西暇想上前与他一问,慢慢行步至他面前。
欠身见礼,“见过御医。”
那御医打量暮西暇上下,冷声问道:“你是何人,宫中大限,不准宫人私自出行。”
听他所言,暮西暇只得老实垂头,好声道:“太医莫怪,奴婢姐妹患病,所以前来太医院求药。”
这宫中内监侍婢众多,太医院从来只为皇家当差,甚少理会下下人等。
这太医冷哼一声,轻佻打量暮西暇她容貌,“偏生得好相貌,只是太医院太医为皇亲当差,只怕无人为你姐妹诊治,快些回去吧,免得被人撞见,要受责罚,本太医忙着,惠贵妃身子不快,正要前去应差。”说完他将木药箱带在肩头提了一提,拂袖自暮西暇身侧朝前走去。
独留暮西暇愣在原地,眼瞧他看去,这不过也就是一位衣冠禽兽之辈,谅他医道也不会高出几何,此等人在自身看来根本不配为医。
“太医可否告知京燕太医何在?”暮西暇眼朝着他大喊了声。
那人听得这句止步,转过头来怔怔望向她,默了一阵才应,“你怎知这人?”
“四皇子告之,小女暮西暇。”她婷婷而立,语调平平说道。
若非不提暮西暇三字,这位御医只怕不肯为这小小宫婢留情,如此想来,一女子空有美貌,也未见得会要世上人人谦让,果真傻女之前在加雍亲王之女才有些用处。
御医听得暮西暇三字,脸色这才缓和,而后慢慢走至她身前,带有愧意赔笑道:“在下有眼无珠,原来是暮大小姐。”
雍亲王家受难,两女双双入宫为侍,此事于这宫闱之间更是人尽皆知。
“御医大人言重,小女前来正是为寻京燕太医而来,还请大人告之。”俯首应道。
而京燕入太医院,是因四皇子之故,所以太医院众人待京燕这人更是礼敬三分。
那御医俯首应道:“想必暮大小姐是受四皇子指示而来,京燕他此时并不在太医院正殿。”
他抬眼望向暮西暇,而后再是垂首道:“京燕入太医院,只为研习医道,他在正殿之外,那处偏殿之中,日常制药起居皆在那里,暮大小姐可前往那处一见。”
当真奇事,入宫为官,竟还有不当正职,偏偏研习医道之人,而想来那位京燕太医当真奇人吧。
听他所言一笑,暮西暇欠身道谢,“多谢御医大人。”而后回首朝那远处一座正浅浅升起炊烟偏殿望去。
“小人受惠贵妃所命,实在有事,便先离去。”
暮西暇听得他说这一句,而眼朝向那偏殿,慢慢移开步子朝向那边走去。
殿门紧紧合着,而窗纸也是不透光的磨砂材质,暮西暇想见见其中景况,便含住手指,而后轻轻将窗纸点破。
闭起一只眼睛朝里看去,这当中摆放许多草药,“荨麻草,佛耳草,辛夷花……”
因为在王府当中通读医术,在书籍之上曾见草药形态,所以她在那窗纸缝洞之中见那草药便随着叫出名来。
她正看得仔细,忽而眼前黑了下去,正奇怪是怎么回事,殿门突然打开。
暮西暇她愣住,身子仍是稍稍前倾动作,见面前那人一身太医院官服,而官帽未戴,由长布束发。
他眉目冷峻,薄唇鹰钩鼻,见此面貌便是一刁钻之人。
莫非他便是京燕?
暮西暇才要开口问询,那人先是冷冷出了一声,“你是何人?”
“请问可是京燕太医?”暮西暇歪过头狐疑打量他周身。
此人模样可与想象当中相差甚多,他这一身掩不住的桀骜之气,可与宫中御医相差甚远。
“我只问你是何人?为何在此偷窥。”那男子剑眉横起,露出不悦之色。
暮西暇听他话中似有不快之感,稍稍低下头去,轻声道:“叨扰大人,小女是听闻四皇子所言,所以前来求医,还望大人从医心肠为小女一看。”
在这男子面前,暮西暇便不敢抬头,到底是自身理亏在先,擅闯他人领地。
而这偏殿听方才那人说来是他居所,而这当中只简陋一木床而已,其他便尽是草药,这人听闻四皇子所言,乃是用毒高人,他也可称作医痴吧,竟与这满殿草木同住。
暮西暇她脑子当中胡思乱想,垂头看脚下布鞋子之上染满污泥。
自昨日这鞋子之上便弄成这满是污垢,也来不及清洗干净。
而那人听闻暮西暇提及四皇子,这才问话,“你与四皇子何干?”
见他开口说话,暮西暇仰起头来说道:“小女……暮西暇,四皇子曾许诺为小女请来良医。”
她这样一说京燕便知道了,前些日子的确四皇子与他说过,雍亲王家大小姐病似有好转之兆,想请他前去再做诊治,只不过近日来多生变故,而他自身又不愿在大唐久留,所以与四皇子辞行,而四皇子又不舍奇才,便将他举荐太医院。
“暮大小姐。”京燕他双手交合在小腹之前,微微点头叫了声。
暮西暇展开笑颜歪头笑道:“正是,还望大人为小女诊治。”
她已入宫中,仿佛来此游玩一般,京燕也本身为洒脱之人,不喜与那攀龙附凤之人相交,但今日一见这位暮大小姐,她出身皇族却性情极有洒脱只感,便有心相识。
“那么,请暮大小姐进来一坐。”京燕让开身子,展开一臂请她进门。
暮西暇一笑相应,才抬起步子而后又放下了,险些忘了,她并非是那病入膏肓之人,明明是带木苍儿前来求医。
一时之间竟忘了提,便忙于京燕说道:“今日并非小女求医,而是小女姐妹木苍儿,还望京燕大人为她一看。”
京燕本是冷傲之人,一心只有医道,听她方才所言有些迟疑,怔住片刻。
见他似乎不愿,暮西暇连忙再道:“贫苦人家,积劳成疾,她比起我可是病得严重太多,你我都为从医之人,便发发善心吧。”
她还未发觉此言不妥,她为雍亲王嫡长女,又怎是从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