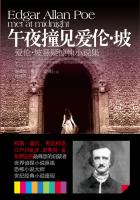7月3日
柔和的阳光照射在我的眼皮上。视野泛着温暖的红色。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反正睡得特别舒服。
随后,一阵昏天黑地的剧烈震荡把我的五脏六腑都要晃出来了,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生生拽下了床。
“车厘子!起来!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
我整个人差点儿没呕吐起来:“贝拉!你神经病啊!”
伊莎贝拉不由分说,直接拽着我的头发就往电脑前按,我随便扫了一眼屏幕,随后马上给了自己一拳。
我终于清醒了过来,这是真的,我连着收到了12份面试offer,18份面试通知。
影视公司、杂志、网媒、图书公司、产业调查公司,之后还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统统去掉,靠谱的这些横竖离不开文化圈。显然我的人比我的房子要走俏得多,大概是因为价格比较低。这也大概要归功于C集团出来的人工作就是好找,虽然我只在C集团待了区区一年就被扫地出门。
我忽然开始怀疑,什么时候我从苦苦找工作的人,变成了自己挑工作的牛掰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嘿,”伊莎贝拉贱兮兮地把她漂亮的头颅靠在我的键盘边上,眼神在我脸上清拢慢捻抹复挑了一圈儿,看得我这个女人都酥了,“在外人眼里,你还挺人模狗样的?”
“实力,”我努力保持着严肃,绷着脸上下滑滚轮,“实力你知道吗?”
她捅了我一下,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准备准备吧,别像当初进S集团那样。”
“S集团没法准备……”
“我问你,你是再也不想去S集团试试吗?”
“想是想,但是我一直没搞清楚,到底哪儿不对。”
你看,两个人之间总有这种别人不会懂,互相之间又不好提的事情。伊莎贝拉愣了一会儿,决心转移话题:“你打算先去哪家?”
“这么多简历,你说我先去哪家啊?这感觉,爽!皇上翻绿头牌子一样。”
“怎么着,你还打算选一家品貌端庄、端撵合德的淑女公司啊。等等——”
她突然按住了我的手。
“地产公司?什么玩意儿。我是个编辑。”
“不对,下面,下面那个——”
招聘网络新闻编辑:中国家电网。
7月9日
决定要去面试了,可是我没有面试的衣服。
用来面试的衣服都是春冬装。我曾经大放厥词,说7月来找工作的都是顶风作案的傻子,现在呢,我就是那个傻子。
好歹从那一柜子奇葩的衣服里挑出了一件中世纪复古风的小裙儿,虽然没什么大错儿,可是怎么看怎么随便——罢了,只剩下几十块钱的人没权利说这个。
面试准备什么的倒是用不着,早在进入C集团之前,我就对各种企业面试了如指掌,长驱直入。不论是300号人竞争的职位,还是硕士博士排队候着的职位,我从未失败过。
为此我曾经回母校给孩子们上过课。
其实方法特别简单,就是看面试攻略咯。看完之后,如果你全盘照搬,你就输定了。你要明白,所有人都在看那玩意儿,你照着做了,保证会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毫无生机。除非你真的是在面试特工之类的职业,要不然,亲爱的,看完攻略以后,掩卷沉思一下,怎么才能在攻略里说的这一片标准的人里,做出一些能让面试官记住的事。
面试和工作不一样,面试和竞标差不多是某种形式的闯关大冒险,在面试的世界里,特点比全面更有优势。
创新型公司,你穿得争奇斗艳一点儿没关系,大花臂也有人爱,哪怕你是异装癖或者嘴上有环,呵呵,也许那家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德行。
传统产业着装要相对低调。如果你面试的还是传统产业里的创新事业部,稍微活泼一点就可以了,专业之外,多聊聊奇怪新鲜的东西。那些面试官终年见的都是螺丝钉,一板一眼的,可以自行想象一下,面试了七八年,所有的面试者看上去都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你能给他一点生机盎然的感觉,他一定会有抱着你哭的冲动。
如果你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说真的,稳定的工作其实竞争压力反而是最大的,因为人人能做的事情,想去做的人一定是最多的。
这方面一直是我知识的一个空白区,因为我真的从来没面试过事务性工作……非要说的话,这样的工作,你不妨表达得诚实一些,不要有任何虚头巴脑的东西。毕竟当一份工作人人都能做的时候,最重要的考察点,就成了这个人是不是老实憨厚、易于管理。要点是打从最开始就适当地诚实拒绝某些事物,毕竟你是工作,而不是随叫随到的便利贴孩子,对不对?
对于面试,我论述了617个字,但这个足够解决面试中80%的问题了。凭借这点儿小聪明,我收到了三家跨国公司的offer,最终选择了竞争最激烈的C集团。去了以后我没怎么竞争,依然是秉承着“大家都抢的项目我就靠边站了,哪儿人少我去哪儿”的原则,成功规避一切头破血流。我是个懒人,没什么学历,能力这种东西,在北京永远是天外有天的事情。我有的只是我的一点小鸡贼和小善良。
但是最后,我留下了。
这为我轰轰烈烈的职场第一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从面试到工作满一年,失败率为零,我像斯巴达壮士一样战无不胜。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失败几次就好了。
国家电网的面试如期而至,我依然还是运筹帷幄。
大厦很是辉煌,我走在里面也略微有点儿小紧张,耳畔幻听起各种辉煌音乐,原来我可以得到这种机会,居然是国家电网,竟然是国家电网。
见了前台的妹子都要笑一笑,以表客气,我暗地狠狠攥紧拳头,告诉自己切莫激动焦躁。
前台妹子煞有介事地叫我填表,我是否入党,父母是否入党,爷爷奶奶是否入党;有没有编辑证,有没有文秘证,有没有四六级证;有没有北京户口——户口当然是没有,于是考官很不屑地瞥了我一眼。
她是个中年女人,我一直疑心她没有戴胸罩,白色的衣服罩在她肥腻的身上,却不知为什么显得松垮,她动上一动,我差点儿以为自己看到了拉奥孔。
她眯起眼睛看看我,用江苏味的普通话问:“离家这么远,你为什么来北京?”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其实从未想来北京,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梦想。那时候,我只知道C集团厉害,C集团要我,C集团在北京,以及年轻就该去外面走走。
我看着她,沉默了三秒钟,脑子里想的却是老甄。
我来的那天,老甄说:“你有梦想吗,我想帮助一些孩子实现梦想,你来吧。”
我说:“没梦想,我现在想的是能有个地方住,晚上吃好吃的。”
老甄笑了,说:“没有梦想人生会很无聊,你留在北京,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梦想。”
听起来还挺好玩的,于是我就留下了。
“你好!”中年女人强行把我拉回了现实。
“哦,我一直向往北京,毕竟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在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并且有结构立体化、资源国际化的趋势。在C集团的工作过程中,我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点。”
中年女人努力点头,似懂非懂,还有点儿溜号。
我看了看她,知道该收线了,就笑眯眯地看了看她:“而且北京的女人都比较优雅嘛。”
中年女人果然笑了,晃了晃她下垂的胸:“那来谈谈对副主编这个职位的见解吧。”
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表述了五分钟,她却一直在摇头。
“我需要的人,要有总监的智慧、市场经理的敏锐、行政经理的沟通力和主编的细致,能力很重要。虽然这个部门刚刚成立,只有你副主编一个人,但是你是直接听命于老板的啊,就相当于是老板的助理啦,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我忍了很久,才重新摆出一个微笑:“嗯,挺好的。”
……她又说了一下我未来的前途有多么光明,如何如何看好我。这种话,听多了,就像寒暄。不过礼尚往来还是要有的,我夸了她几句,尽早聊回正事。
“咱们中国家电网是央企哈,是不是我的档案……”
“我们是民营。”中年女人笃定地说。
“哦?”
“我们这个中国家电网呢,虽然是属于民营,但是在家电界是很有名的,作为中国电商前一百强,我们卖的家电都是质优价廉,我们未来和一些大企业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嘛!”
哦,中国,家电,网。敢情是我断句断错了。
我礼貌地笑笑,心平气和地听她说我应聘的岗位工资是2500元,点头,告诉她我考虑考虑。
出了门我就狂笑成狗。一个电话拨给伊莎贝拉,尽情吐槽。
“中国,家电,网?”伊莎贝拉在电话那头笑得不行,“这语文是鲁迅爷爷教的吧,人家那文字功底,你差远了。”
“虽然我没有文字功底,但是我有总监的智慧、市场经理的敏锐、行政经理的沟通力和主编的细致啊。”我们两个女人隔着电话尖酸刻薄起来。如果刚才的中年女子听到了我们的你来我往,必定会羞愤得胸罩尽断。
“人生阅历,绝对是人生阅历,”贝拉笑得都哽咽了,“以后你就给你孙子讲,你奶奶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奇女子。”
我对着人潮汹涌的大街,迎风笑成了一个傻子。末了伊莎贝拉突然说了一句:“你那个小白,今天说出差回来了,还装得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要和我们合租,被我给撵出去了。”
“贝拉,你别不让啊,小白除了我这里没去处!我回去跟你说!”
“车厘子,你要是哪天死了,绝对是死在你的这颗精纯琉璃莲花玻璃豆腐心上。”贝拉压低了声音,叹了口气。
7月10日
我是被一通电话铃声吵醒的。
第一缕阳光伴着电话铃声的聒噪,照射在我一片狼藉的卧室里。我踩着仅有的一只拖鞋,一蹦一跳地跳过枕头和沙发垫,跳过一地鸡毛和杯盘狼藉的桌子,跳过头发乱七八糟、眼角带着泪痕、酣睡不止的伊莎贝拉。
我的手捞到电话的前一刻,好像踩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软软的,还会呼吸。我吓得浑身一紧,跳了起来,把拖鞋甩得飞了出去。
紧接着我发现我踩到的是李昼,他和衣而卧,蜷缩得像个婴儿,睡得很安静,下一瞬间拖鞋好像被甩到了李昼脸上。他微微睁开眼睛,我第一次发现,李昼的瞳孔颜色浅得可怕,他淡淡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又睡了过去,瞳孔泛着淡淡的阳光。
是MR.C。
消失了多日之后,他又出现了。
“喂。你好,车厘子。第一轮的测试结果出来了,根据几天的观察,你的表现为不合格。”
“观察?可是你一直都没在啊!”我彻底清醒了。
“我们现在加一条规则吧,你去找满七个人,填满这个房间,既然是合租,他们不能够免费,给你五天时间,看你的能耐,如果做不到,那么很遗憾,我们的测试可能需要提前结束了。”
“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该怎么,怎么——”
电话那边只剩下一串忙音。
我挂掉电话,李昼再次睁开浅黄色的眼睛,瞥着我。
伊莎贝拉翻了个身,又一次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我……我去买早餐,一会儿准备今天的面试。”我尴尬地笑了。
“房子出什么问题了?”李昼问。
伊莎贝拉呻吟了一声,也趴了起来,挠挠乱七八糟的卷发。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昨天晚上的记忆渐次恢复。
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起了小白。
伊莎贝拉不许小白来,车厘子偏让小白来。
我们就此展开了友好的会谈,并且成功地导致了身上多处瘀青,伊莎贝拉的嘶吼吓得普通青年一整夜都没打LOL,文艺青年去酒吧待了整夜。本想下班之后来喝一杯的李昼,就这么被文艺青年劝来了乌托邦公寓,成了我和伊莎贝拉世界大战的第二位受害者。
我不明白伊莎贝拉为什么那么剑拔弩张地讨厌小白。
这一次李昼却平静得很,他告诉我说,我走之后,小白成了创新事业部的新经理。
然后我们的争吵突然告一段落了。
我无力地解释,我走了,创新事业部总还是需要经理的,不是小白也会是别人。
然后我突然发现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我们就这么闹腾了一夜,然后把房间弄成了这副德行。
“还行,还行,”伊莎贝拉干笑,“总比早晨起来的时候,李昼躺在我的床上要强。或者更糟,车厘子躺在我的床上。”
她揉了揉乱七八糟的卷发,打着哈欠进了厨房。紧接着,一声冲破云霄的尖叫从厨房中传来。
你猜怎么着。
早餐早就已经做好了,满当当的五人份,煎蛋、果汁、面包,文艺青年的那份还是解酒的绿豆汤。
普通青年戴着眼镜,对我们笑呵呵地说:“你们吵得那么激烈,一定没好好吃饭吧,吃吧。”
“你简直是座敷童子啊普青大叔……”伊莎贝拉慢慢抬起手,合上了自己的下巴。
“快吃吧,”普青大叔胡子拉碴地笑了,“还有,我不是大叔,我只比你们大一岁,和文青以前是一个宿舍的。”
“哦。”我们异口同声,面无表情地回答。
一顿饭吃得很安静。
“我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儿了,”今天的普通青年格外宽容温和,“我在这里住了三年多,你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两次。一定是说你自身存在的问题挺大的,才会这样。上次发生这件事是两年前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我吃了口煎蛋。
“搬走了,最后他饿得受不了,无处安身,回老家挖煤去了。厘子,怎么不吃了?”
伊莎贝拉一言不发,直接跷起了腿,点着了烟。
“别急,你让我想想。”李昼说。
早晨的蛋黄太噎人,我都快哭了。
“你别怕,车厘子,”普通青年突然站了起来,显得有点儿激动,“我们有这么多人呢,我们都能帮你。”
“对啊,傻宝贝儿,你不是有个乌托邦公寓吗,咱们把它提上日程。”伊莎贝拉吸了口烟,吐起一个浑圆的烟圈。
“如果我们弄得足够好,其实反过来可以牵制C先生,和他提出我们的条件。”李昼慢条斯理地嘬了一口豆浆。
“咳咳……”我使劲儿咽了一口荷包蛋,“你们怎么突然都对我这么好?”
一转脸,所有人都去写招租文案了,没人搭理我。
欢迎莅临乌托邦公寓。
乌托邦公寓招合租人,有24小时热水,全天Wi-Fi,虽然有点小贵但是没隔断啊,还有欢迎你的我们,嗨!
半个小时后,普通青年一脸肃穆地把合租的文案交给了我:“怎么样?”
伊莎贝拉直接把烟碾碎在茶几上:“这么写,下辈子也招不来人吧。”
普通青年终于有点儿光辉的脸黯淡了下来:“我去打一局LOL……”
伊莎贝拉和李昼默默对视了一眼。
“我觉得你伤害了他。”李昼说。
“我来!”伊莎贝拉用力挽了一下她并不存在的袖子。
欢迎莅临乌托邦公寓。
嘿,还住地下室呢吗?
生活质量是不是差了点?
来我们这儿吧,乌托邦公寓。
客厅和全息电视,红酒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庞大寂静的城市里,我们还是可以搭伙过日子。
下班以后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做菜吃。
放假了我们可以约友人三两,闲庭赏月,泛舟池上。(后院有游泳池,我刚才发现的。)
难过了我们可以一起喝酒,微醺也好,酩酊也好,金钱和居住是生存,有人懂,才是生活。
“除了泛舟池上有点儿扯以外,别的都挺好的。”我看了看。
“我觉得你写得不够理性,真的。”李昼也交了他的文案,给我看。
欢迎莅临乌托邦公寓
你觉得地下室省钱吗?
你错了。
让我们算一笔账,600元一个月,10平方米,空气混浊。
根据拉格朗日函数……
(此处省略一整页数学公式)。
最终得出结论,来乌托邦公寓的平均价格低于一个地下室。
还看着干吗,打电话,过来租。
我和伊莎贝拉默默无语地看完了。
李昼抱着胳膊,眯起眼睛凑近我们,等着我们夸。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说。
“非常完美,如果爱因斯坦活了过来,他一定会来租的。”伊莎贝拉说。
7月11日
合租启事发出的第二天,我们的手机一片死寂。
第二份工作的面试明天开始,我被MR.C的警告分了心,整个人焦躁无比。伊莎贝拉和李昼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在一遍一遍刷着租房广告,LOL的声音成了固定的BGM,李昼拿着铅笔,在表格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公式,伊莎贝拉戴着耳机看电视,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又哭得梨花带雨,最后我才发现,她看的居然是百老汇的歌剧。这一新的发现让我毛骨悚然,顺带着,心情也好了不少。
虽然情况并没有变好,只能说是变糟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安心得很。
就好像真的有了这座房子我就有了一切,就有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下去的底气。
我自己的定价是主卧2800元,次卧1900元,我自己住最小的房间就行,总还是够的。
然而就在我打开电脑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错了,错得离谱。
一下子世界就变了。
【59同城最新信息发布】天通苑精品豪华主卧,1200元~1900元。
次卧甩租,只要900元!
精装次卧1200元,绝非中介。
天通苑精品主卧,1600元~1900元!紧邻地铁豪华装修房东直租绝非中介!
天通苑精品单间!家电齐备24小时热水!500元,拎包入住!
……
我的报价,远远高于市场价格。早在一天之前,事情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手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盯着自己发布的“主卧2800元”广告,忽然觉得自己是个笑话。
伊莎贝拉看出了我脸色不对,从旁边凑了过来,她只扫了一眼,就拍了一把修长的大腿:“怎么会这样?七月房子不是好租么?怎么一下子跌了这么多?”
我僵硬着手指,在键盘上敲下字。“还记不记得咱们租的时候的房价?不是这样的,怎么租的人多了反倒便宜了?”
伊莎贝拉拍拍我的肩膀,把下巴凑近我:“别急,少安毋躁,想想办法。”
我慢慢冷静下来,一手托着腮,捻得下巴发疼。
李昼把视线从书上挪开,敲了敲我的电脑背壳:“我们忽略了一件事,这和我们着急无关,贝拉。”
“几个意思?”贝拉问。
“是不是这个受众是刚刚毕业、租不起房子的学生,所以打的是价格战?”我问。
“对,就是这个,价格战,”李昼点点头,“可是,价格战只能说明一点,厘子。”
“是我们太天真了,不了解市场。”我在七月的阳光底下打了个寒战。
“不是的,厘子,价格战不是谁都能打的。是有人一下子租了整整一批房子,才能打得起价格战。”李昼说。
“别急。我想想。”伊莎贝拉按住了我的肩膀。
李昼看了一圈网页,迅速得出了结论:“价格调查过了,有隔断的房子是1900元的主卧、1200元的次卧。没有隔断的,不知道为什么,也是这个价格。2100元的主卧已经是最贵的了。”笑够了,残酷的事实横陈在面前,整个页面都调查过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看着页面上的广告一点点绝望,一点点开始发呆。
我看了一会儿豪华三居的大客厅,洁白的沙发、实木地板和豪华的墙灯全被我看了一遍。
真完美,美得跟画儿一样。
哎,等等,怎么这么像画儿啊?
我点击了放大图片,仔细看清楚,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啧啧,我好像漏掉了什么。我叭叭点开了每一张广告。墙灯、雪白沙发、豪华浴室,末了甚至出现了旋转楼梯和立式鱼缸。
这不是3D做的嘛。
叹为观止,终于找到了拿来主义的现实应用。鲁迅爷爷可以瞑目了。
忽而一下子,这几天租房子的种种状况在脑子里旋风一般过了一遍,一瞬间我好像明白过来了。
“李昼,这不是房子的真实价格。”我说。
“我也发现了。”
我忽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了,硬拽着李昼和贝拉说了一遍。
随后我们翻翻页面,挑了个“房东直租绝非中介”的号码拨打过去。
老实说打了这么多电话,我还是略微有点儿认生,每次开口都有点儿抖,虽然已经不那么明显。
“哎,喂你好。”是个男人的声音,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口音。“我租房子,不是中介,我不是中介。哦,你现在就要看房是吧,看什么样的房子?好的好的,1200块的次卧是吧,哎呀,那个刚租出去,现在只剩下最便宜的1400块了啊,也来看看是吧,好,好!可是我现在不在家,叫我哥哥领你去。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嗯,好嘞。”
不多时,“哥哥”来电,告知地点,依言而去,相聚在静水宾馆门前。
一个五短身材、脸色黝黑的矮个子男人站在楼下,一身西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布鞋。他的脸显然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看不出年龄,只能看出两坨高原红。他看见我,马上扯着嗓子开始喊,方圆十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你好啊,来看房子的吧,我是房东啊,我是一个老北京,祖宗三代都在这里!”
他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
“您,您好,您是房东本人吗?”
“我是他哥哥。”他说。
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儿面熟。
哎,这不是那天我在中介公司打仗的时候遇到的人物之一吗。
还没反应过来,我的手机又响了。我还以为是来接应我的李昼,想不到还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你好啊,刚才你不是要租房子吗?我是他哥哥。”
“哦哦——哥哥好。他的另一位哥哥已经在我这里了。”我故意抬高了声音,拿眼睛斜瞟那人。他面无表情地看向苍茫的远方,也把手揣进笔挺的西服兜儿里,小肚腩都挺了出来,微分开腿,露出带着破孔的布鞋。
“他二哥,”我摁掉电话,对着他扬了扬,“还真巧,你们家谁是老大呢?”一边说,我一边若无其事从他身边走过。他原地愣了一会儿,闷着抢先一步走到我前面,给我带路。说得也是,都到这份儿上了,即使我有商业间谍的嫌疑,也总不好直接把我拒了。
“上车吧,姑娘。”他殷勤地做了个邀请的动作,我心下有点儿打怵。但是已经到这儿了,我身为一个先遣部队,还能让李昼和贝拉等着吗。
我收住脚步,双腿并拢,把包挎在肩膀上,微微颔首。之后勇猛地一个翻身跨上了他的电动车。
“我就跟你说,你来找俺们可就对了,你知道不,我们大哥是黑帮老大,整个顺风区十里屯子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还在美国有好几个小老婆……”
“开车。”
不远处,李昼乘坐的出租车也发动了。
“跟紧。”
“让我跟着这个……开得太憋屈了……”
“加钱。”李昼说。
司机兴高采烈地一踩油门。
五分钟以后。
“还没到?不是紧邻地铁吗?”我迎风怒吼,被风灌得饱满得像一面日本的鲤鱼旗。
“俺们家老大年轻的时候,你知道不,在夜总会,那是非常的嚣张的……”这个二货青年还在讲他老板的热血青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
十分钟以后。
“还没到吗?不是——”
“后来啊,那个后妈就死了,那个后儿子啊,就决心跟着俺们老大干,这就是俺们老二啦……”
15分钟以后。
“喂,还没到吗?不是——嗷!你转弯倒是吱一声啊,咳咳。”
“剁了一根手指头,还能打麻将,打得更好了,人称他是六指赌神……”
我所有的要求都被扼杀在萌芽中了,二货青年醉心于他老大的奋斗史,一直兴高采烈地喋喋不休,唾沫星子飞溅。
20分钟以后,我已经开始相信我遇见了人贩子。脑子里开始交错各种凶案现场,惊恐地迎风流泪。
我回头看了好几眼李昼的车,可惜茫茫车流,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此时二货青年猛地刹住了车,我的脑袋撞到了他肉软Q弹的后背,砰的一声。
揉了一会儿,看他摇摇摆摆地继续往前走,我也只能龇牙咧嘴挎着包跟上。嘿,还真是个小心眼儿的,跟着赶着一直上了17楼,一开门,一片黑暗。
这熟悉的场面。整个房子被隔得像迷宫一般。我小心翼翼地扒拉开走廊里晾着的湿漉漉的秋裤和内衣,看他掏出一堆钥匙,哗啦啦地开了门。
一个长方形的“次卧”出现在我面前,墙面斑驳,水管毕露。我回想起3D照片的豪华模样,微微闭起眼睛。
这次卧……我拿指关节敲敲两侧的墙壁,这是我们早就养成的习惯,一进入这样的房子,就开始砰砰敲墙,来判断哪里是房子的真实墙壁。实墙敲起来沉闷有力,隔断敲起来空洞轻松。而实墙所在的位置就是墙本来的结构。这方面我们都是熟练工,只要敲上一敲,就能料定它被改造之前,到底是四室一厅,还是五室一厅。
几秒之后,我的脑子里迅速地形成了一个3D模型,不知为什么模型的客厅里还有白色的沙发。“而这个——是这房子以前的厨房。”
“这么说吧,”我定定神,攥了把汗,却有了点儿底气。我抱住了胳膊,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状况,腿也下意识地交叠起来,“你们这边房子的状况我也看了。咱们对房子价值的判断还是比较一致的。其实我想法也挺单纯,不是靠这个赚钱,只想把我的主卧和次卧租出去。不带隔断的房子吧,我也看了,咱们这一带其实不多,是吧?”
他好像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跟他说话,语无伦次起来:“这这这,我要钱!要钱!”
“乖,给你。今天呢,正好也就咱们俩,不提公司,你帮我把这两间也租一租,怎么样?”
“价钱打算租多少?”他怯生生抬起头,看着我。
我微微扬起下巴,对上他的视线:“你看呢?怎么个价位合适?”
“主卧也就是——1900块吧!俺们都是这个价,这个价!”他伸出三根手指,不明白到底想表达个什么。
我嗤之以鼻:“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找你了。”
他也毫不犹豫地沉默,不过既然打过一次交道,他也明白了总不能跟我大眼瞪小眼瞅到天黑的道理:“你开个价。”
见他一副反正是你消费的表情。横竖只能是开价了:“主卧2800块,次卧2300块。”
“你那是扯。”
“2600块和2200块是底线,在此基础上多100元,给你加100元。”
他啃咬嘴唇,又一次陷入不置可否,我知道我的话已经带到了。
“等你的好消息。”我眉开眼笑,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结果刚到门口,他的话如期而至。
“你总得给我个七八百吧。”
“这就看你租成什么样了呗。”我顿顿脚步,转身走下楼。不料他忽然猛冲出来拦住我的去路,看着我。
我下意识退了半步,他开了口。
“你要是降价就跟我说一声!”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接过来:L股份有限公司天通苑大区经理,王某某。
“OK。”把名片装进钱夹,我让开他的肩膀转身走了,一时间毫无表情,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楼门口,暮色四合。
几乎是有了北漂就有了中介,许多年一直共生共存,相爱相杀。中介也是北漂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算计着一块八毛,争取多得到几十块钱的利益,之后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到现在整个租房市场已经被中介瓜分得所剩无几,他们以先到者的姿态,赔着笑被房子真正的主人剥削,也居高临下地剥削着我们。
李昼在楼下等着我。
我看了他一眼,好像虚脱了一般,一下子坐在马路牙子上。
呼——终于深深松了口气,不知道这次装得像不像。
“影后,偶尔你还靠点谱儿。”他说。
像不像都得装,要不然就是装得特别洒脱,要不然就是装得特别沉稳。明明已经慌成这个样子了,手心出汗,却只能装。
因为你必须强大,至少看起来强大。这个城市里的人不需要眼泪,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义务去同情弱者。即使手抖了,心抖了,表情一丝一毫也不能叫人看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不人道,OK,你随时可以离开。
而现在我只想骚扰别人,媒介自然是电话,这几天我亲爱的电话非常之劳碌,每隔半个小时都要工作一次,辛苦胜我。
我瞟了一眼五花八门的来电记录,无视,信手直接摁出一串数字,一个黏腻的声音响起来。“对不起,您要拨打的用户已经销户。对不起,您要拨打的用户已经销户。对不起,别打了,挂啊,老娘说话你听不懂啊!”
这彩铃。我嘴角微微抽搐。
“喂,傻帽儿小车车。”一副沙哑的烟嗓响起,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伊莎贝拉。”
“哭了?还是怎么的?喂喂,哭什么啊你,别给我丢人,我说的最后一个方法,好用不好用,嗯?”
“用了,挺好的。”
李昼坐在我身边,一直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觉得有点儿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还是不说话,让我拍。
回家之后我们依然绝望地等待着电话。
最终有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狂喜着扑了上去。
“租金是不是写错了啊,前面多写了一个1是不是啊?”对方操着粗糙的普通话问我。
“一分钱一分货的,我们都不是想一辈子窝在地下室的人,对不对?”
“死贵啦!你一定是二房东,人品特别差啦!手狠心黑,想赚我们的钱。”
“哦,”一瞬间一股火从我头顶蹿了出来,“谢谢您千里迢迢给自己找了个敌人,慢走不送。”
我挂了电话。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电话了。
还有四天,我就要从这里被赶出去了。
夜深了,绝望一点一点随着黑暗蔓延。
伊莎贝拉和李昼看了我一眼,不约而同地又埋头在自己的事儿上去了。
“别怕,实在不行跟我住。”伊莎贝拉随口说。
“或者跟我住。哦,好像不太方便。”李昼自言自语,又翻了一页书。
我看着他俩,有点儿茫然地想,即使我明天就要回老家挖煤,我也会躺在煤堆里,怀念起他们的脸。
临近晚上九点的时候,电话终于又响起来了,我爬起来扑向手机,一只涂着红指甲的手突然按住了我,紧接着它又推了我一把——伊莎贝拉接起电话,狠狠剜了我一眼,用烟雾一般的声音说:“你好,这里是乌托邦公寓,您需要租房吗?”
李昼瞥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跟人家学着点儿。”
紧接着伊莎贝拉突然沉默了一会儿:“哦,车厘子,找你的。”
我疑惑地接过电话,对方是个男人的声音:“你好,这里是CCTV城市频道,明天的面试没有问题吧?”
“没,没有。”我这才意识到,各种事情发生得太多,我把这件事完全给抛在脑后了。
“好,明天见,顺祝商祺。”对方的声音轻快了很多,但是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把“顺祝商祺”这四个字说出来的。
我挂掉电话的一瞬间,伊莎贝拉突然腰肢一软,趴在沙发上:“早说是你找工作的事儿啊,浪费老娘的美好的表情。”又努力捏了捏脖子,吐吐舌头,“和温柔的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