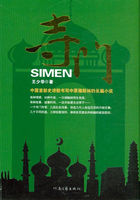“扯淡!齐淑贞、朱廷秀算嘛子东西,给人家宋美龄系裤腰带还嫌她们于粗呢!”
“不过,齐淑贞、朱廷秀两个还是蛮惹人疼的!”刘大虎精神有些振奋。“嘛叫惹人疼?”
“就是招人爱喽。哎,你说你喜欢哪一个?说实在的!”
“论脸蛋子嘛,齐淑贞俏些,可她胸脯太平喽,没嘛兴趣。朱廷秀倒是剌激一些。”
“朱廷秀屁股肥嘟嘟的,那瞟少不了二指厚,就像老娘的脏!”“你昨瞅得嘛子仔细?”
“你也不是一样,你昨知道人家齐淑贞的胸脯平?说不定人家里边有束胸呢!”
“嗨,你狗日的嘛想得那么仔细喽!”“大哥别讲二哥,脸上麻子一般多!”章玉楠“扑哧”一声笑了。
刘大虎也旁若无人地扯开嗓门,刚笑半截,就被章玉楠的于势给挡了回去。
“注意外头,别叫哨兵昕见,汇报给排长,再多关我们几天!”刘大虎咬着腮:“他妈的,我不怕!”
远远地,传来阵阵“刷刷刷刷”的脚步声。“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个耻辱的日子!”章玉楠说。“对,记住!”刘大虎一拳砸在床铺上。
“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外头又传来排长李继岳那一昕就打战的嗓门。
军乐再次响起,接着洋鼓有节奏地敲了起来。
不知过多久,只昕汽车一辆接一辆发动了引擎,接着便是一阵轰鸣,
将窗户上的木板震得沙沙作响。
晚饭后,周元照和王小天来看章玉楠他俩,刚推开禁闭室的门,还没说话,刘大虎便将于中的饭碗朝门口扣了过来:
“滚,滚,滚你妈远远的,你们别来,猫哭老鼠,假慈悲!”
王小天不等刘大虎再说什么,掉头便往回走。周元照也没滋没昧地跟着走,身后传来章玉楠那夜猫叫春似的冷笑。
七
今天实弹打靶。
清晨有雾,缭锡且厚重,把偌大的操场包裹得严严实实。当排头兵刘大虎站好位置后,那队形便一字儿摆开,瞬间便列好了队。
今日与往日不同,一个个精神充足,胸脯鼓得满满的,掩藏着一股威武之气。就连排长李继岳也格外来劲,嗓子如同喝了一碗香油鸡蛋茶,润滑得十分滋润,喊起口令来,透亮丝丝的,像早春的萝卡那般脆。
昨天下午晚操过后,当排长李继岳宣布今天实弹打靶的消息,全排上下都激动得跟什么似的,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是骤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那种跃跃欲试的神情。几个月来的那些苦和累,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能不欢欣鼓舞和雀跃么!一激动,那觉便不好睡,你咳嗽他翻身,床铺也捣蛋,“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尿也多,来来回回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夜几乎没断。“妈的,家后拉钻辘,改场(常)!”人人心里都在骂,骂得兴高采烈。
雾把兵们一颗颗心吊了起来,悬得扑通扑通地乱跳。排长宣布原地待命,那队伍无声无息散开,翘首望着东边天,于不自然地抓紧冰凉的枪柄。但希望还是灌满每个人的胸膛,悄悄地期待着那动情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操场的上空。
终于,那颗不太耀眼的太阳终于慢腾腾地溜了出来,雾恋恋不舍地且战且退,最后消逝在营房外的旷野。蓝天不碧,却也叫人心旷神怡。排长李继岳“进入掩体”一声令下,战士们便一下涌进昨日固定好的位置,匆匆将子弹压进枪膛,心跳便突然地加快,仿佛揣着几只活蹦乱跳的待哺的雄兔。
赵蔼如心惊肉跳地趴在那儿,端着枪,两眼紧盯前方靶心那圆圆的一圈,不多会儿,他便觉得眼睛有点迷糊了。他腾出一只于,用袖管揉揉眼,心中暗暗说:不要慌,不要慌。可那颗不听命令的心却接二连三地蹦脏。立马,他的气也不畅了,像鸡毛不多的风箱杆扯着粗气。他偷眼瞅瞅右边的周元照和左边的王小天,见人家都沉着得很,暗骂自己软蛋,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奔腾的情绪,枪在于中不住地颤抖,还老想着小便。他便将下身紧紧地压在被雾打湿了的地面。为了松弛自己的神经,他有意不去瞅靶子,仰头望着不太晴朗的天空和远处那座含而不露的白云山……
“预备一一”李继岳扯着长音。
赵蔼如忙将目光收回来,单眼吊钱望着准星。他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家中那个瘸子木匠余大栓,当他刨好一根料子,他也是这样的神情,满足地欣赏于中的活,那架势就像在欣赏一件价值连城十分了得的国宝,美得他直流口水,连烟袋杆也咬不牢。
“放!”排长大声喊道。
赵蔼如收住心,慌忙扣动扳机,随着清脆的一声,他觉得他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沙漠。随即,不昕招呼的小便旁若无人地溢了出来。他顾不得许多,急忙拉动枪栓,退出子弹壳,重新压上子弹,瞄准靶心,然后扣动扳机。他不晓得他是怎样打完排长发的五十发子弹的,待他站稳在被枪声震得抖动的大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酸软得连一丁点儿的力气也没有了。
八
当报靶员宣布成绩时,全排人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昕走了耳。出乎人的意料,章玉楠拿了第一名,打了四百六十五环,第二名是朱廷秀,打了四百五十四环,周元照居三,打了四百四十八环。排长李继岳在政教室为前三名披红挂花。之后,不知谁提议叫朱廷秀表演个节目,朱廷秀倒挺大方,泼辣的脸上艳阳高照,她为大家唱一首家乡的小调“火红的高梁”:
高粱熟了,高粱熟了,
家家磨刀,家家磨刀,
八百里天地一片火爆口。
高粱熟了,高粱熟了,
家家磨刀,家家磨刀,
男女老幼齐弯腰口。
……
有人哭了,是赵蔼如。他只打一百二十环,全排倒属第一。许多人跑过来劝。
“别劝,让他哭个够,要不下次再打靶剃个光头也挡不住!”排长李继岳酸不叽叽站起身,“哼”了一声,然后走出了教室。
赵蔼如哭得更动人了,鼻子眼泪满脸。
哭个啥子哟,不就是一朵纸花子嘛,也值得你撕心割胆去哭!”章玉楠不可一世地晃着脑袋。
别神气,今回瞎猫碰着死老鼠,还不知咋的巧的呢!”肖雄望着洋洋得意的章玉楠,满脸不服。
“你逞啥子强,不才打二百来环嘛,俺睡大觉让你练半年,怕也不中!”章玉楠瞥一眼肖雄。
“你别门缝瞧人,把人给看扁了!”朱廷秀说,接着又来劝赵蔼如。大个子章玉楠,不知咋回事,一见朱廷秀,马上矮了下去,笑也不是,
哭也不是,抹抹丢丢地溜走了。
第二天,全排人举行投弹比赛,章玉楠又甩了七十多米,破了前几期黄埔纪录。团长郭大荣专程来排里为他祝贺,还奖励他十块大洋。激动得章玉楠嘴唇一个劲地抖,多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感激之辞。
晚饭过后,朱廷秀和齐淑贞在操场上散步,章玉楠走过来,正儿八经地对朱廷秀说:
小朱同志,俺有句话想和你说。”
想说你就说呗,又没人堵你的嘴!”朱廷秀望着章玉楠那严肃的表情,心里怪想笑。
俺想,俺想单独和你谈谈。”
你们谈吧,我回宿舍。”齐淑贞知趣地转身走了。
黄昏格外静。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在操场上空盘旋。深秋的风吹着困乏的天空,忽明忽暗。
别走得太远了,有什么你快说吧。”朱廷秀停住脚步。章玉楠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远方有什么,他一样也未看清楚。他不停地挠着头,仿佛头发里生了虱子。
“你咋不说呀!”朱廷秀有点急了。
“其实也没嘛大事。”章玉楠好不容易挤出个笑脸来,“俺想请你给俺提提意见。”
“有啥意见好提?”朱廷秀笑了,笑得满脸绊红。“就是说、说、说俺这个人咋个样子嘛!”
“咋个样子嘛……”朱廷秀学着章玉楠的腔调,“一个鼻子两只眼,没瞧出哪块地方不好嘛!”
天上黑影了,羊城已华灯初上,染亮西半个天。一列火车轰隆隆从远处驶来,操场上一阵颤动。
“廷秀。”章玉楠的嗓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俺是说……喜不喜欢俺!”说着,他伸出颤抖的子想去摸朱廷秀的子。
“你要做什么?”朱廷秀使劲甩开章玉楠的子。
“俺夜里时常做梦,梦见和你……”章玉楠突然伸开双臂,猛地揽住朱廷秀,接着伸嘴去寻找朱廷秀的嘴唇。
朱廷秀想喊张不开嘴,想打又伸不开拳,她灵机一动,狠命地按章玉楠嘴咬了一口。
章玉楠浑身疼得直哆嗦,不由自主松开了子,一声没“哎哟”出来,扭脸便跑。
“做你的大头梦去吧!”朱廷秀张大嘴往脚底狠劲地吐了一口。
九
广州的冬天过得特别快,没下一场雪,也没觉得西北风怎么上鼻子上脸,春天便及早巴早地来了。一场情意绵绵的细雨,使得家家户户的晒台上、门前、路两旁的花圃开出许多招人眼的花来,五颜六色,一簇簇,一片片,整个广州城香喷喷袭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这天拂晓,好端端的天空突然飘起雪花来,那雪愈飘愈大,愈扬愈猛,只可惜没沾着地便化了,工夫不大,地上房上便显漉漉的了。
这是广州多年来少有的春雪,梦一般不由人地使人们想起几天前上海那一场大屠杀,弄得本来就阴冷的心头又添了一层寒。
“时间过了!”赵蔼如望着扑打在窗玻璃上的雪花,不由掖掖肩头的被角。
“奇怪呀,天都这么亮了,怎么没昕吹起床号呢?”周元照披衣坐起来。“管他呢,他不吹,咱们才落睡个痛快!”刘大虎将身子往被窝里一钻,
“好冷哟!”
“兴许号兵睡昏了头吧!”王小天自言自语地望着房顶。
“不对,即使号兵睡过了卵,李排长也该来喊呀!”周元照疑疑惑惑地下了床。
“管那么多熊事作啥子嘛,好不容易摊这么一回赏愿,咋呼个啥子嘛!”章玉楠骂骂咧咧翻了个身,把头缩进被窝,嘴里咕哝半晌,然后弄出一个很响亮的屁,“睡,不睡白不睡!”
一声尖厉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早晨,随即外头便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快起来!”肖雄拍拍隔壁上床的程成,然后急忙穿衣服。屋里的人没人招呼,全都坐起来紧张地穿着衣服,有几个先起的,早已从枪架上摸过枪,窜出了门。这时只昕房外有人喊:“都到操场上集合,快!”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飘着。
队伍很快集合好,愣了半天,大家这才发现,营房大门口和操场四周以及远处的弹药库全都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喊口令的也不是排长李继岳,而是武装整齐的威风凛凛的团长郭大荣。
大家正在疑惑,忽昕郭大荣宣布:“所有的人,将枪支交到这边来。”队伍里有些骚动。
“快点,不服从命令,军法从事!”郭大荣声嘶力竭地喊,于臂在半空中一劈。
章玉楠第一个出列,将于中的枪放到指定的地方。接着,每个人都交了于中的枪,然后又按顺序列好队。
“现在我宣布一一”郭大荣把个“布”字拖得有扁担长,“接上级命令,共产党图谋不轨,大有吞并我党之势,中央为先发制人,进行全面清党,务必一网打尽,不留后患……总理所定的‘三大政策’,是为当时的需要,现在情况变了,这个政策不适应了。政策嘛是临时性的,是可以变的,不像政纲那样固定不可以随便变动。根据省主席、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于谕,对黄埔内的共产党进行全面清理……一排排长李继岳已被逮捕。”郭大荣咳嗽了一声,用舌头舔舔唇边的白沫,抬眼扫队伍一眼,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花名册,念了几个人的名字,随即上来几个士兵,恶狠狠地将念到名字的几人用绳子绑了,然后推上营房门口等在那里的汽车。
“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要主动交代,争取宽大!”郭大荣倒背着于在队伍前来回走几趟,又说,“对那些隐瞒不报的,要检举揭发,有功者奖。全体人员,从现在起,不准随便出营房大门,不准结伙串联,不准惹是生非,凡不从者,格杀勿论!”
雪渐亭,从黄埔岛方向漫上来一层层黑云,将阴死阳活的天空染得更力沉重。
“你,出列。”郭大荣一指章玉楠。
章玉楠只觉得脑门“轰”的一下蒙了,一股凉气顺脊梁骨向上爬。心暗想:“我章玉楠这下完了!”但转念一想,“我非团非党的,有什么可怕的?”虽想得这么透彻,但他的腰还是直不起来,并拢的双腿活活撒撒地一个劲地颤。
“你叫什么名字?”“章玉楠。”
“对,我知道你的名字,打靶打得好,投弹投得远……是不是孙文学会的?”“报、报告嘛子团长,俺可没参力共产党!”
郭大荣一咧嬉笑了:“我问你是不是孙文学会的!”“报告嘛子团长,俺说不大清楚。”
“从现在起,由你临时负责排里的一切事情,要努力干。”章玉楠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从郭大荣脸上那种表情看得出来,他的耳朵没出毛病。不由己双脚并拢,响亮回答:“是!”“要查出谁是共产党或者谁与共产党有关系!要深挖!”“是!”
“发现异常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是!”章玉楠重新来了个立正,又说,“是!”
十
几天来,章玉楠虽然费了一番苦心,但还没有查到谁是暗藏的共产党或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急得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说别人,就连他本人也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水平,他整日苦思冥想,怎么能使上司满意,又能体现自己的才能来,现如今他倒恨自己小时候不用功读书,以至于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也没法施展。他走坐吃睡都在想计策,连上厕所也在想。
这天夜里,还真叫他想出来了,这个计谋连他也不由暗暗称好,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他欣喜若狂地摇醒身边的刘大虎,两个人溜到厕所里,章玉楠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你放宽心干,我刘大虎支持你!”刘大虎把胸脯拍得“啪啪”的。“反正这时候是俺嘛说了算,趁此机会报俺那几天禁闭之仇!”章玉楠把牙一咬。
“说得对。”刘大虎握紧双拳,“第一个先把周元照那个小子抓起来,还有……”
章玉楠一把捂住刘大虎的嘴,说:“别走漏消息,一个一个来,还有那一巴掌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