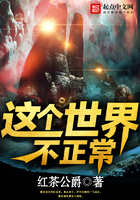其实,这是北魏官场的通病了,门户之见非常明显,世家子弟是一个派系,寒门子弟又是一个派系,绝大多数人都是各自为政,有些人精明圆滑,只知道拍马屁讨好上级,有些人则没有门路,认为自己升迁无望,便开始怠政懒政,大到各级官员,小到这守卫城门的士兵。
宁飞羽今天算是栽在了这小小的守卫士兵手里,他也没办法把自己与后宫的关系拿到台面上去说,只能安排手下的侍卫们在城外安营扎寨暂时休息。
说到安营扎寨,宁飞羽和手下可是什么都没带,好说歹说才找守城门的士兵借来了两个帐篷,十几个人大男人只能挤在两个帐篷里勉强遮风避雨。
陆韶华吃完宵夜便被侍卫带到了周承昀所在房间的偏房。侍卫们心知肚明,可陆韶华却一无所知,她进了偏房后,看到房间里还有道门才明白自己是被安排在了偏房。
“隔壁正房睡的是谁?”
陆韶华实在忍不住好奇心,还是拦住了正准备离开的侍卫。
这位侍卫虽然把周承昀的原本用意想歪了,不过还是强忍着笑意一本正经地回答道:“陆姑娘,殿下住在隔壁房间。”
“什么?”陆韶华呆滞了几秒,急忙往外走,边走边说,“男女授受不亲,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若被日后的王妃知道此事,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侍卫有些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陆姑娘,这是殿下的安排,现如今驿站只有这里还能住人了。”
陆韶华一脸挣扎之色:“柴房呢?柴房应该没人吧,我住柴房也可以的。”
侍卫摇了摇头,彻底熄灭了陆韶华心中燃起的星星之火:“柴房住满了。”
“啊?那怎么办?可我不能住这里啊,不然我去找殿下说清楚。”
陆韶华正欲去正房,却被尽心尽责的侍卫拦住:“陆姑娘,您还是别去了,殿下已经睡下了,更何况这两间房是隔开的,也不算是共处一室吧,您还是将就一下吧。”
陆韶华哀伤地看了看四周,确认偏房的安全后,只能低头认命:“多谢了,你退下吧。”
侍卫关了门退了出去,陆韶华走到床前,直接钻到了铺好的被子里。被子很薄在炎热的天气里盖正好。
陆韶华习惯性地摸了摸头发,想要把发髻解开,可一摸之下才想起来她梳的是男子发髻,也不用多做打理。或许是太累的缘故,陆韶华顾不得睡在隔壁的周承昀,连外衣都顾不上脱去便沉沉睡去。
漫漫长夜,偏房的陆韶华睡得倒是没心没肺,可谁在正房的周承昀却毫无睡意,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周承昀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有生以来头一遭,他和自己的意中人距离如此之近,这种奇妙的感觉挠的他的心头发痒,实在是睡不着,他便起床一连打了两套太极。
可谁知道,太极打完他还是睡不着,无奈之下,他只能不断地在心里默念着陆韶华的诗作。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连念了十多遍,周承昀才有了困意,隔了好长时间才沉沉睡去,睡梦中,他好像看到了陆韶华诗里面的桃树,看到了站在桃树下拿着一枝桃花朝着他微笑的陆韶华。
直到清晨城门才开,宁飞羽此时拿着睿王府令牌才被放行,众人也是无语,可谁都没有多说一句,更没有表露出不满之色,只是暗暗记在心里。
宁飞羽命属下前去睿王府准备粮食,自己则独身前往户部尚书府。陆文德上朝去了,宁飞羽便在前厅中等待,直到巳时陆文德才回府。
宁飞羽将自己返程的目的和沿途所发生的事情详细告知,陆文德异常气愤,可他再气愤又有何用,证人已经被伏杀,想要再寻证人,必须赶往驿站,可敌在暗,如果他们再度收到消息再次设伏还是一样的结果。
陆文德有些为难,思虑再三,权衡利弊,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此时先以赈灾为主,待到返程之时,睿王亲自护送证人回京,行刺皇子可是死罪,如此这般方能破局。我这里会搜集证据,准备妥当,待到睿王回京之时,就是凶手浮出水面之日。不过,我担心的是那些在驿站百姓的安全。”
宁飞羽觉得陆文德言之有理,不敢多做停留,急忙回了睿王府。好在粮食已经准备妥当,他顾不上奔波的疲累,从府中又抽调出一些人手,火急火燎地往驿站赶去。
雒阳驿站里,众人正忙着做早饭,捡柴火的捡柴火,劈柴的劈材,熬粥的熬粥,正忙得不亦乐乎。
詹子濯洗漱完毕,在教孩童们识字,许多孩童因为家境贫穷,始终上不起学堂,请不起先生,詹子濯深有感触,他突然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的书也没有真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成日里只知道吟诗作画,实在是太过惬意。或许,他应该办一个学堂,让天下读不起书的孩童都来读书识字,真正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或许,这样的人生才是他想要的。
詹子濯心想,《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易·乾卦》中又有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由此可见,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方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
看着眼前这些可爱懵懂的孩童,他们那一双双渴求的双眼,詹子濯下定了决心,什么长安城第一才子,这些虚名他统统可以抛弃。
驿站内,读书声朗朗,百姓们看到这一幕,不约而同地对詹子濯竖起了大拇指。
一切好像都很平静的样子,可谁能猜得到房顶之上突然射出许多木箭,正在忙碌的百姓们有一部分人被木箭射中,剩下的人突逢变故,尖叫着躲避箭枝。
詹子濯大惊失色,急忙高声呼喊:“快躲起来,躲起来!”
正在跟着詹子濯读书识字的孩童看到自己的亲人倒在了血泊中,哭喊着便跑了过去。
“别去,别去,都跟我来。”詹子濯飞快地拉住想要去亲人身边的孩童,高声喊道,“都别去,那里危险,快跟我来。”
孩童们都把詹子濯看成是教书先生,还算听话,再也没有人哭喊着要去找自己的亲人,可一个个在詹子濯身后均哭得像个泪人。
詹子濯不敢多做停留,带着孩童们便躲进了屋子里,把门用桌子顶住,让孩童们后退,他自己挡在了最前方。
驿站外头的未曾中箭的百姓也都找了地方躲起来,只能哭泣着看着自己的亲人中箭身亡。
留下来保护百姓的侍卫虽然奋起反抗,可是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能在没有工具的辅助下爬上屋顶,也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伙纷纷捡起地上的干柴火往房顶上扔去。
也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刺杀百姓的杀手们突然退去,并没有对剩下的百姓和侍卫赶尽杀绝。
侍卫长见状,直接组织手下拿起剑杀了出去。百姓们见驿站内再无箭射出,这才敢从躲藏的地方出来,
詹子濯听到门外百姓的哭喊声越来越响亮,把房门开了个小缝,透过门缝往外张望,在看到安全之后,才打开房门,放孩童们出了房间。
驿站内一团乱,熬了一半的粥被打翻在地,原本燃烧的柴火堆早已被踩灭,四处都有中箭气绝身亡的百姓,也有几个穿着侍卫衣服的尸首。
原本宁静和谐的驿站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一片狼藉和痛苦的抽泣。百姓们不明白,他们得罪了谁,究竟是谁要杀他们,他们手无寸铁,他们谁都伤害不了,究竟是谁要致他们于死地。
孩童一边哭泣一边找着自己的亲人,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趴在亲人的尸体上大声哭泣。
詹子濯扶着门框,腿有些发软,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种单方面的屠杀,血淋淋地令他心寒。
“究竟是谁?”
詹子濯仰天长啸,心中无限悔恨,他没能保护好百姓,都是他的错,都是他没有用。
“先生,我们怎么办?”
一位满脸泪痕的中年男子怀抱着一个中箭身亡的妇女尸体,走到詹子濯身边,低声征求他的意见。
詹子濯望着中年男子怀中的妇女尸体,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她是你的妻子?”
中年男子把怀中的妇女轻轻放到地上,替她拨开额前的碎发:“她是我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被官府打死了,如今她也死了,就剩下我一人了。”
詹子濯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劝慰眼前这个失去了所有亲人的男子,就连节哀顺变这四个字都说不出口,这位男子的哀伤他也感同身受。
中年男子抹了抹眼泪,坚强地站起身:“先生,我是个只知道种地的粗人,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才能给自己的媳妇和孩子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