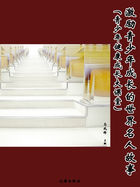院子里,一阵风吹过,阴风阵阵,原本阳光明媚的小院一下子变得阴暗起来,老槐树“沙沙”的声音越发的响亮。放在石桌上的白色坛子,此时摇晃起来,风吹得越发的阴凉。原本密封的坛口,有一股阴气缓缓升起,天空越发阴暗,像是夜幕降临。
“老婆子,”隔壁的小院传来老头子哄亮的嗓子,“这鬼天气怎么回事,刚刚还晴天的。”老头子走出房子,看到天阴暗得跟黑夜似的,奇怪地道。
“老婆子,老婆子,”老头子见自家老婆子没应声,越发地喊大声起来。
“唉,老头子,你唤啥啊。”还在安慰阿庆娘子的老妇人终于不耐老头的叫唤,出屋来。“哟,这是咋回事啊。”见到阴暗的天,她惊讶得不亚于她家老头。
此时,石桌上的坛子早已不再摇晃,风也渐渐停歇,那股阴气跟回镜头似的缩回到坛子里。而这一切,老妇人似乎一点也没发现院子里的异常。她抬头看看天,只见阴暗的天空,层层乌云笼罩,一丝阳光慢慢透出云层,乌云渐消渐散,转瞬间,就消得无影无踪。老妇人心中奇怪,却也没当回事,对着院墙外的自家老头喊道,“老头子,俺等会就回。”
老头子,见她应了,也就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回了自家屋子。
老妇人回屋,见阿庆娘子躺在坑上,脸上挂满泪痕,却已没有眼泪流出,双眼无神,无力地垂着双手,整个人变得毫无生机。
“唉,”老妇人长叹了一声,坐在坑沿上说道:“阿庆嫂,你想开点,这都是命啊。!”老妇毕竟是老实的山里人,也不怎么会安慰人,说完,便陪着她默默垂泪。
老妇人坐了一会儿,便起身道:“阿庆嫂子,你节哀吧,既然人死,你就安心得过日子吧。”她说着,边向着屋外走去。
女子勉强起身,对着老妇人道:“老婶子,您回吧,俺没事。”
老妇人摇摇头,出了屋回去了。
女子无力地靠在坑上。
没过多久,隔壁就传来老头子哄亮的声音:“老婆子,咋回事啊!”
“唉,”老妇人直叹气,“命苦啊,这日子,该怎么过啊!”说着,她的声音渐渐小下去,隐隐约约地听到她说,“阿庆没回来,方才有人来传信,死在外头了……”
女子听了,眼泪又下来了。她从隔壁山村嫁过来,当初只用了两头猪,三只羊,几只鸡作了聘礼,娘家原来有个老娘随着哥嫂生活,自从她嫁过来,没过两年,老娘就病故了。她现在就算有家也归不得。
原本指望着靠夫婿过活,没想到夫婿新婚三月就离了家,她苦等三年,日盼夜盼期望着他能平安归来,不指望能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就望着夫妇和睦,能生几个娃子,平安过一生就好。
却原来夫婿身死外头,叫她以后如何指望?她越想越灰心。外头晴朗的天气又变得阴暗,她突然想到夫婿的骨灰坛子还在外头,强打起精神起身,摇摇晃晃地扶着门槛出了屋子。
只见院子里,石桌上,那个白色的坛子,阴气缭缭,一股青烟在阴风中徐徐上升。女子睁大了眼,身上一下子有了力气,扑向石桌。
“夫君,夫君,是你回来了吗?”女子泪眼婆娑,伸着捧着那白色坛子,激动的摇晃着。
“夫君,你是不是放心不下为妻,真的回来了吗?”女子大声的呼喊着,毫不在意声音渐渐涨大。
“阿庆嫂子,你这是怎么了?”隔壁传来老妇人的惊奇地喊声,只听见“噔噔”地声音传来,没过多久,就见老妇人慌张地跑来。
“婶子,你快看,俺夫君回来了,阿庆回来了。”女子激动地向着老妇人喊道,整个人像打了激素般兴奋起来,将手里的白色坛子递向老妇人,示意她看。
老妇人看了看一切正常的坛子,怀疑地看向女子,“阿庆嫂子,你是不是疯魔了?”她有些迟疑地道,心想这阿庆嫂该不是受打击太大,失心疯了吧/
“不,婶子,刚刚这坛子冒出青烟来了,是阿庆回来了。”女子还是有些激动。
“阿庆嫂子,你还是先进屋歇着吧,”说着,老妇人伸手扶着女子,引着她回屋。
“你看,天都暗下来了,看这样子像是要下雨了呢,你还是把这坛子抱回屋吧”老妇人扶着她边往屋里走,边唠叨:“先放几天,等到了头七将阿庆安葬了吧。”
女子见坛子不再冒出青烟,似乎方才真是她看错眼了,难道她是产生幻觉了。可能是自己太过伤心了。她将怀里的白色坛子抱得更紧了,随着老妇人进了屋。
看到堂屋里的案桌,对着旁边的老妇人道:“婶子,你看将阿庆放在这好吗?”
老妇人见那案桌,干净整洁,点了点头,“就放这吧。”
女子将白色坛子轻轻放下,又找来的抹布,将案桌擦了擦,将坛子重新安放好。老妇人助她上了香炉,上了香。安置妥当了,就扶着女子进了里屋,重新将她安置在坑上,问:“阿庆嫂子,你也该饿了吧,老婆子这就回去给你下碗面去。”
女子拉住她要起身的手,说道:“婶子,不用了,俺吃不下。”说着,便又哽咽起来。
“唉,饭还是要吃的,人是铁,饭是钢啊。”她轻声安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