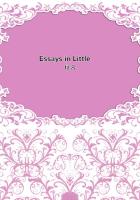龙城幼稚肤浅的把戏层出不穷,却一次又一次被仇天涯轻而易举地破解。
有回龙城把他引到了一片海带丛里,海带立马缠住了仇天涯全身,而龙城却在其中自如游走。龙城自以为能把他困住许久,结果没一会儿就感觉到自己的脚腕被人抓住了,一回头便看到仇天涯在他的身后,而摇曳的海带已经被斩得一干二净。龙城脸上瞬间流露出惊恐,那一次,仇天涯用海带把他捆在海柱上整整两天;
还有一次,龙城命一群墨鱼包围住仇天涯,朝他不停吐墨,仇天涯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手里的子牙剑又突然被人抽走,仇天涯凭直觉去抓龙城,结果手背却被子牙剑划了道口子,龙城趁机逃之夭夭。待到迷雾散去,龙宫门口一声轰隆,仇天涯赶到龙宫,龙王心爱的百年大珊瑚已被砍倒,根上插着子牙剑。龙王出来一看,立刻心疼万分,龙城故作正派地跟龙王告状:“父皇,你看这就是你找来的高人!”
仇天涯手上的伤口被海水渍的发疼,他伸出手,子牙剑便自行飞回了他手里。面对栽赃嫁祸,他却毫不辩解,而是把剑递给龙城,说:“它是你的了。”
龙城露出万万没想到的神情,试探问:“我的?”
“对,你的。”
龙城庄重地接过子牙剑,自认顶天立地了两百年,却连一件称心的兵器都没有,仇天涯如此不吝啬子牙剑,龙城便认为他和自己一样顶天立地,当即发了话:“好!看在这剑的情面上,你可以当我的师傅!”
时隔多年之后,仇天涯还是会记得龙城那时说的话:“但我不想叫你师傅,这样,我上无兄长,就管你叫哥哥如何!”当时仇天涯的脸上爬上了一抹笑意,龙城一时豪气冲天所拜的师傅让他在日后吃过不少苦头,以至于他经常怨声载道,可却从未后悔过,反而随着日益了解而愈发对这位师傅五体投地。
龙城曾问过他当时为何要笑,后者坐在蚌上对他说:“凭你父皇的年纪,叫我一声‘祖父’也是不为过的。”
“啊?那你为什么比父皇看起来更年少呢?”
“因为我生于六界之外,没有寿命在册。”
直到今日,龙城仍然不能明白仇天涯说那句话时的神情。
一剑刺出去,没有再收回来,握住龙城的那只手离开了,使龙城从回忆里醒了过来。这招才使了一半,司魂却已站回一旁袖手旁观,龙城感觉失去了支柱,下半招夭折在他半天的迟疑里,挫败感重回心头。
收回子牙剑,地上那条弯曲无力的划痕令他触目惊心。
“天涯哥哥,你回来了。”龙城盯着手里的子牙剑,眼中深渊让他自己的灵魂都跌了进去,语气穿越回了当初的两百岁。
“嗯。”这回司魂没有责怪,声音柔和了许多。
“父皇怎么样了。”
“你放心,他很安全。”
“刑天呢?”
“我没有跟他交手,但我已经使他走了。”
“有劳天涯哥哥了。”
“龙城,”司魂过去拍着他的肩,“子牙剑是把好剑,它不会认错人的。”
龙城侧过头去看司魂拍在他肩上的手,当初划出的伤口已留下了疤痕。由于银光甲的缘故,司魂身上并没有多少伤痕,因而此刻他觉得自己做下的这道伤痕很耻辱,他替天涯哥哥耻辱,为自己耻辱,那个抵御了千军万马的天涯哥哥,岂可被这样一个荒唐小儿留下伤疤。
“天涯哥哥。”龙城的声音带着哭腔。
“嗯?”
“你不该给我子牙剑的,我不配。”龙城将剑举到司魂面前,“还给你吧。”
司魂推了回去,“它本也不属于我,是我偶然在天之涯的崖壁上拔出来的,听闻是世始时候的宝器。多年以来,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使得了它,直到那年我带它去了北海,还是稚子的你竟能将它抢走,还用来陷害我,当时我便知道,它应是你的。”
“给了我,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总有一日,你会和子牙剑两不辜负。”司魂说,“龙译已经审完了,你是想继续留在这里练剑,还是想我一起去看看?”
龙城略施法术,子牙剑在他的手里消失无踪,司魂见状说:“走吧。”
子时已到,阳间万物皆入睡,阴间亡魂却是醒时。司魂与龙城走在去往地衙的路上,各怀心思,于是都不言不语。
北海上第二次重见,刑天已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刑天。也是,早该将他看透了,当年自己刚被打入地狱之时,他不就立马撕开真面目了么。司魂初是不信的,这八百年里他甚至不敢去揣测,直至龙城龙译二人皆死于刑天手下,终于是亲眼所见。
他从阿鼻地狱的边沿救回了个魔头。
“司魂大人有礼,司阳大人有礼。”司魂被鬼差打断思绪,方知原来已经走到了地衙,龙城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打怯,愈是到结果揭晓,人便愈是想要拖延拒绝。
“属下参见大人。”司魂与龙城齐声说。
“来得正好,”陆判说,“司刑,说出来给所有人听听。”
苏子幕:“回大人,四皇子无一罪过。”
龙城听罢舒了半口气,但还有半口气悬在喉咙间,究竟这样的审判结果会给龙译带来什么去处。这时陆判对众人说:“你们先出去,我有事和司魂商讨。”
除司魂之外,其余人答道:“是。”
众人出去之后,陆判从堂上走了下来,到司魂面前说:“你看龙译如何?”
“大人是指什么?”
“龙译岁数虽不大,却比一般人稳重多了。龙王九子里只有他一直在帮老龙王料理北海,龙城虽是太子,却也不及,而恰好他又有冥神的命格。”
“大人是想留下龙译?”
“这样龙城心里也好过点不是。”
司魂欣慰一笑,“若龙城能感念大人这番心意就好了。”
陆判笑着摆摆手,“可不敢指望这个,他少让几个人投错胎本座就谢谢菩萨了!你只说,觉得行还是不行?”
“大人主意甚好,只是不知大人想要给龙译什么位分?”
“你们三个都是一样的位分,龙译来了自然也不能低于你们,就封他做司命,你看如何。”
“甚好,那他主掌什么呢?”
“地府事情多是多,却也杂,渡魂台交给龙城一个人怕是不行,先让龙译去帮衬着,而后本座另有安排。”
“另有安排?”司魂从陆判的神情里读出了些深意,于是平日从不多嘴的他这回追问了起来:“敢问大人可否告知?”
陆判捋着胡子,神情微有惆怅,但还夹杂着一丝安然,“司魂呐,我老了。”
司魂看着陆判,心中怅然若失,苦笑道:“龙译好命。”
惆怅在陆判脸上转瞬即逝,地府的人没有空闲来一场完整的喜乐忧伤。“龙译是仙道的人,总该禀明天帝的,这回你去罢。”司魂没有迟疑,但是眼神里包含了千钧,“属下遵命,属下告退。”
“司魂,”陆判对他说,“世事锁不住清风,去时匆匆,来亦自如。”
这不是教导,也不是告诫,陆判对他一切的话语,皆是忘年之交的恳切和提醒。正如陆判自己说的——他老了,他几乎与六界同寿,自天地伊始就执掌乾坤命轮,足够做龙王祖父的司魂在他面前也是晚辈。即便这样,很多事情陆判不会以长者的姿态去强加于司魂身上,因为尽管跌落了神坛,司魂依旧是六界里少有的道高之人,跌宕起伏之后,除去官职,他们是凄冷冥界里被搁置在危处的孤独者,两个惺惺相惜的孤独者。
司魂知晓陆判的心意,郑重说:“谢大人。”
与那三人转述了陆判的旨意,苏子幕一听便揪起了心,面上还故作风轻云淡,对司魂说:“修炼了上千年,我可都没福气去到那天上走一遭,不如你将这好差事让了我。”
司魂看透了苏子幕的本意,拍拍他的肩,直言道:“不必了,多谢。”
一向能四两拨千斤的苏子幕变得无措,他想不通陆判此举何意,司魂此举又是何意?方才只要司魂允了,他愿意不嫌麻烦地去替司魂走上一遭,天界的人不会对区区一个阴使有所言语,管他是如何从狐妖变成的司刑,但放在司魂身上就不同了,只要他在天门前一现身,便自带来了一场风雨。
陆判岂会想不到这些,那又为何要让司魂去受这样的难堪?至于司魂,他或许是不愿表现出太草木皆兵,以证明他还没沦落为过街老鼠?苏子幕只清楚自己拗不过司魂的选择,将目光转向了一边。
司魂对龙译说,走罢。
清风欲何去,主人莫掩扉。
“冥界阴使司魂,携北海四皇子参见天帝。”
天界的确因他的来到而出现了一场暗流骚乱,刚一迈步进去,窃窃私语声便不绝于耳,只是,没一人讥诮他为罪徒,有偶与他碰面不好回避的,甚至仍称他作仇将军。谁都想不到,时隔八百年之后,人们会因北海四皇子之死而再次见到仇天涯,他们以为仇天涯早在某层地狱的酷刑之下灰飞烟灭了,这下子所有人又牢牢记住——这天底下还是有一个仇天涯在的。
回冥界之前,温琼追出来与司魂叙旧,北海一见,他回天界之后没和任何人提起这次照面。二人话里都避免开那场风波,说的都是以往最逍遥自在的时光。
“能帮我个忙么?”临走时司魂问。温琼笑他的些许生分,“要我做什么?”
“替我去趟梨园。”
司魂在天上没有呆多长时间,冥界已过两日。陆判问他:“如何?”
他答道:“无何。”
“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你该在人前露露面了,总躲着不是回事。”
“我没躲。”司魂说,“无所谓,左右我永世都为冥界之人。”
“你啊,本就不是哪一界的人。”陆判还未说完,司魂插嘴说:“大人,花等不了太久的。”表露出了他想退下的意图。
陆判瞥了一眼他手里攥着的东西,和声说:“退了吧。”
醇凉正蹲在地上摆弄灶火,守着这口灶百年了,水蓝轻纱的衣衫却没染上一丝尘灰,她已经能够通过脚步声来辨听司魂的到来。“两日不见大人了。”醇凉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正好迎着司魂的面。
司魂走到她跟前,说:“是不是都不习惯我不来的日子了。”
“是怕大人不习惯。”她与他耍起了嘴皮子。
“龙城的弟弟死了,我带他去了天界一趟。”
“如此司阳大人可要伤心了。”
“没关系,陆判大人封他做司命,他们兄弟可以同在地府,他弟弟叫龙译。”
“那得恭喜司阳大人,也恭喜大人,又多了一人替你分担。”
“是啊,总算能留出更多的时间来看你。”
果然三句不离此。“大人不该把时间浪费在孟婆身上。”
“八百年都熬过去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司魂把一物递到醇凉面前,“不喜欢白色的山茶,白色的梨花总该喜欢吧。”
醇凉放下勺子一看,是一枝梨花,上面密密的开了一整枝,白得仿佛还沾着天界的雾气。她没有接,只是执拗于司魂的话,“大人怎么就确定我一定喜欢?”
“因为这是你的梨花。”司魂说。见她不腾出手来接,司魂变出个瓷瓶,放在显眼却不碍事的地方,把花插了进去,边摆弄边说:“在天上遇到了温琼,我让他去你的梨园折了枝花,树下还埋着你当年酿的酒。”说到这里司魂忍不住笑了起来,“八百年的佳酿,我自作主张让他拿去喝了。你记得吗,当时他们三个沾了我的光,老蹭你的酒喝,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却是一口难求。”
醇凉默默地看着司魂伺弄,只说:“花迟早会死的。”
司魂不以为然,“这里有什么不是死的。”
“彼岸花就是活的。”醇凉转回身去熬汤。
“可梨花是你的花。”
一场白雪尽,烈火灼其华。
还是一如既往的艳丽,烧得天际都泛红,妖境里正是夕阳时,万花开得正艳,一只亮丽的绿色孔雀在花丛里昂首挺胸,刚刚露出个小脑袋,看见横卧在榻上的菁华,它缓缓展开了孔雀翎,逗得菁华一笑,顺手擦去了唇边的酒滴。几只妖坐在泥土上作乐,见着妖尊的红颜一笑,它们互相看来看去,然后也跟着嘻嘻而笑,孔雀、乌鸦、蝮蛇,万妖各有各的自在,偶尔菁华一时兴起,还会广布恩泽,她将妖界变成了世间最大的极乐世界。
拈起杯子,菁华忽然想起了故人的好酒。
太阳沉得无影无踪,圆月还未高高升起,正是短暂的黑暗,菁华听见妖群里的骚动,便知是谁来了,自然地起身走到一旁,接着黑暗中出现了刑天的身影,他毫不客气地躺在了菁华的榻上。菁华一挥手,整个亭子里的灯火都燃了起来,而下面一个妖精都没有,全跑光了。
菁华坐在丛边,一把花藤交织出的椅子托住了她,她慵懒地斜倚着身子,看见刑天毫无生气地眯上了眼睛。
“你把北海四皇子给杀了?”菁华问。
刑天睁开眼睛,抓起酒壶往嘴里倾倒,倒光之后就随手将酒壶丢在了地上,一只小妖从地里探出半个身子,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拾干净,同时流露出惊慌的眼神,菁华用目光安抚它,小妖收拾完碎片又立刻遁回地下。“这回可不怪我,北海的老龙王自不量力,他先来招惹我的。”说完刑天扫视一圈狼藉的桌子,菁华知道他在找什么,遂起身变出一壶酒,给他斟了一杯,刑天再次一饮而尽,菁华问:“总归不如她的酒。”
刑天嘴角掀起,不屑地哼了一声,菁华倒完酒又坐回了原处。“你杀了北海两个龙子,”菁华说,“他会恨你的。”
刑天不知道来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像甚是疲惫的样子,闭着眼睛说:“谁?仇天涯?”
菁华倚在藤椅的一侧上,没出声,表示默认。
“谁不想把我除之而后快,不连你都在恨我吗?”
一听他提到了自己,菁华阴阳怪调地说:“我哪儿敢恨你,承蒙魔君大恩,我方能有这八百年的快意日子。菁华现下一切,还不是拜你所赐?”
刑天听出来她的言外之意,“你是嫌我不作为,可你还是否知道时机二字?莫心急,眼下时机到了。”
“什么时机?”菁华问。
“我需要一个人——”
“谁?”
“听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