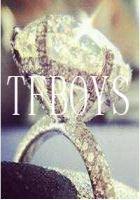“老公,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死。就好像你一次又一次地骗我,隐瞒我一样。就算我看到你躺在我面前了,我还是会以为你是在演戏。是在麻痹对手。所以我只是偶尔慌张和不确定,但我还是相信你和我都好好的。”
所以方才,我并不是那么害怕。
可现在想来,我真的后怕。
“咱们做个约定好吗?如果你是演戏给别人看,一切都是假象,你就给我一个我们之间的暗号。让我清楚让我明白。如果是真的,也请你给我一个暗号。”
闫祯抓住了我不太安分的手,点头道:“你这个提议倒是很好。”
闫祯思索了下,道:“如果一切都是假象,我会给你留下Y这个字,Y也就是闫祯在骗你。如果一切都是真的,我会留下P这个记号。表示,潘雨彤,我没有骗你。”
对了,闫祯和我约好的,一定有东西遗留下来。
如果一切都是假象呢?
“蒋少杰,闫祯是在哪儿被发现的?你带我去,带我去看看。”
蒋少杰立刻去开车,我带着孩子们跟在了蒋少杰身后。
到达了一个水流相对较缓的河滩那,蒋少杰指着的一处道:“这里,就是闫祯被发现的地方。”
我走了过去,绕着那个地方看了又看。
一堆砂砾,一些石头落叶,上游漂流下来的垃圾,我什么都没找到……
“警方没有发现什么吗?”
蒋少杰摇了摇头。
我低着头继续翻找,直到天色泛黑,几个孩子灰头土脸地查看了一圈又一圈,对我道:“妈妈,没有看到Y也没有看到P。”
我回头看了眼两个疲倦的孩子,心一疼。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不给我留下一个Y,闫祯,我那么痛恨谎言的人,却恨不得这个时候你是在骗我。
我颓然地坐在了地上,两个孩子没有再问我什么。
我和两个精疲力尽的孩子坐在了蒋少杰的车里,孩子们累得都睡着了,而我痴痴地呆着。
外头再次下起了雨,我靠着窗,忽然一阵恶心反胃。
我摇下了车窗,对着外头一阵干呕。
脑仁一阵一阵地疼,蒋少杰把车开到了路边,我打开车门,却发现什么都吐不出来。
然而,这种恶心的感觉却一直持续着。
蒋少杰不放心我,就把我送到了医院。
“医生,她是不是怀孕了?”
蒋少杰问着医生,医生让我去做一个尿检和抽血,半个小时后,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医生盯着脸色苍白的我,道:“你没有怀孕。你现在还是头疼干呕?”
我麻木地坐着,蒋少杰替我回答了是。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刺激和不能接受的消息,有些人对无法接受的事实的反应就是恶心头痛反胃,甚至还会四肢发冷,浑身颤抖。我看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蒋少杰叹了一口气,道:“医生,她会一直这样吗?”
“那要看什么消息。”
蒋少杰坦言,“她丈夫我兄弟没了。”
那医生愣住,道:“那情况会比较严重,就怕她会一直这样呕吐,吃什么都会吐。这几天最好先住院,打营养针,你们家属朋友一定要陪着她,她现在还是哺乳期,很容易有些不好的想法。”
蒋少杰给我办了住院,我躺在了病床上,对蒋少杰道:“燕子需要你,我这有很多保镖,你快回去。”
蒋少杰犹豫了下,对我道:“燕子没事。”
“没事什么,你们这些男人,一个个的都不顾家,你们知道家里的女人每天担惊受怕是什么日子吗?滚,都滚!”
我丢开了枕头,蒋少杰被我逼地没办法,只好离开。
我躺在床上,我知道我不能颓废,我还有三个孩子,我还有妈还有严奶奶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还要靠我撑着。
我曾经答应过闫祯,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定要撑下去。
就算活地不黑不白,就算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甜蜜的生活,我还得活着。
两个孩子躺在我的身边,我摸了摸他们的脑袋,发现他们从找不到那Y和p开始就再也没有提起过爸爸这两个字。
他们比一般孩子要敏感,敏感地知道,他们再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我也无法给他们回答。
他们更清楚,我已经是一个在沙漠里精疲力竭的骆驼,不能再承受任何一根稻草。
我两个孩子,用这种方式爱着我,保护我。
他们没有哭闹,安安静静地守在我身边,就算他们今天饥饿难耐,也没有对我说一句,妈妈我饿了,我们回去吧,别找了,找不到什么字母了。
眼泪无声的落在了枕头上,湿润了我的头发,染湿了枕巾和被子。
我不可以倒下,我除了照顾我的家人,我还必须给闫祯报仇。
那个杀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凶手,不知道还藏在哪儿为结束了闫祯的生命而庆功。
可伤痛来的没有节制,身体拒绝着一切闫祯已经死亡的消息。
我空洞而变得荒芜的脑海里,只能浮现出闫祯的种种过往。
他说,想要复仇吗?我帮你。
他说,潘雨彤,我只是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土壤,他说潘雨彤,你该长大了。
你一定能破除那个篱笆,站在高高的山头,在那一片草地上成为最为粗壮的树。
他说,生命赋予我的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的慈善做出来了,他说好人会有好报。
好人……为什么会成为寡妇!
我的工作室已经上了正轨,我像是他们口中的人生赢家一样,而我却仿佛只是坐了一个梦。
那个由闫祯为我编织的一个梦,在他离开后,就犹如见不得暖阳的冰雪,全部消融,一切都成了钢筋空壳,而那些华丽的过往,只留下了这么一个空壳。
闫祯,我宁愿你什么都不曾给过我,我宁愿上天给我的垂怜能全部都给你。
可这样的你,这世上给与我光明和真诚的人,再也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这个病房就迎来了不速之客。
我正要办理出院手续,告诉两个孩子,我们要回白家去的时候,白老和白云以及白清扬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了他们一眼,道:“见过爷爷,爸。”
白老两鬓斑白,才短短几天没见,就仿佛老了十岁。
他来到了我的身边,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道:“你没事了吗?我来之前听说你病了。”
我把那骨灰盒抱了起来,道:“我还有孩子,还有家人,我还有爷爷的信任,这整个白家不是要给我管了吗?我不能有事。”
白老很早就有让我和闫祯接手白家的意思。
白老叹了一口气,“白家现在由清扬接手。”
我微微一愣,看向了白云身后的白清扬。
“真快啊,闫祯昨天刚走。”我对两个孩子道:“我知道事实已经无法转变,闫祯的冤屈也洗不掉了。但是人不是还要生活的吗?”
我知道,我必须回到白家。
在闫家,我得到的消息必然是少之又少。
白豪是怎么出现在那个仓库的,他离开前都见过谁,这些信息,除了在白家,我一点都打听不到。
白豪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就算再凶险,我也不能让闫祯蒙冤而死。
“爸,爷爷,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回去吧。我想妈一定很着急。“
我的双手忍不住地颤抖,能给白夫人的,只有这么一盒骨灰,白夫人是不是又会发疯?
那期盼了几十年的儿子,相聚不过短短几个月就再也见不到了。
白云来到了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雨彤,暂时不要告诉她,我怕她承受不住。你二叔二婶的死,和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低下头,道:“爸……”
白云踉跄了一步,道:“清扬,放过她一把,就当我求你。不要再提你那个无理的要求。”
白清扬来到了我的面前,他倏然道:“爸,这件事我决定了,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让这件事做到。”
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
再一次的恶心袭来,我跑到了卫生间,一阵干呕之后,医生进来对我道:“我建议你做一个心理治疗,否则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的。”
我摆了摆手,尖锐的指甲嵌入手心。
我是一个演员,我本应该把平静地接受闫祯的死这一段表演出来。
然而,身体却意外地诚实。
我靠着冰冷的洗手池,看着镜子里头狼狈而憔悴的自己,猛地一把水掬到了脸上,让自己不要将仇恨的心理表现地太过明显,至少那凶手能对我稍微放松警惕。
否则,就如闫祯说的,我和孩子都非常危险。
闫祯,你会保佑我的是不是?
我眼眶通红,忍了忍,打开卫生间的门,却看到了几个脸色不一的面孔。
“雨彤,你这是怀了?”
白老牢牢地盯着我,他略是死气的脸上像是生出了一丝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