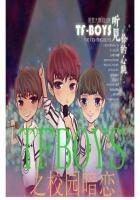伍梅在那个晚上想起了家里还等着自己的小虎哥,就提笔写了封信给他。几个月后爹妈却把同一封信寄回来,又在信底下加了一行大字:“人家早结了婚,还把你给了他身子的那事到处说,你丢尽了咱伍家的脸。”伍梅盯着那几行字,也像输了什么一样,从此对什么都没有了抵抗。她让那些男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抵去几百块的债务,这楼里的阴影,也罩在了她的心房上。
这一天许太太心里烦着,几个月来她总是能听见伍梅房间里的响动,她不知道自己是该去找伍梅谈一谈,还是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就这么毁了,可她还有哪条路?伍天会怎么想?就这么想了半天也没得出个结论。她又想起作家已经一日没下来吃饭了,就把中午剩下的饭菜热了热,又拿上酒杯,往里面倒上一点威士忌。
敲响门的时候,作家眼神聚焦在许太太的身上,这让她脸颊上飞快闪过一丝绯红。一转眼,作家已在这里住下了整十年。作家是不矮的,却因为多年伏在桌前,许太太差一点忘记他的身高。他有四十几岁吧,抑或是四十岁不到?这十年里阴影楼外的什么都在变,似乎只有这里面的许太太和阁楼里的作家没有变。作家的眼神依旧单纯忧郁,声音也低沉的好听,许太太不自觉地脸又红了一通,问他:“你又在写啦?这次写什么呢?”
那作家说:“一个爱情故事。”
许太太也不问个究竟,那作家却开了口:“我在写一个单身女人和一个作家的爱情故事。”
作家就看着她,也不说下去,偏偏让许太太独自去咂摸这话里未挑明的意思,许太太却慌了,胡乱编了借口就跑下楼。她这会儿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胸脯,好像又塌下去了一点,脸上的斑点也隐隐约约地长出了几颗,唉,她心里叹着气,更何况,再好的男人也不愿意和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在一起吧。许太太想了想,把柜子里半瓶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点,喝到胸口发烧。
伍梅不久就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可那些男人接着来,高矮胖瘦的,都是同一样的猥琐。原本改邪归正的伍天再一次受蛊惑赌瘾发作,在赌城里一宿运气不佳,可人人都知道他有个漂亮的妹妹,甘愿借钱给他看他流水般输掉十几万。伍天去找伍梅,发誓再也不赌了,可是伍梅的眼睛里却没了光,只剩下顺从。
伍梅快要临产的那几天,许太太四处联系着医院,可伍梅执意不去,她求伍天拉来个接生婆,胡乱塞了二百块。接生那一日,连续一天一夜,伍梅在屋子里咬断了枕巾,湿透了床铺,就是没吭一声。等到接生婆接过许太太备好的红包告辞时,伍梅半倚在床边,脸色惨白得像死了一回。许太太一口口把红糖水喂给她,而伍梅看着身旁粉红色的小婴儿,她自己没哭,许太太看着伍梅几绺粘在前额的头发,想起了她初来的那一天,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半年后孩子已经长出模样,一双眼睛是欧式的,头发半黑半黄,皮肤也白得透明。伍梅叫孩子小雨,她只有逗孩子的时候脸上才带笑。伍天把一个男人的容忍度用错了地方,禁不住诱惑重操旧业,赌债又欠了许多,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债主追到门上,逼得他把一份工作也丢了。伍梅彻底成了赚钱和还钱的工具,许太太帮忙照顾孩子,常常抱着这孩子到作家的阁楼去,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必说,一边看作家写字一边织毛活。
这天晚上一个男人从伍梅屋子里走出去,许太太假装没看见,嘴上逗弄着孩子心里却想着,苦命的丫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正想着这些,伍梅却开了门,许太太一时慌了神,一张脸红着,像被人看穿了心思。她说:“伍梅……”
伍梅说:“许太太,我明天早上要去别的地方走一走。”她说完,有些犹豫,好像又要说什么,又止住了。
许太太问:“你去哪儿?”
伍梅说:“挺远的地方,许太太,我明晚在别处吃饭,别给我留饭了。”
许太太问:“你带小雨去?”
伍梅摇摇头:“许太太,我要麻烦您了,那地方她没法去。”
许太太点点头,看见伍梅的脸上竟然上了妆,裙子也是不常见的,整个人竟有一股凄凉的美丽,她身后的屋子,空了一半,许太太看见她缓缓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