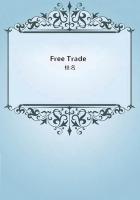婉儿与太子李贤之间的关系因为那场“赵道生事件”后的谈话而悄然有所改变,自那那一回往后,每当她再度递来奏议奏状,李贤都不再让她在大门外候着了,而是让她直接去书房。
“表面上看,我这赌是打输了,就冲这一点,我好歹也不能每次都把你晾在东宫门外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仅仅是表面上输了,不信,咱们接着看。”李贤轻描淡写地说,“张泉儿是故意引你来看我和赵道生的,以后他们两个都不会出现在书房了,你大可以放心。”
这一日午后,李贤把婉儿让进书房并没有让她在一旁一味干等,而是说:“这书房里有很多好书,这些好书你在内文学馆里是肯定看不到的,等我的功夫,你只管随便取阅便是。”
婉儿认真地谢过了太子,若说是别的,她怕是要一概谢绝,可论到书,婉儿总归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于是那一日,婉儿很快徜徉于一片新的书海中,太子说的没错,这些书大部分是她没有读过的,她自幼长在掖庭从未出过宫,一本《研神记》便让她瞬间忘了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婉儿不知道她自己看了多久,合上书本时,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看吗?”李贤冷不防的一句,吓了她一跳。
“奴,奴婢……太子恕罪,奴婢看书一时忘了时间……”
“没问你这个,直接说好不好看。”她看见太子面带微笑地看着自己,似乎一点怒气也没有,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好看,真好看!”
“那么这本书你带走。”
“啊?”
“没错你带走吧,”李贤说,“天色已晚,带着这奏状回你的天后去吧。这本《研神记》算我送你的。算是为上次的谈话向你道歉。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输给你的赌注。”
李贤把夹着自己见解的奏状和那本《研神记》一同拍到婉儿手里,然后不由分说地反剪着手走出书房。
婉儿跟着他走了出来。已是酉时了,整个大明宫笼罩在夕阳暖暖的色调中。
只见李贤伸了个长长的懒腰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是一天!”
看着他的背影,婉儿的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了一下。
武后得知太子注疏的事情,表示非常欣慰。婉儿知道这欣慰是发自内心的,听着武后口中的赞叹,她心里也很为李贤高兴。
一日,婉儿在武后那里当值。武后忽然问她:“婉儿,贤儿他很喜欢你吧?”
“奴婢不敢!”婉儿惶恐地答。
不想武后一听却先笑了:“这有什么敢不敢的,一个人若真喜欢你,还问你敢不敢让他喜欢?太子前日还专程来对我说想让你去做她正式的侍读呢。”
“太子侍读?!”婉儿更惊讶了。
“没错。婉儿,你知道太子以前的侍读是谁吗?”
“禀天后,奴婢知道。是王勃。太子如今还经常吟诵王勃的诗句呢。”
“是啊,王勃不但是诗人,而且是个真真正正的人间仙客,不参半点儿假的。”
婉儿点头道:“王勃高才,做太子侍读当之无愧,这岂是奴婢所能比拟。”
武后看了婉儿一眼,无限惋惜地说:“只可惜他英年早逝,这仙客来凡间巡游了一番,定是深感无趣,故而又重返天庭去了。”见婉儿面色惊异,又说,“没错,听说他死了,意外溺水而亡。之后贤儿很是潦倒了一阵子,而且还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好在现在有你。王勃给贤儿当侍读的时候,贤儿还是沛王,正所谓近朱者赤,不过是那短短两年的时间,贤儿的各方面学识都有了出人意料地长进。若不是当年的一篇《檄英王鸡》(英王即李显)的小文,这人间仙客或许现在还在宫里安然无恙吧。”
“《檄英王鸡》是篇什么文章?”婉儿小心翼翼地问到。
那一日武后闲聊的兴致很高,便给婉儿细细讲来:“那一年宫里宫外的很多公子王孙都迷上了斗鸡,贤和显那时还小,自然也在此列,王勃为助兴写了一篇讨伐英王李显所持之鸡的战书,名为《檄英王鸡》,现在想来纯属小孩子胡闹,不料却开罪于当今圣上,圣上认为这是王勃被人指使,蓄意挑拨两个皇子之间的关系,故而将王勃贬出皇城,可惜啊。”
又是一个出言不慎的故事。婉儿正想着,武后又说:“你去给贤儿当侍读,我这儿可怎么办呢,近来有你在身旁,我当真轻松了许多,决云毕竟是掌事姑姑,无法寸步不离地在我这儿当值。不过是偶尔乏了,想添个帮手,却也能让圣上不安心至此!圣上是大善之人,担忧你在我这里一个不慎丢了性命,于是便收你做才人,贤儿也向着父亲,这点我心里明镜似的。”
婉儿刚要宽慰几句,却不料武后话锋一转道,“不过婉儿,一望便知你绝非凡俗女子,若不是那日贤儿来插一杠子,我知你必会选我这边。罢了!”她索性一甩手道:“你去吧!年轻人在一起研习诗书,是好事!我这边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诏你过来的。”
婉儿心里很感激太子,因为数日的相处,已让她谙熟了李贤的秉性,他真的正如太子妃房氏说的那样,外表高傲不羁但内心却很炽热,单论见闻学识,婉儿自知是做不了太子侍读的,但他那日却看出了自己对东宫里那些藏书的痴迷,故而才暗中成全她,让她有机会、有时间慢慢看个够。
仪凤三年九月初,大唐第一相士明崇俨巡游回到长安,带来了治疗困扰高宗李治已久的头疼眼疾的秘方。
明崇俨一向精通厌胜之术(“厌胜”最早见于《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的记载:“因巫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指的是一种巫术行为,后来则被引用在民间信仰上,转化为对禁忌事物的克制方法。厌胜之术又称左道、鬼道、巫蛊之术。简言之,就是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因其害甚烈,故被唐朝列为国禁)、相术和医术,并凭借此三项本领颇得帝后喜爱,甚至还赚得一个正谏大夫的官职。
这一次他以针灸、头顶拨络法为主,辅之以药物,竟让高宗李治日渐模糊的视线恢复了长久不见的清晰。武后大喜,高宗李治自己也有言曰:“治好眼疾,还我半条命哉!”
就这样,尽管他的特长被列为国禁,但明崇俨在宫里的地位却再一次平步青云。武后常常诏他入宫作法,并总要屏退左右,不许任何人打扰。
婉儿心里觉得很是奇怪,她实在想不通像武后那么一个头脑清明的人,如何会对一个术士的胡言乱语如此看重。固然他医术了得,可巫术相术之类则毕竟难保言之有物。
“自古帝王和谋权者之侧,都得有个把能通天眼的小妖。”李贤不以为意地说。他把明崇俨比作小妖,足见对他的厌恶。
不想说小妖,小妖即到。这一日,李贤正和婉儿在读书之余共一盘棋局,武后却领着明崇俨亲自登门了。
婉儿起身行礼,明崇俨也上前拜见太子,李贤很不情愿地起来,正眼都不给明崇俨一个:“母后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要事,诏孩儿去便是了。”
武后那日似乎心情大好,也不跟儿子计较这许多,只闻她道:“明卿曰今为吉良之日,特来为太子相面。贤儿,你只需站着不动便好,明卿,这会儿就开始吧。”
只见那明崇俨稍稍眯起双目,细细盯着李贤看了半晌方道:“太子容止端雅,状类太宗,大器也!”
李贤听了很是不屑,婉儿却长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武后听了,却并未见十分高兴,相反却有些忧心忡忡。她在东宫坐了一炷香的时间,没说几句话,只是照例和房氏闲聊了一会儿,甚至连茶都没饮一口,便匆匆地带着明崇俨走了。
大家都未注意到武后异样的神情,但只有一个人预感要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躲在假山后面的赵道生。
当晚,明崇俨有密函上奏武后,内容虽无从得知,但自那以后,武后与李贤本来得以缓和的关系又再度紧张起来。
不久后,宫里竟有流言说太子非武后亲生,而是武后的亲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又有传言说明崇俨相士那日得见李贤并无太子之相,却不便明说,只得密奏武后以表忠心。总而言之,这流言一时间扰得整个大明宫不得安宁,太子自是不当一回事的,因为他虽自知四个皇子中,他在面容上是最不像母后的,可连父皇都常说,他的性情最像母后年轻的时候。况且以他对母后的了解,她对背叛自己的人一向毫不留情,那么对敌人的孩子,是绝不可能宝贝般地抚养长大又立为太子的。
然而这些无所不在的谣言却让婉儿夜不能寐。
多日来她曾奔走于这对非比寻常的母子之间,她深知让这对母子之间产生间隙的不是小人的挑唆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他们彼此都太过强硬的个性,他们谁也不服输,谁也不肯退让,因此婉儿所担忧的,恰恰是李贤的毫不担忧。
一日,婉儿正在屋里整理书案,却闻屋外有人唤她:“婉儿姑娘可在里面?”
婉儿记得这声音,她推门而出,果然是赵道生。
“姑娘如今是太子爷跟前的额红人了啊,道生不知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书房自从姑娘入得,道生就入不得了。”
“你有事吗?”
“哟!上官姑娘行事不公啊,叫他张全儿大人,到了我这儿怎就连个称呼都不赏一个?”
婉儿刚要回屋关门,偏又被他拦下,只见赵道生看了看四下说:“道生此刻有要事讲与姑娘,可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还请姑娘随道生借一步说话。”
“婉儿还有事要做,恕不奉陪。”
“真是很要紧的事,事关东宫众人生死。”
无奈之下,婉儿只好随他来到一处偏殿。
赵道生一改方才的嬉皮笑脸,突然严肃道:“素闻婉儿姑娘天性韶警,聪慧过人,岂不闻太子府已大祸将至?”
“婉儿愚钝,太子府何祸之有?”话说到此处,婉儿都没有太上心。
赵道生上前一步说:“太子府之祸,在于太子小觑了那术士明崇俨,此人一日不除,太子府便一日不得安宁。”
“明崇俨那日分明当着天后的面说太子容止端雅,状类太宗……”
“最要命的也正是这句话,状类太宗!婉儿姑娘还不明白吗!当今太子可以像已故太子李弘那般儒雅,可以像历朝先帝那般贤能,甚至可以暂时监国、将所有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都也无妨,可一旦太子留心政要,那么他在政治上显露出的才干则是武后最不愿看到的。太宗皇帝是何许人也,姑娘应该比我清楚!武后卧榻之侧,岂容状类太宗者安睡?”
“可他们毕竟是母子……”
“母子又如何?!武后和已故太子李弘也是母子!明崇俨这等术士从中挑拨太子‘不堪承继’是小,若是无意中充当了谋权者的工具,那就对太子大为不利了。”
“那是传言……”
“没错!可有些传言是空穴来风乱人心,有些传言却是真!道生今日所言皆发自肺腑,之所以把这些说与姑娘,不只是因为知道姑娘还时常去武后那里帮助打点政务,更重要的是,道生知道婉儿姑娘虽是武后的人,但心向着太子!”
这赵道生冷眼旁观,倒是看得分明。
谋权者若真要对太子不利,那么就算没有明崇俨,也会有其他工具。婉儿心说。
经赵道生这么一提示,她发现自己是很不情愿往这方面细想的,她承蒙武后的知遇之恩无以为报,可在太子府一段时日与李贤的真心相对与相处,让她险些说服自己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如今放眼东宫最为重要的三大宫僚,虽然薛元超是个******,与太子并非同心同德,可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已升任宰相,太子右庶子早在头年年初就已坐定宰相的位置,面对宰相群体中东宫的势力渐长,武后感觉到空前的政治压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偏巧此时出来一个明崇俨,于是,一切顺理成章。
想到这里婉儿长叹了一口气:“此类事体我等是插不了手的,说来也无用!”不过,她心里对赵道生的印象却有了很大的改观——原来,他不是个只会狎昵惑主的户奴。
“杀了那明崇俨!”赵道生忽然说。
“不可!这样反而会打草惊蛇,引来更大的祸端!”
“杀了明崇俨,再给太子三年时间,其羽翼定能与武后相抗衡!到那个时候,就再无人敢借明崇俨的胡言乱语倒行逆施了。”
婉儿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赵道生,她发现自己今时今日才真正认识他。
“怎么?婉儿姑娘害怕了?或者,姑娘以为道生真跟那张泉儿一样只靠皮囊混饭,只会做女人做的事?”他又恢复了惯常的嬉皮笑脸,“不过,此时还需从长计议,今日说与姑娘,是想给姑娘提个醒儿,万一那术士明崇俨哪日被鬼神杀了,道生也定会随之遭遇不测,那时武后仅凭太子狎昵之事定不了太子的罪,要烦请姑娘尽全力周旋于二人之间,力保太子无恙了。”
这个形同鬼魅的赵道生托孤一般干脆利落地把话说完,便抬脚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