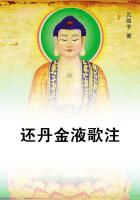“贺姐姐,这是在做什么?难道百草堂抓的草药还会有问题吗?”小姑娘好奇地问道。
贺疏雁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又不好将自己如此谨慎的原因对她和盘托出,只好微笑道:“倒不是怕他们的材料会有问题,实在是我对这些东西有点兴趣。见过药方,却未曾见过真正的草药是什么样,所以借此机会拿出来对比一下认一认罢了。”
想了想,又叮咛小姑娘道:“你这次回去,那什么太子良娣之事,暂时切莫与令尊令堂提起。”
没想到小姑娘却颇为懂事地点头道:“我知道。这背后道人短长之事还是少做为妙。”
贺疏雁顿时哭笑不得,摇头道:“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好妹妹,这事总有一日要向令尊令堂言及,只不过不是今日。”
“那却又是为何?”黄玲月顿时迷茫起来。
贺疏雁爱怜地摸了摸她的包包头道:“玲月妹妹,你想,这太子正妃未娶侧妃未定,却独独把太子良娣的名号给定了下来,这说明什么?”
“嗯,无媒苟合。”小姑娘一击掌惊叹道。
何书健被这小丫头的胆大也弄得一时无语,顿了顿,好笑道:“理是这个理,但话不是这么说,妹妹你这也太直白了。人家也未必就到了苟合这一地步。没准只是私底下两情相悦而已。”
“总之是不光彩的事情。”小姑娘点头道。
“总之……就是这个意思吧。”贺疏雁想了想,同意了黄玲月的说法。“而且此事宫内外并无人知晓,可见是极为隐密之事。既是阴私隐秘,那我们还是装作不知道为好,也可避免引祸上身。”
“好的,姐姐。我明白了。”黄玲月小姑娘极为受教道。
就这么两人返回贺府。贺疏雁亲自煎了药给江氏送去,便又和黄玲月在自己院中说笑玩耍了一番,见时辰不早,这才将执意不在贺家用晚膳的黄玲月送了出去。
贺方今日下朝回家倒是极晚,说是朝事太多,几乎来不及处理。待他堪堪踏入中矩院大门时,江氏已然命人将先前备好的晚膳热了又热。
“夫人真是辛苦了。”看着桌上热气腾腾色香味俱佳的饭菜,贺方由衷感叹道。
“妾不辛苦。”江氏一边替贺方更衣,一边摇了摇头道,只是语调却不似从前那般温婉,却别有一番凄楚。
“这是怎么了?”贺方敏锐地察觉了自己夫人的不同往常之处。
江氏苦笑了下,携贺方一同入座,道:“并无什么大事。老爷先吃了饭再说吧。”
贺方口中咀嚼着饭菜,眼神却忍不住四下搜索,希望能找出一星半点导致自己夫人失常的线索来。
没多时,他便发现这房中所有摆设一应都被换过,无论是花器茶具,还是窗帷灯幔,就连多宝阁上的所有古玩珍品都被全数换了下去。
这是大扫除了吗?贺方有些奇怪。近日里无年无节,这扫除之事却又是因何而起?
等再品尝着饭菜时,顿觉口味与往常又不一样,似乎是厨房里换了厨子的关系。贺方不由皱眉道:“今日可是换了厨娘,这味道竟然完全不同了。”
“老爷可是吃不得?”江氏蹙眉道。
“倒也未必,这味道与之前相比也不差,只是一时有些不习惯而已。”贺方摆了摆手,示意无事,只是心中疑云渐浓。今日里这家中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处处都透着古怪?
好容易二人吃完饭,便有侍女们上来收拾了碗筷、残肴下去。没多久红绡便捧着汤药入内而来,禀告道:“夫人是时候吃药了。”
吃药?贺方微惊,顿时便拽着江氏的手道:“夫人,可哪里不舒服?这吃的是什么药?”
江氏笑一笑,推开贺方的手,接过红绡手中药碗,垂首凝视那深黑的药液,似乎心中挣扎不已。
这氤氲冲鼻的药气熏得贺方有些头疼。再见到江氏如此情形,他心中不由更为惊疑不定。“夫人,这是怎么了?你有什么事便与为夫的说啊。”
江氏却看着他凄然一笑,猛然仰头将碗中汤药一饮而尽,顿时一张秀美的面庞被苦得皱成一团。
红绡连忙拿出怀中的蜜饯匣子,挑出一枚桃脯喂江氏含在嘴里。
好一会儿,江氏才缓了过来。她对着贺方温婉一笑,眼角也不知是因凄凉还是因药苦而微有泪痕。她道:“老爷不必担心,这药只是补身子的。”
说着她牵起贺方的手往内屋而去。一路走,一路将今日老夫人和她所言之事娓娓道来。
“真是胡闹!”贺方听了之后心中不免生气,只是从中兴风作浪的是他自己的娘亲,他并不好说什么,憋了半天还是终于忍不住吐出这四个字来。
“老爷请息怒,多亏后来雁姐儿的一番话,倒是改了老夫人的主意。”江氏柔柔地安慰道,便又将贺疏雁曾说过的话搬了出来。
听到自己女儿的说辞,贺方顿觉老怀大慰,总算这件事情没有任由贺老太君意志所摆布,而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也多亏了自己那人小鬼大的大女儿在这等险恶的境地里还能找出有效化解危机的话语来。
“可不是吗。”江氏也与有荣焉。只是她眉宇间的神色飞扬,还未及半刹便又低落下去,凄然道:“此事虽暂时得以推脱,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老爷毕竟不可膝下无子,雁姐儿也不能没有个兄弟。是以妾想着索性便找个好大夫来替妾看看,也争取好早日为老爷诞下麟儿。妾也算得是对得起贺家的列祖列宗了。”
听着自己结发之人的柔柔话语,贺方只觉心中郁沉难当,当下便抓住了江氏的手,反复摩挲良久,才叹了口气道:“夫人,你受委屈了。”
“妾不委屈。”江氏神色淡淡推开了贺方的手,折身在一边坐下后眉目间却首次露出了些微悲色。“老爷可知,妾这些年来竟一直被人以药物戕害。”
“夫人,你说什么?”贺方大惊。
江氏便将艾小太医的诊治结果一一复述了出来。贺方越听,面色越沉,听到最后不知不觉已紧紧捏着茶盏,连骨节都发白了。
“竟有此事……岂有此理!”贺方怒道。随后反应过来自家夫人之前为何会将屋内所有摆设尽数换过,不由得问道:“那夫人可曾查出什么端倪来?是谁做下此事?”
江氏看着他眉间微动,一霎那间悲色无限凄婉动人。她就这样以一种寻求帮助般的眼神看着贺方,只看得后者心中又软又痛。可是良久之后,江氏却还是扭开了头,轻叹了一声道:“没有。妾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没有查出来?”贺方疑惑地重复了那句话,眼中神色闪烁不定,一脸的将信将疑。
“夫人,你不是没有查出来,而是已经有了答案。”没多久后贺方摇了摇头,语气肯定的说道。他太了解自己的夫人,了解她的手腕和能力,也了解她的品行和性格,若是真的没有查出来,江氏必然不会是如今这副力图粉饰是非的样子。而是早就向他求援,让他帮着分析情况,推断答案。
而此刻江氏的神情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不是没有查出来,而是查到了不得的人身上。
而在这贺府一亩三分地里又有什么人对江氏这个主母来说是动不得,甚至连说都不敢说的呢?答案只有一个——贺老太君。
想通这处关节的贺方更是愧疚难当,他伸手去握着江氏的手长长叹了口气,却始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江氏见自己的丈夫洞悉了个中情由,倒也不曾暴跳如雷,指责自己是在污蔑老太君,而是一幅力图安慰自己的样子,心中早已酸楚难当,不知不觉就滚滚落下泪来。
“夫人。”贺方见状更是心痛,伸手替江氏搵却眼泪。江氏却赌气般扭开头去不做理会。“夫人。”何方心虚地又叫了他一声。
江氏终于按捺不住气道:“我自嫁入贺家又何曾做错过什么,对她又哪里不是毕恭毕敬?女子七出我犯过哪一条?就算我有错,尽可发落我,便是要休要弃,悉听尊便!可为什么却要断了我做母亲的可能呢?!”
“我究竟是有哪里对不住她?从进门起就仗着个杜姑娘对我百般刁难,如今也不肯正眼看我和雁姐儿一眼。这究竟还要我做到什么样子?是不是要把我的性命赔上,她才肯善罢甘休啊?!她怎么能这么狠!怎么能这么狠!”
贺方见自己素来强势开朗的妻子时刻哭得跟泪人一样,自己早已被这强烈的感情冲击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菱儿……”贺方喃喃地唤出了当年他们新婚前后柔情蜜意时的爱称,伸手揽住了自己妻子正在抽噎的肩膀。
“对不起,菱儿。这些事情……我没保护好你,这是我的错,真是对不起。”他一迭声地道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