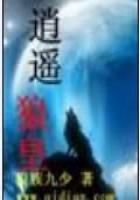贺疏雁微微摇了摇头:“晚了。我不是没给你机会,也不是没给你时间。最后最后了,你回报我的是什么?一个足以让我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陷阱!”
“贺凌韵,你应该知道,有句话叫做‘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你我之间虽然谈不上忠或不忠,但道理是相通的。”
“贺凌韵。你我姐妹之情,就到此为止吧。反正对你来说,也从来就没有过吧。”贺疏雁淡然道,转身向里间走去。“待我等归家,我自会向父亲母亲说明一切。对了。”她忽然站定了脚步,扭头看向低着头在地上沉默不语一味流泪的贺凌韵道:“庶女谋害嫡女,按律当斩。当然,鉴于你并未得手,这种情况或许能判轻些,大概也就是流个三五千里吧。”
“放心,还不到罪该万死的份上。”说完之前那句话,贺疏雁便脚步不停地往里间走去,同时最后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身后贺凌韵委顿在地,垂着头,咬着唇,神色莫辨。
天蒙蒙亮的时候,方铭琛已经在指挥着手下的兵将打扫战场了。
说是战场,却委实有些高看了那些流寇马匪。
原本以为不管怎么说,也是起码从三大营中“抽调”过来的部分人马,对付起来多少要耗费些力气,对于他这个初出茅庐始上战场的崭新将领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谁知,不知是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军营,导致沟通障碍,还是因为连日来的安逸销蚀了他们的武勇和斗志。总之,在方铭琛亲卫队的突袭之下,一干“马匪”顿时溃不成军,场面一时混乱至极。
有哭嚎的,有拿着武器却没头没脑乱窜的,也有趁乱搜刮财务伺机逃跑的,当然偶尔也有一两个真刀实枪和他们对着干上的,可惜双拳难敌四手,没几回合就被众人一起合力掀翻了。
算一算,从寅半时刻开始整队,到势如破竹地拿下这个“山寨”,竟然不过三刻钟。其中还是因为四处搜寻逃匪才耽误了这么些时候。
意识到这一点,方铭琛的眉头紧锁,似乎忧虑重重。
“我说,少爷,你这是什么表情?我们打了胜仗哎!”成元白从后面晃了上来,嘴里还是叼着根草,随着他说话的动作一翘一翘的。
他的身上颇有些狼狈,烟熏火燎的颜色有之,喷溅上去的血色有之,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看起来就很奇怪的污渍,也不知道是吃饭时洒下的肉汤,还是被山中果子、草叶染上的。
相比之下,虽然是率军突击在第一位,遭到反击也最猛最多的的方铭琛,除了轻甲上间或飞溅到的血痕,倒是比成元白干净整洁多了。
“伤亡如何?”方铭琛没理会下属的得意洋洋,开口问道。
“无人死亡,不过伤了的,倒有七八个兄弟。好在没人重伤,都是些皮肉伤罢了。”成元白轻飘飘地回答道。
方铭琛点了点头。
“我说,少爷,你刚才在愁什么?”说完正事,成元白的八卦之魂又熊熊燃烧起来。
方铭琛叹了口气,指了指面前忙忙碌碌的众人,道:“你记得我和你说过,这些所谓的马匪,可能来自三个不同的大营吧?”
“是啊,没错。”成元白点头道。
“太弱了。”方铭琛的语气有些沉重。
“嗯……啊?”成元白习惯性地点头之后,忽然反应过来自己上司说的到底是什么,顿时就愣住了。
方铭琛用关爱后进少年的眼神看了看成元白,叹气道:“甫一交锋,都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这么溃不成军了。”
“如果那三大营都是这样水准,我大熙,岌岌可危矣……”
这话题来得太庞大、太沉重,成元白摸了摸脖子,不怕死道:“也许是殿下多虑了。可能这些人也只是三大营中的乌合之众呢?”
方铭琛点了点头道:“但愿如此。”
两人并辔而行,成元白微微落后一个马头的距离。方铭琛看着手下人有条不紊地整理着马匪的尸体,并将还活着的按受伤轻重分别安置。
在经过中伤那一组的时候,方铭琛意外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粗豪声音:“小崽子,快给老子拿酒来!哎哟,疼死老子了!”
“你给我安分点!狗强盗,还当这里是你们山寨哪!在这耀武扬威的,小心小爷怼死你!”另一边有人喝骂道,听起来是方铭琛这边带的兵。
“狗强盗?!”那粗豪的声音发出一声怪笑,“爷爷我杀无根山匪的时候,孙子你还不知道在哪玩尿和泥呢!”
然后那个声音低了下去,似乎喃喃自语了什么,最终湮于沉默。
方铭琛驻了马。这个声音他是不会认错的,正是昨日他和成元白潜入山寨马厩时,遇到的那两人之一,不过当时只知道另一个叫老八,如今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一个倒是不曾听到名姓。
这倒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人所提及的“杀无根山匪”一事,委实让方铭琛不得不留意。
方铭琛清楚地记得,无根山剿匪是发生在距今近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那边的山贼,由于和官府勾结,是以日渐坐大,终成一患。
其实无根山左近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四处隳突劫掠,民众苦不堪言。等到被那些山匪喂饱了的官府后知后觉地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他们已经再无能将山匪控制住了。
距离无根山最近的县衙甚至成了山匪们的血洗目标,而且毫无半点反抗能力。山匪们甚至在血洗县衙之后,登堂入室,自己组了一套班子,各色职务一应俱全,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县衙里当上了“官老爷”,横征暴敛,几乎闹得那一片民不聊生。
这件事终于被察觉蹊跷的御史冒险报到了中央。皇帝看到奏章一时震怒,雷厉风行地点了大将,带上兵马就出发去剿匪了。
虽然是大将和正规军,但是在无根山那种地势险峻之处,却委实发挥不出原本战力的一半。所以当时当大军打到无根山脚下,收复了之前被山匪强占的县衙之后,就迟迟无法再进一步了。
而那些山匪,打了几场硬仗之后便整体龟缩到了无根山之中,倒也没受到什么损失。可是这么一来,仗就难打了。而领军的将军出发前又是被皇帝下了死命令的,这一仗,只许大捷。是以,也只好带着军队驻扎在了无根山下,以此为营,一点点,一寸寸地向山中推进。
这一场仗,打了整整八个月。从春暖花开,打到了万木萧条,总算把所有山匪一一镇压,再无遗漏。只是官兵这里,也损失惨重。
那些被迫在自己不熟悉的地势环境里厮杀的士兵,竟有半数左右是因为不熟悉环境而遭遇跌落山崖、吸入瘴气、陷入沼泽、被毒蛇啮咬等等致命状况而减员,而山匪更是和他们玩起了游击战,设陷阱、打埋伏,一时间风声鹤唳杯弓蛇影,众士兵哪怕步步为营,也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落入了那些圈套,从而从此与无根山同在。
这一仗胜得如此惨烈,以至于那位将军班师回朝后,朝野上下为之喝彩颂功的人一个都没,皇帝也只是草草嘉奖两句,赏赐了些金银俗物,也就就此作罢。那位将军也自知不值得被喝彩歌颂,在领了赏赐之后,便将那些东西统统变卖为金银,随后尽数用于对那场战斗的伤亡者的补助之中。
也正因为这种独特性——大熙开朝以来的第一遭,也是仅有的那么一次——才让那时候年纪尚幼的方铭琛对此印象深刻。
如果说,那个粗豪的汉子所言不假,他确实参加了那场无根山剿匪的话,能从那张战争中活下来,也确实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可是如此,也就证明了他确实是军中人——当年无根山剿匪一仗打完,这些幸存下来,又有着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可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哪家军营不想弄一两个回去?参谋也好,练兵也罢,这种经验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那既然如此,这人又是这么会在这里出现的呢?十年来,凭着“无根山剿匪凯旋者”的金色光环加持,怎么着,也该升上去了吧?怎么会被“抽调”到这里来冒充马匪?
这事越想越蹊跷,说不准,还真能有些答案落在这个粗豪的汉子身上。
这念头从脑中闪过,方铭琛当下一拨马头,就往飘出那些对话的地方走去。
他所要去的地方是个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茅草屋,只怕是这些临时马匪们随便搭起来落几天脚的。看起来手艺有限,茅草屋四面透风,是以那些声音才能如此清晰地传到外面来,被方铭绝听个正着。
而也因此,他转变方向的动作,也被在里面保持警惕时刻注意着外面动静的哨兵发现了——他才到门前,就有士兵从里面迎出来,为他执住马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