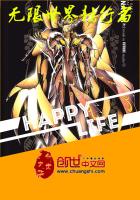短短一瞥,我发现驾驶座上的人左耳留着长鬓,同时立刻认出来他藏在帽沿之下的那双眼睛。
他是张横。
我以为他还在船上,又或者和船员们一起去什么喝酒之类的地方。
不知道他认没认出我来,但在刚刚那一瞥之后,张横并没有其他的动作,而是重新把帽沿拉低。
他是张横?
可能是因为自己痛到极点的缘故,我转眼朝下的目光发现我弄错了之前刀疤脸从我的皮包中扔下来的针剂颜色。
那并不是蓝色,而是透明的液体。
而且我想起自己在泄压阀通道中逃生的时候给自己注射的是绿色针剂。
我意识到刚刚连“极乐弥留”的颜色都没分辨出来的我现在很可能认错了人。
认错了么?
“枝那狗!舒服么?”刀疤脸仇视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其实和我仇视他们一样,所以我对他怎么称呼我并不感到奇怪,他现在扯着我的下巴,把我的脸强行地面对着他那对靠在一起,近乎于是个盲人一样的白眼球。
舒服……真谈不上,但我有些意外,因为现在真实的感觉竟然不是疼。
我发力紧了紧脚趾头,竟然发现腿脚的知觉没有因为刚刚炸裂般的疼痛遭遇而失去。
现在难道说不是应该因为痛楚而昏厥么?我不知道造成这样的是什么缘由,但我现在还能活动,虽然还被绑着,感觉上也并不是多舒坦。
除了我依然不能有什么大动作,还和先前一样处于任人宰割的之外,胸口的沉闷感觉渐渐开始减弱,我的意识反而比被刀疤脸注射之前还要清晰一些。
这算是个小小的好消息,不过如果要继续挨打的话,就要算坏消息。
啪!啪!啪!
刀疤脸凑近我之后,不停地抽打着我的脑袋。
同时的,我还听到了刀疤脸的大声嚷嚷。
“八格牙路!蟑螂一样的枝那人!居然还没有死!?”
如同我惊讶这红日烧饼的民族居然在他的话里面还会用汉语副词“居然”一样,刀疤脸这时也表达了足够的惊诧。
似乎是我还活着这个事实,诧异到了他,因为按照他所掌握到的结果,我被注射了那么多之后,现在应该死透。
我很想骂街几句,然后想象自己像绿巨人一样挣脱这个绳子,将刀疤脸暴打几十遍。
但我的愤怒完全与被揍的滋味无关,刀疤脸这时拳脚带给我的疼痛感其实远远比不上之前我所感受到药效疯狂的那一段时间。
之所以这么能调动出我的怒火,是因为此时的我反抗不能。
“我会自己找出来的!到时就将你们全部干掉!”刀疤脸给自己戴上了手套,我不知道他又要干嘛,然后继续听到他说道,“到时我会成为最高的董事!合适的机会就要把你们枝那人全部干掉……一个也不留……”
刀疤脸是二战遗留至今的人么……我不禁有些吐槽他哪来这样的自信和仇恨,要说到他口中的枝那人恩怨。
红烧饼岛上的狂热分子才是罪魁祸首,由此我想到了那帮人死不认账的脸皮还真是厚得令人发指。
然后刀疤脸在我的眼前,把脸皮重新“PS”了回去,他的斗鸡眼形态消失,再次成为了刀疤脸的模样。
这……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他撕下那层面皮只是为了用仿佛可以打破吉尼斯斗鸡眼程度的记录来逗我发笑么……不过,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都是你们这些应该被灭族的枝那人!还要让我戴这东西……跟你们这些枝那人多说一句话,都让我作呕!”刀疤脸站在他让我感觉诡异的立场,表达的是仿佛与我们不共戴天……简直了,我要是不读一点历史,还真以为过去我们怎么他们“伟大”的红日烧饼岛了,说不定我还会因此而自责。
然后我就看到他把那道刀疤贴了回去,继续说出来的内容,可能已经忽略了我的存在,只是对他自己说的。
“这张应该再够8个小时……速战速决……神风万岁!”
我猜刀疤脸一定在国内待的时间很长,连自言自语下意识说出来的都是普通话。
也是幸亏他说的这句普通话,我才明白刀疤脸之所以把面皮撕下来并不是为了引我发笑,而是那层仿佛一次性面膜一样的面皮只能持续8个小时。
先前在车里的时候,大概是前一张面皮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所以刀疤脸不得不换。
这似乎是告诉了我,他已经假扮真正的刀疤脸至少已经有了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刀疤脸整理好衣服,从衣服里掏出了一把枪。
他看起来是发现确实从我这儿问不出他想要的内容,所以,这是想干掉我么?
想到这里之后,我就有些惊慌。
不过好在事态没立刻发展到我刚刚猜测的那一步。
车停了。
“找个地方干掉他!等我回来,不想看到这个枝那人还活着!”刀疤脸把他手里的枪扔到了前座,他在吩咐开车的下属警员。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而且这个警员当然也是个冒牌的下属。
“我把讨厌的苍蝇们带走,告诉他们说凶手的伤势恶化,现在已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抓紧时间……拜托了……”
前座的刀疤脸帮凶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帽沿之下的脸暂时我还是看不清。
刀疤脸先前还表现得像个媒体交际花,看来讨厌才是他真实的想法。
“苍蝇”的比喻一定是说的穷追不舍的记者们,这会说抓紧时间的意思是要他的帮凶下属尽快处理了我。
似乎对于我能告诉他什么信息已经完全不重要,而且老实说,刀疤脸并没有好好地对我逼供,他一点都不专业,耐心全无。
可能折磨我一阵再干掉我,才是这个变态想干的事情。
我的脑海中忽然就联想到了真正的刀疤脸警员头头,他可能已经被这个冒牌的刀疤脸给折磨了一遍然后英勇就义了。
那些记者和媒体比我们要先到了酒店。
大概是都知道我们要来酒店,这边媒体的人数比车祸现场可能多上一倍还不止。
车窗上能看到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正在奋力拦着记者。
从酒店一来一去的折腾之后,这个时间点差不多也应该快凌晨三点。
这里和车祸现场还是不太一样,围观的好事人群基本没有。
一来时间上已经很晚,这个时候能赶来看热闹的人可能也只有酒吧等夜场里下班的处于激素ing作用中的男女们。
二来酒店所处的位置附近没那么多的居民楼,离得最近的是个很开阔的公园和许多湿地类景观。
所以在酒店的,基本上除了报导的媒体根本也没什么其他人。
这样仿佛是一场露天发布会的场景,我实在是不懂刀疤脸在玩什么游戏。
刚刚在车上明明还想偷偷处理了我,猥琐得就像是恨不得直接把我拉到坟场就地埋了。
而我目睹到酒店现场的这阵势却好像瞬间反了过来,仿佛是要铁了心把事情闹大的意思么……我不禁这么在心里吐槽一句的同时,发现自己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感觉到剧烈疼痛,虽然这段时间并不长。
但仍然让我意识到,刀疤脸给我注射的针剂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把我的肌肉给融化,与其纠结它出了什么问题,我不如现在做点什么。
所以我开始尝试去挣脱。
若不然,就是坐以待毙。
只是由于手脚上的力道不济,所以挣扎的效果一开始并不好,目前我仍旧是被绳索禁锢着的状态。
刀疤脸并没有在车停了之后就立刻下去,他等其他警员把媒体拦在外面,首先拉起警戒黄线之后,才开门下车。
我听到刀疤脸在下车之前似乎是对周围的情况不满意,但他这回说的是他的母语,我没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仅仅从他的语气程度上猜测,也许是因为现场的“苍蝇”太多。
随着车门一开,迎着刀疤脸的就是一顿咔咔咔的闪光灯,好莱坞的红地毯也不过如此了吧……我顿时觉得刀疤脸其实只少一条通往酒店大门的红地毯。
而且他和演员做的工作的确还挺像,“化妆”然后接受闪光灯的照射。
闪光灯和记者瞄准的不仅仅是刀疤脸,他们似乎还在等我。
然后我看到刀疤脸在十几米开外的远处,对着众闪光灯们不知说了什么,又再指指酒店的方向。
原来还盯着我这边的记者,也转移了目光。
参考编鬼话的人一定会听信鬼话,没有鬼话就努力制造鬼话的行业准则。
记者媒体们肯定是相信了刀疤脸所说的,“我已经处在去医院的路上”。
是去坟场的路上还差不多……我看了眼离我越来越远的刀疤脸那边,然后把目光继续转向车前座一言不发的刀疤脸帮凶。
我已经感觉到身体的异样,它似乎并没有因为失血过多而让我永远失去行动力。
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我能感觉出来我的行动力在一点点恢复,虽然很诡异,我也不知道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我所知道的是这个身体从我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再属于正常的行列,而且我想起在蛇昙沟逃亡的过程里,纳兰曾对我的举动。我们的手“绑”在一起过,也许我身体里已经掺杂了纳兰的血。
我这么猜测着,而且一提到纳兰,我觉得我瞬间就可以接受任何超乎寻常的怪异表象。
因为还有什么能比纳兰亭更怪异的么?
没有。
我盯着车前座,生怕被他发觉,好在他把车窗打开了,正在看着外面。
于是我趁着他的注意力在外面,正在努力尝试靠近那些被刀疤脸扔在后座的“手术刀”。
它们是纳兰亭让我带出来的,而且我已经见识过它的锋利。
如果我能摸到散落在车里的任意一把,我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断这个绳索。
啊!砰!
车窗外混杂着的尖叫声和枪声,打断了我的注意力。
我扭头看向车窗外面找到持续不断的声音出处,是来自刀疤脸附近。
不知为何刀疤脸和两三个警员现在正躲在一辆警车的后面,与他们对面十几个警员枪战了起来。
两边后来都有人员的补充,但对面增加的警员是刀疤脸这边的数倍。
如果一直射下去没人投降的话,刀疤脸被打成马蜂窝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伴随着子弹打击金属车身和四周玻璃陶瓷等等的动静,现场很快乱作了一团。
除去酒店的人员开始跑得不见踪影,记者和媒体也开始了逃散,但这些人似乎敬业精神尤其突出。
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用生命去抢头条独家,他们不断反复一个动作。
后退几步然后又迎上去,麻溜动作的同时还不忘咔咔咔地拍几张。
怎么说怼就怼起来了……又不是在酒店拍警匪枪战……我忍不住吐槽一句,然后意识到了事态的重点。
是警员在和警员开枪。
我知道刀疤脸那边一定是假警员,现在他们开战了,说明那个自信狂妄的红烧饼岛人伪装的刀疤脸已经被人识破。
而且刀疤脸很快前后都有警员,他带着他的手下被包围了。
“哼!”
就在这阵混乱枪战发生变得激烈之后的没几秒,所有车窗被关上。
在相比外面嘈杂的****声更显得安静的警车内,有一声不屑而轻蔑的冷哼传进了我的耳朵。
来自车前座的刀疤脸帮凶。
他压了压帽沿,同时发动了车子。
我以为他会冲进去枪林弹雨中,一脚踢开车门,然后把刀疤脸救走。
毕竟在我看来是帮凶,这么做很合情合理。
不过他的行为并不如我的想象猜测。
车是发动了,但他只是后退着离开了酒店,把刀疤脸丢在了那片混乱之中。
一言不合就背叛么?真是醉了。
但那也许正是刀疤脸之前安排好的撤离,所以我心里这句询问“张横?”的话还没有立刻说出口。
我仰躺在车后座继续观望,手里已经摸到了其中一把“手术刀”。
不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预想的坏打算到底会有多坏。
这辆车逃跑起来的速度不快,我从车体外一侧的后视镜里,还看到了越来越近的车灯光。
灯光还不止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