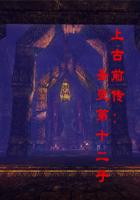梅香倚在自家的门楼子前,眼巴巴地看着不远处的秀秀和福儿:童养媳带着她的小丈夫在玩绷绷绳呢。秀秀仍旧穿着那件紫花布小褂儿和蓝裤子,辫梢上扎根红头绳。她好像只有这一身裤褂,前天是它,今天还是它。梅香心里奇怪,裁缝家有那么多的七彩布料,怎么不给秀秀多做两身漂亮衣裳呢?倒是福儿,今天换上了一身很洋气的学生装:白洋布的敞领子衬衫,黑色灯芯绒的背带西裤。好笑的是,背带裤中间开道口子变成了开裆裤,好笑死个人!
梅香心里非常不服气,福儿才五岁,他凭什么穿上学生装?
秀秀的那双手细长细长的,灵巧得像两尾游动在水里的鱼,那条绷绷绳绕在她手指上,中指一挑,食指再一挑,直线变成了斜线,变魔术一样地神。
“福儿,把手伸过来,挑这根线。”秀秀腾不出手,努起嘴,用下巴指点着,告诉福儿往下应该怎么做。
福儿远比不上秀秀那么灵,他竖着一根胖乎乎的手指头去勾那根线,才勾到指尖上,线就被他弄乱了,搅成一团麻。福儿马上跺脚,要哭。
“再来再来!看我绷个格子花。”秀秀慌忙哄着他。
手指漂亮地飞舞,啪啪几下子,一个新花样又绷在秀秀手上。“福儿看看,像什么?”
“烧饼。”福儿笑嘻嘻地,一汪亮晶晶的口水聚在嘴角,欲滴不滴。
可是任凭哪个花样过到他手上,一准要乱,不是掉了一个头,就是缠住了解不开。
秀秀不着急,倚在门楼子边上偷看的梅香倒急得直咬牙。蠢福儿!笨福儿!你不会绷绷绳你还玩什么玩?滚到一边淌你的口水吧!梅香恨不得腆了脸子走过去,替下福儿,自己跟秀秀玩个痛快。
可是梅香没有往前走一步。好歹她也是石家的大小姐,娘无数次关照过,大小姐有大小姐的规矩,随随便便的陌生人不能上去搭讪,那是不合礼数的事。梅香心里痒痒的,却把脚步子管得很牢,钉在地上一动没有动。
余妈买菜回来,看见巷子里的福儿,没了好脸色,故意拉长着声音:“梅香啊,没家教的小孩子你可不能搭理啊,跟好人学好人,跟着乌龟你会学出王八样!”
一边说,一边抓起梅香的胳膊,连拖带拉地弄进家门。
梅香又好气又好笑:余妈跟裁缝娘子斗气,关福儿什么事情呢?他还是个鼻涕娃娃嘛。再说了,裁缝娘子又不在跟前,余妈说了是白说,骂了也是白骂,好笑哦。
余妈给娘带来了外面纷传的消息:奉军的张学良和直系的吴佩孚在热河一带开战了,双方动了炮,还动了军舰和飞机。
“军舰是什么东西?飞机又是什么东西?”余妈很好奇。
“总是比枪炮更厉害的吧?”娘猜测。
“这下子仗要打大了。不说军舰飞机吧,光是拿炮子儿打人,一打就是一大片呢,多厚的城墙都挡不住。哎哟,也不知道会不会打到青阳来?”
“那倒不至于。”娘帮着从菜篮子里往外拿东西:活蹦乱跳的青虾,三指宽的一刀五花肉,红艳艳的苋菜,鼓着脸颊的青蚕豆。“热河离青阳远着呢,隔了黄河,还隔了淮河,军队要过来怕是不容易。”
买菜本来是厨子老五叔的事,昨日老五叔的儿子娶媳妇,娘许了他回家喝喜酒,今天这差事就让余妈代劳了。
余妈小心翼翼托起篮子里的一块嫩豆腐,放进白瓷碗。“阿弥陀佛,不打仗就好。”她说,“只要有太平日子过,吃糠咽菜都是香啊。”
娘抿着嘴笑:“真到吃糠咽菜的时候,怕又不好了。”
余妈点头:“可不是,现如今只要有掏钱的事,个个都喊贵。米,面,油,柴,哪样不涨价?还有呢,说是今年南边北边轮着发大水,上到天津卫,下到湖南广东,淹死的人成千上万。今天菜市上就见着一个小姑娘,身上插了根草标,听人讲是北方逃荒过来的,娘老子养不活了,要卖了她。再有件事……”她鬼头鬼脑凑近娘的耳朵:“城东万盛行家的小儿子,昨儿夜里被土匪绑票了……”
娘煞白了脸,下意识地瞟一眼梅香,打断余妈的话:“这种事,不能瞎传的。”
余妈领悟了,赶紧说:“那当然,万盛行的老板太招摇,他自找。我们是规矩过日子的人家,不一样。”
梅香走上前翻她的菜篮子:“余妈你买猫鱼了吗?”
“买啦买啦,余妈还能忘了你的事?”她从篮子角落里翻出一个荷叶包,打开,是几条翘嘴小鲹鱼,三寸长,一指宽,银光灿灿,很新鲜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卖鱼的小把戏要了我一个铜板。啧啧,猫食倒比人食贵。”余妈唠叨着。
梅香接过荷叶包,转身奔出门。她要赶到呆小二的家,给黄黄做饭去。
梅香从来没有给爹和娘做过饭,如今她的肩上却担了责任了,要给坐月子的黄黄做饭。她对自己要求高,每天做的饭都不重样:昨天是煮鱼,前天是烤鱼,再前天是油煎鱼……她会仔细地刮鱼鳞,剖开鱼肚皮,小心地掏出鱼内脏,在水里漂干净,每一道工序都照着厨子老五叔的一套来。她还从家里带出来各种调料,给黄黄尝试鱼的各种口味:甜的、咸的、五香的、麻辣的。黄黄勉强可以接受甜,但是绝对不喜欢辣,昨天她往猫食锅里扔了一根红辣椒,才小手指头那么大吧,结果黄黄只用鼻子嗅一嗅,就打一个大喷嚏,活像见着了鬼一样,尾巴夹着,落荒而逃,逃出老远之后,返身坐下,委屈地看梅香,不知道它犯了什么错误,惹得主人用辣椒惩罚它。
鱼汤已经辣了,把鱼儿捞出来重煮都不行了。还是呆小二拿出两个铜子,到赵疤眼的肉铺子里割了酒盅大一块猪肝,回来煮了,剁碎,拌进米饭,黄黄才不至断顿。
梅香就有点羞愧,觉得自己对待黄黄的态度不及呆小二,她没有真正地把黄黄当成小妈妈,尊重它,尽心尽意地伺候它。
所以,她今天一早就恭恭敬敬地向余妈讨教了鱼汤的做法。她要把荷叶包里的小鱼洗干净,放上两滴油,再放进两颗盐,文火煨出雪白的、浓得发稠的汤。
不知道是被北方打仗的消息吓着了,还是被土匪绑票的事情弄懵了,反正梅香出门时,巷子里难得的冷清着,从东头到西头,只有麻雀在地上蹦来蹦去地跳,不见一个人影儿。太阳才不过升到树梢那么高,阳光斜射,把一条巷子照得半边明半边阴,阴阳交错处,有一只酱黄色的蝴蝶翩翩飞舞着,穿梭在光线两边,翅膀时亮时暗,仿佛一个调皮的精灵故意捉弄着阳光,又仿佛阳光故意地逗它的乐子。
梅香只顾看那只蝴蝶,路过井台时,没有留意井台上的人,忽然听见“啊呀”的一声叫,一扭头,才发现是秀秀。
秀秀跪在井口边,手扒着灰色粗砂石的井筒子,脑袋扎下去,一个劲地往里面看。她那条大辫子从背侧滑到了腋下,晃荡在腰间,辫梢的红头绳像一朵小火苗,一下子跳进了梅香的眼睛里。
井底下有什么?死孩子,还是金蛤蟆?梅香很好奇,忍不住地拐上井台,也跪下,跟秀秀脑袋对着脑袋地往下看。
井底下黑咕隆咚。一股清凉的水气扑上来,带着陈腐的青苔味,腥甜的污泥味。井水微微荡漾,撞到井壁上,有沉闷的啪啪响。可是梅香都快要把脑袋扎进井里了,还是什么都看不着。
“到底是什么呀?”她抬头问秀秀。
“吊桶掉井里了。”秀秀哭丧着脸,害怕得声音都发了抖。
梅香有点失望:“是吊桶啊!我还以为你看见有人淹死了呢。”
“衣服才洗了一半。我婆婆要打我的。”
梅香扭头看井台上的那个洗衣盆。盆子几乎有澡盆那么大,堆尖的一盆衣服,还有搓衣板、捶衣棒、装衣服的竹筐、放皂角和石碱的小石钵子,七七八八一堆东西,难为秀秀一样一样从家里搬到井台上。
可怜的秀秀,她把小她几岁的梅香当成了救星,眼巴巴地讨主意:“咋办啊?咋办啊?”
她说话带着南乡一带的口音,很急促,仿佛有一条狗在后面追着她,她必须把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
梅香很享受有人把她当大人看,故意放慢语气:“没事啊,呆小二马上要来挑水了,他会帮你捞吊桶。他有个长钩子,专门捞吊桶用的。”
“我没钱。”秀秀可怜巴巴地卷着衣角。
“他不收钱。”
“真的不收钱?”秀秀不放心。
“我不会骗你噢。”
秀秀松一口气,肩膀塌下去,人都要瘫了一样。不过一只吊桶落了水,差点儿把她为难死。可是她马上又不安起来,转头四顾:“他什么时候来呢?我这会儿就要用水哦,迟了回家,我婆婆……”
梅香热心热肠:“那我回家拿个吊桶来,你先用着。”
梅香说完扭头要跑,秀秀连忙拉住了她:“别,可不能这么麻烦你,我还是等等吧。”
秀秀伸手拉梅香时,宽大的袖子滑到肘弯处,露出小臂上的几处伤痕,深一道浅一道,蚯蚓一样爬着,有的已经结了疤,有的还在瘀着血,结疤的紫黑色,瘀着血的深红色。
梅香心里轻轻地一哆嗦。她看见过秀秀跪搓板,不知道她还要挨这样的打。把胳膊打成这模样,要下多狠的手啊!难怪秀秀掉了一只吊桶会怕得没了魂。
秀秀低着头,飞快地把衣袖掳下来。伤疤和瘀血太难看了,她不要让梅香看。
一时间,井台上很安静,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心里都有很多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几岁?”过了一会儿,梅香打破沉默,问秀秀。
“十二。你呢?”
“我八岁。我叫梅香。”
“梅香。”秀秀轻声念着这个名字。
“我就住你家隔壁。爬墙头的时候,我看见过你。”梅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青砖雕花的大门楼。
“我晓得了,你是石家的大小姐。”秀秀龇牙一笑。她长着两颗石榴籽儿样的小虎牙,笑起来的时候也像石榴咧了嘴。
梅香还有很多话要问。寂寞中的两个小姑娘,忽然碰到了彼此,有心贴心的快乐。可是这时候呆小二挑着水桶担子过来了,梅香赶忙替秀秀办正事。
“小二,要用用你的长钩子。”梅香朝井口下指了指。
呆小二马上明白了是什么事,嘴一咧,显得很乐意。每逢井台上有人需要他帮忙捞吊桶,他总是眉开眼笑,忙乎得一头劲。
放下水桶,他先走近井台,低头往水下望一望,大概计算着这一天的水深浅吧。然后他转身,大步走进井台南边的杂树林,再出来时,手里变戏法样地多了一根丈多长的毛竹钩。原来他把长钩子藏到草丛里了。他举着钩子,大手在竹竿上从头到尾地胡噜一遍,噜去了草屑和泥巴。然后他在井口上探着身,一把一把地将长钩子放下去。他的动作很慢,很小心,屏着一口气,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把井下的吊桶惊着了,再也捞不上来了。因为专心,他嘴角的咬肌鼓得像两个梆硬的疙瘩块,鼻孔一张一合,脖颈上的青筋一条条地暴着,根根都有梅香的小手指头那么粗。
一只手忽然抓住了梅香的胳膊肘,捏得她生疼。那是秀秀。这回秀秀不是替自己担心了,她替呆小二担心:这么大个人,捏着根长竹竿,要从看不见的井底下捞出一只小吊桶,难为人哦。
梅香反过来捅了捅秀秀,意思让她放心。
呆小二攥着毛竹竿,沿着井口,直直地、慢慢地转了一圈。木头吊桶掉下去,都是在水面上侧身飘浮的,要是铁钩子碰上了,会有“笃”的一声响,呆小二的手里也会有感觉。这一圈钩子好像是放空了,因为呆小二的嘴巴努得更厉害,差不多快要歪到耳根了。梅香知道,呆小二只要一着急,脸上总是这副怪模样。
“你往这边!再往那边!”梅香站到呆小二身边,果断地指挥着他。
呆小二是真听话,梅香指到哪儿,他就把长钩子小心地伸到哪儿。他一点儿都没有因为梅香是个小孩子而轻慢了她,忽略了她。
忽然,井底下“笃”的一声响,闷闷地,带着潮湿井壁的回声。呆小二手里的竹竿停下来,不动了。他抬起头,朝着梅香嘿的
一声笑。
“勾到了?”梅香问他。
他摇摇头,仍旧嘿嘿地笑。
“勾住,捞上来!”梅香发令。
他好像就是等着这句话,梅香才说完,他已经娴熟地操作长竹竿,几下子一摆弄,一把一把地捞起了裁缝家的木吊桶。
吊桶里几乎没有水。这是技术。如果连水带桶往上捞,太重,半道上很可能拽着铁钩子一起掉下去。
“好了。”梅香接过吊桶,转手交给秀秀,又回身拍拍呆小二的胳膊。“挑水去吧。”
“就这么呀?”秀秀手拿着湿淋淋的吊桶发着愣。
“什么就这么?”梅香被她问得有点懵。
“一个谢字没说,就这么了?”
梅香大包大揽地:“那还要怎么?你想怎么谢呀?”
秀秀脸一红,眼睛瞥着呆小二,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呆小二弯了腰,撅着屁股,忙着用他自己的大吊桶一桶一桶地打水。他仿佛已经忘了刚刚做过的事。
梅香返身去拿搁在井台上的荷叶包。太阳太厉害了,荷叶都晒得有点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