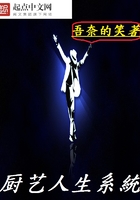说是一罐就好,但善解人意的雷冰是如此会劝酒,又有着丰富的阅历与人生经验可供分享,不知不觉间陆菲喝下一罐又一罐,转眼房间的一角就堆满了空罐头。
说到房间,她原以为雷冰的房间该是黑白色调的,到处透出高贵冷艳的气息,或者是中性并且向男性角度倾斜,充满干练感觉的风格。没想到这儿普普通通,就是个宾馆标准间,豪华,但是没有个性。
除了娜塔莎之外,雷冰是她见过酒量最可怕的人。那酒不知是多少度数,十几罐下去,陆菲还算清醒,但是胃里像有团火在烧,脑袋也沉重了少许。在桑南岛连灌五整瓶伏特加都没辙感觉,恐怕不能再喝下去了,她担心地想,牢牢记着还有更重要的事。可雷冰面不改色,一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她的冰箱里面有多到可以用来洗澡的啤酒,一罐又一罐怎么也拿不完。
“我们,”挂钟显示已经十一点了,陆菲犹犹豫豫地开口,“是不是应该……”
“当然,差不多到时间了,”雷冰笑道,“不等到这个钟点,我的法子没用哦。”
“和时间有关系?好神奇。”
“当然,世上的一切都与时间有关。想让刘弈队长知道你有多想他,对不对?”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陆菲听到这个问题没有再脸红,而是用力点了点头:“我真的很想他。可是要我做什么呢?上次的实验,我和他就隔着一道屏风,也没能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现在隔的可不是一道屏风了,”她向着南方望去,看到的只有房间的墙壁,“姐姐,你的办法……会有用吧?”
“啊呀,这法子和你说的一样,可神奇了。有用或者没用,这个要看你有多努力,而不是问我喽。”
“努力……?”
“没错,努力。比世上大多数事情要公平得多,付出就一定有回报,只看你愿意付出多少。”
地下通道高耸的墙壁在脑中浮现。“很多。非常多。”
雷冰走向衣柜,取出一个箱子,当着陆菲的面打开其中一半。几个支架,几个圆环,收束整齐的电线,看着像是佩戴在身上的,有点像是动力甲的前身、单兵外骨骼的框架。大概又是徐天教授的研究成果吧?
箱子的另外一半紧紧闭合,她看到雷冰捣鼓几下,一组怪异的天线便从箱中升起。
“说实话,刚才我一直在犹豫。”雷冰注视着天线的顶端,她脸上总是带着的那种对一切都了然于心的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与认真。
“犹豫什么?”
“……算了,一点小事,将来有机会再告诉你好了。你的生日是10月24日吧?年份是哪一年呢?”
“是呀。2003年。”她怎么知道的?陆菲暗暗纳闷。
“周岁才十五呀,”雷冰突然惆怅起来,“不管是何年代,这都相当了不起。好吧,”她举起支架,“坐到椅子上去,那边那张,带扶手的。趁这时候,想想要对刘弈队长说些什么话比较好。”
陆菲乖乖照办。
雷冰把支架和圆环戴在她全身各处,很轻巧,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这令她想起在TianchaoJoy上玩过的游戏。联想箱子上的天线,凭着仅有的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女孩猜想,是不是这东西可以把想法像广播一样发射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等等,那样的话,岂不是人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吗?那些话只能对刘弈一个人说,和陶盈商量她都觉得害羞,遑论其他人。
不过这些只是自个的猜测罢了,徐天教授弄出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仅仅初中毕业的自己能搞懂的。
没有胡思乱想多久,雷冰完成了设备的安装,坐到电脑前一手支颚,一手握住鼠标,好半晌没有动静。突然她冒出了一句话:“面临困难的选择时作出决定和执行这个决定,不知道何者更加残酷?”
什么意思?
雷冰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纠结到了极点。陆菲默不作声地看着她,目光也随之来来回回。第二十次从墙边折返,她径直走来,双手按住陆菲肩头:“你……想不想……见到自己的……”
陆菲的双眼因诧异而瞪大:“我爸爸?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想见我爸爸?”
“我说什么了吗?”雷冰同样瞪着她,满脸不可思议,“我想说的是‘自己的恋人’,你怎么联想到爸爸上去了?啊我明白了,你们两个滚床单的时候,他要你这样叫他?”
“没有,我没那样叫过他。爸爸是我乱想的,什么关系也没有,肯定是因为喝多了。”陆菲急忙否认。奇怪,刚刚为什么会觉得雷冰会说起爸爸呢?完全没理由嘛。不过,她的本意似乎也不是如同宣称的那样,是想说“自己的恋人”。这种答案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何要问得这般犹豫?真是怪。
“没有啊?下次试着这样叫,他会喜欢的,”雷冰打个指响,“想好要说啥了吧?这就要开始了。”
“等等,”陆菲道出担心,“别人会知道我想说的话吗?”
“当然不会,哪有那么大的发射功率啊?”
“还有个问题,”陆菲抬起一只手,观察着手臂上缠绕的电线和金属支架,“我就只是坐着吗?姐姐刚刚不是说,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行吗。”
“等开始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
语毕,雷冰坐回电脑前。这个所谓的法子更像是又一场实验,陆菲如此认为。事到临头,她突然觉得让刘弈知道自己很想他似乎没多大意思,他当然知道,而且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和刘弈一样,思考不是陆菲强项,稍稍思忖这里面有几层关系她就一阵眩晕。
就在她稀里糊涂的时刻,新的意识悄然进入思维。明明什么都没看到也没听到,需要她知晓的信息却像是看过一场电影,或是听过一段曲子般源源流入脑海。
陆菲用力眨眼,又伸手掏掏耳朵,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幻觉。截然不同的影像与眼前的雷冰重叠在一起,互相又如此泾渭分明,她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丛林、草场与公路,还有长蛇般在路上蜿蜒行进的车队,前后好几十辆汽车都是同样的型号。
这不是长州附近,虽然地理知识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贫乏,热带才有的植被陆菲还是认得出来的。可要是细细分辨,大树、灌木和草丛又变得模糊不清,什么都看不仔细。不只是植物,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
刘弈就在车队里,她没来由地认定。
她看到了AL,林间随即爆发了战斗,火光、枪声与爆炸屏蔽了视听,陆菲的心顿时悬起。时间的流动变得奇怪,AL与刘弈的动向时而快到她的眼睛无法跟上,时而又慢如蜗行,像是电影的升格镜头。
男孩,农场,张牙舞爪的流氓举着手枪;背叛,伏击,逃过搜捕的幸存者;陷阱,点心,林间崎岖的小道上刘弈在飞奔;烈焰,老人,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高塔,仪器,一波波信号射向天空。有些事像是已经发生过,有些则还没有,人与事在一刻不停地变幻,各种各样的可能在陆菲脑中交织。
连桑南岛上的事也掺和进来。她看到自己失手坠落,这次没有东西托住身躯,直掉进漆黑的深渊,化为模糊的血肉;或者黑人与亚裔割断了刘弈他们赖以爬上的绳索,再将她一并扔下;还有那具行动迅捷的黑色动力甲,不仅击倒了秦队长,连刘弈也跟着倒下。这、这些是什么?怎么会这样?陆菲越看越慌张,汗珠在额上、胸前与脊背大颗大颗地渗出,须臾湿透了衣服。
甚至连自己也一样出现在了眼前,披散长发、抱着膝盖坐在阴暗的角落里,身体在不断颤抖,却看不到表情。和照镜子完全不同,这感觉怪异无比。
最可怕的景象出现在最后:刘弈倒在硬邦邦的、开裂的水泥地上,头顶是白惨阴森的灯光,胸前赫然有三个枪口在汩汩向外冒血。他的双眼睁开,一只手徒劳地伸向上方,临终仍想把握住什么。浓重的血腥味呛得她几乎要窒息,周遭的空气在顷刻间变得冰冷,眼泪突然决了堤。陆菲站了起来,凶手就在刘弈身旁,枪口的硝烟还未散去。她向前迈步,想要看清那个人。
所有的混乱蓦地消失。雷冰端坐在电脑前,脚下是光滑冰凉的地板,没有粗糙的水泥,也没有中枪的刘弈,开着空调的房间温度怡人,空气中还有啤酒淡淡的焦糖香气。
“你看到了什么?”雷冰问。
“刘弈,是刘弈,他,”眼泪再度夺眶而出,“他被人杀害了!不要,不要!”
雷冰将她抱住:“放轻松,那不是真的。至少还没发生过。你要是再这么慌慌张张的,说不定就会变成真的了哦。”
这句话蕴含着奇妙的力量,女孩瞬间停止了哭泣,她靠在雷冰肩头,身子因呼吸而起伏。
“可怜的孩子,”雷冰轻拍她后背,“你看到的是刘弈,可又不只是他。该是你努力的时候了。”
“……我该怎么做?”拭去眼泪,陆菲问。
没有直接回答,雷冰从床上拿来枕头。“可能会有些疼,”她把枕头递给陆菲,“咱不能吵到别人,想喊的话请咬住枕头,当然要是受不了的话也可以放弃,一切都取决于你。为了改变刘弈将要遇到的不幸,你愿意付出什么呢?”
“我在这里,就可以改变他遇到的事?”
“你不是已经有过两次亲身体验了吗?一次是你被人绑架,他以毫厘只差避开了你,命中身后的绑匪;一次在桑南岛上,他完成了不可能的射击,用狙击步枪命中告诉不规则运动的对手。”雷冰的笑容有点怪怪的。小时候,她偶尔责怪淘气的陆程,就会带上这种笑。
“明白了。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请开始吧。”
“姐姐提醒你哦,千万别逞英雄。我见过很多自称男子汉的孬种,面对枪口倒还能装得面不改色,躺到牙医的床上却一个个现了原形,平时的豪言壮语忘得精光。过一会,也许只是相当于螃蟹轻轻钳了下,也许会超出想象。我再问一次,为了他,你愿意付出什么?”
答案再显然不过,她毫不犹豫:“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