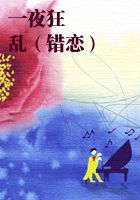车内,诗寞怕弄湿了钟筠听的座椅,半蹲着不肯坐下,他看不惯,硬是把她拉着坐下,还说什么湿了就湿了,过会儿就干了。诗寞很尴尬地坐在车上,看着钟筠听从后排座位上拿出一件外套,细心地为她披上,“怎么弄的?”这问题前不久他就问过,现在又抛出来了。
“刚才······我就想到外面走一走,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商店可以逛街的,然后才回来吃饭,谁知道走到一个水池边,没站稳就掉水里了。”诗寞编着谎话,神色不自然尽量不去看他的眼睛,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理由找也总得找个像样点的吧?她怎么可能有事没事往外跑,这大中午的吃饭时候她跑去逛街?而且路这么大,她怎么不选其他路走偏偏对这个水池边情有独钟?
钟筠听听着她拙劣的谎言也没有揭穿捅破,唇角浮上一层淡笑,面上对她的解释深信不疑,“下次注意点,别这么不小心了。”面对这种轻柔的责备诗寞只有说“嗯”的份,他望了眼窗外,“你还没来得及吃饭吧?你这个样子也不好出去,这样吧——”
他思索了一会儿,“这附近有一家卖衣服的店子,我去挑一件给你穿着先,然后再去吃饭。淇淇,你就在车上陪着南宫姐姐,不要乱跑知道吗?我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叮嘱完淇淇,等她认真地点了头,钟筠听才放心地打开车门。
“钟总。”诗寞伸出手,她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缩到衣服里去。每次她出了什么问题都是他帮着解决,实在是无法还他了。
“嗯?”他的脚才下去一只,转过头来看她,“算了吧,老是麻烦你我也不好意思,等会儿我打辆车自己回去就好了。”
“那怎么行?我哪有让你一个人回去的道理?你穿着一身湿衣服回去也不舒服,很快就感冒了,你跟我出来要是生病了,我最起码也得给你个交代吧。对了,你要什么样的衣服?”
诗寞心头微微热着,刚才的烦闷瞬间抛之脑后。“那就······还是裙子好了,换起来方便······谢谢。”
“好。”
钟筠听下车后,诗寞赶紧打开车窗看看苍鸩走了没,她到处张望,看来是回去换衣服了吧,他的情况绝对不必自己好多少。松了口气,她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身上的外套传来阵阵热量,似乎带着一股很淡很淡的清香,不自觉地想要睡觉。
“你在找我吗?”
诗寞大惊失色地差点从座位上滚下来,拾起外套到处找着声源,他就在自己打开了一半的窗户边上,脸色差到极点,浑身湿漉漉的。
真是见鬼了!神不知鬼不觉就跑到这么近了,诗寞往里靠了靠,“你不是走了吗?”
“谁告诉你我走了?”苍鸩把手掌搁在窗户上,另一只手拉了拉车门,是锁的,“乖,下车吧,车上不安全。”
他这连哄带骗的,车上不安全,在他身边就更不安全了,她是傻子才会下车。“你走吧,就算不安全也不关你事。”诗寞不看他,把衣服裹得更紧。
苍鸩看他身上是一件男士外套,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把它扯掉,“你现在全身都湿了,会感冒的,跟我回去换件衣服,你要什么衣服都有,下车。”
“苍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想再重复一遍,我不会和你回去的。”她瞥了一眼他,真希望这尊佛祖赶紧滚得远远的。
后座的淇淇贴着窗户,跪在座位上好奇地打量这个男人,他许是察觉到她的目光,向她看过来,眉毛一挑,“怎么车上还有个小孩?”很快,苍鸩就想到了那个带小孩冲出来的男人,一千种可能在他脑中过滤,一个利刃就丢了过来,“是他的?”
她怎么能上已婚男人的车子?苍鸩认为这太荒谬了,“你怎么会和一个有孩子的男人一起出来?”他老婆知道会怎样?光自己知道就已经抓狂了!
诗寞没否认他说的话,蔑视着他,“你不给?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孩就不是我的?”她就是要气死他,把他气走自己耳根子就清净了,可惜她还是想错了,这种话完全是漏洞百出,但她就会胡说,也没考虑这句话的真实性。
苍鸩有一瞬间的恼火和寒彻,不过马上他就笑了,诗寞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叫出了一个很久没叫过的称呼,“宝贝,下次玩笑也要开得好一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才离开我两年,就有了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你千万别说这是领养来的,我猜她八成是那个男的,你可别破坏了人家幸福的家庭。”
淇淇一脸无辜状,车窗关着,完全不知他们在讨论什么。
诗寞被噎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回想刚才自己说过的话,脸皮都磨薄了几层。是啊,她哪里来的小孩?
看他这架势是赖着不走了,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爬到驾驶位上,好在车钥匙没拔,可以发动,诗寞试着用自己那一点从苍鸩那儿学来的开车技巧,发动车子,生涩地握住方向盘,踩住离合。嘴皮子斗不过他,那她跑总行了吧?
等开出一段距离她踩下油门,车子摇摇晃晃地开走了,苍鸩本能地退开,登时就七窍生烟了,自己跑得再快,能和车比的吗?
钟筠听提着袋子回到自己停车的地方,发现车不见了,心生疑惑。
苍鸩注意到了他,瞬间化成了一批凶猛的狼,两眼发着恶毒的绿光,好像要把他撕开吃掉。他会是那个女孩的老爸吗?苍鸩有点不确定,可能是,就冲着这种可能性他微眯着眸,继续用杀人的眼神盯着他。
钟筠听莫名其妙,怎么又来了一个落水者?这种眼神看他做什么?自己得罪他了?不过他自身的素养很好,正要笑问他有什么事吗,苍鸩气哼哼地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瞪完他大摇大摆地从钟筠听眼前晃过。
他一走,钟筠听就接到了诗寞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听着她说开到了一个商场附近,并告诉他方向,放下电话后钟筠听就朝着那个方向跑去。
苍鸩坐回自己的车子,他慢慢发觉,他来海沙市不仅没有观到海缓解自己的脾气,反而被这几天接连的几件事搅得心更加烦躁不安,他打开车窗,点燃支烟叼在口里,打了个电话出去。
“廖姨,我上次把诗寞的衣服那些东西翻出来后,你把它们丢在哪里了?”
廖姨心里又惊讶又惊喜,惊讶的是他还记着那些被他遗弃的东西,惊喜的是这种好迹象说明了他有意和诗寞复合,里面也许装了什么贵重物品。她虽然上了年纪,但该记住的事情还是不会忘记的,她答道:“苍少你是要找什么?我把它们都装在一个箱子里了,还没丢呢。”
苍鸩的心松了一下,没丢就好,他吸了一大口烟,把烟夹在指缝中,吐出烟圈,“那行,帮我找找看,我记得有一个戒指盒丢里面了,还有一条项链,现在就去找。”他现在始终还记挂着那枚狠心被自己丢弃的DarryRing,他不是女人,却第一次像女人一样珍爱一枚饰品。
苍鸩不知他当初是抱着何种心理去买这一枚钻戒,只是一次求婚他就相中了这枚寓意深刻的戒指,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他自己都有所不明的感情。或许当时他无牵无挂,也没有想那么多,一张身份证换终身一枚戒指,看似不值,却俘虏了她一颗心,离自己任务成功迈进一大步。
这是戒指在那个时候的意义,他不懂珍惜,丢了也不觉可惜。可现在细想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承载了一个女人的一滴泪,他至今也不会忘记诗寞能发声是自己将这枚戒指套进她的无名指上。
他从来不懂责任,不懂真爱,如今有些懂了,戒指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透过它就好比看透一个人的内心,在对方的心里面,自己值得他这么去付出,完全信任他。
他轻视了戒指的力量,而诗寞,恰恰赋予了戒指力量。自己要是珍重戒指,就等于珍重她,不负她心,她也就不至于恨他的欺骗、虚情假意,辜负她的付出,扼杀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了。
世上很多事情都要等过后才发觉,才来后悔,他就是这样,做的时候理所应当,过后悔不当初。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为何事后才醒悟?
苍鸩的精神有些涣散,廖姨在说话他恍恍惚惚地也没听见,手中的烟快烧完了,灼烫着他的手指,飘渺的思想被拉了回来,把烟蒂从车窗丢出,“苍少,苍少?”
“说。”苍鸩拿了一条毛巾出来擦头,听廖姨道:“项链我是找到了,可是你说的戒指盒没有啊。”
“没有?”苍鸩忽地立起来,头顶一下子撞到了车顶,疼得坐了回去,把手中的毛巾搭在头上,“怎么可能?你仔细找找,东西都放在一起,除非有人拿了,否则不可能找不到。”有人拿了?“廖姨,除了你还有没有别人碰过箱子?”
廖姨埋头找着,把整个纸皮箱倒转过来,每件衣服都抖了抖,“没有吧,自从你上次把诗寞的东西丢了后,我都放在箱子里碰都没碰过。”
这就奇怪了,莫非盒子还会长了脚跑了不成?
“······还是没有?”又等了几分钟,他问道,“抱歉,苍少,箱子已经翻遍了。”
“那行,我现在派人去别墅拿。”他不知自己拿回项链有何用处,诗寞不会因为一条项链而因此感动。可是,人有时想做某件事的时候哪里会去思考这么多为什么呢?
没人知道,戒指早已被一个人拿了去。
打开白色的戒指盒,凹陷的地方嵌着一枚璀璨钻戒,玲细细端详着,冷漠的神色逐渐变得柔和,她把戒指从中取出来。
它很美,钻戒有棱有角,每一颗细小的钻石都是精挑细选,精心打磨出来的,对每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奢望,得到自己钟爱男人的求婚钻戒,并且是一生只能有一枚。
但她并不看好苍鸩和诗寞的爱情,毕竟因戏生情的婚姻能多长久?她是以一个旁观者,一个卧底看待他们的。
她自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合格的卧底,她在苍鸩面前扮演的是一个私人医生,他或者诗寞受伤帮忙救治,恪守本职,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偏偏自己的内心却没有向着苍鸩,所以这一点上她比他还会做戏。
其实她本来不是这样的,她很珍惜苍鸩给自己的从医机会,万分感激他。是左昱,自从遇见他,她就成了他的眼线,甘愿为他做任何事,像是被洗脑了一样。
玲呆在苍鸩身边比较久了,和诗寞有时也有接触,对两人都了解比较清楚,所以左昱总能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他们感情进展到哪一步了。比如说,苍鸩上回被人下药还能把诗寞送到医院救治,向诗寞求婚的经过,他委托自己务必连夜给南宫御燚配出药等等的事,左昱没一个不知晓。
她亲眼看着苍鸩一步步走向叛变,看他这个杀手逐渐卸下伪装。
将戒指放回原位,她巧笑着踏进一间别墅,“阿昱,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