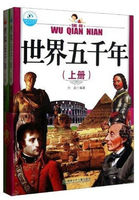苏云婳心中怔了怔,她虽然已经对这个名字,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映像了,但是却也知道,这是母亲的侍女之一,想来自己小的时候,定然也没少得她好处,不然,又怎么会在听到她的名字时,觉得格外温柔呢?
不过,这温柔之后,却是与温柔等同的难过了。恍惚想起出现震动的那日,僧人要往下冲她还拦了拦的事儿,她心中就越发地不舒服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僧人援救不及。
慕容承景看着她的神色,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安慰,只是握紧了她的手,希望以此来传给她自己的力量。苏云婳仿佛感受到了他的心意。转头来对他微微点了点头。
“两位施主,故事贫僧已经说完了。两位若是已经做好准备,不如就早些出去吧。”僧人已经恢复了那种浮于红尘外的模样,他眼神坚定又清冽,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波澜了。
苏云婳走到冰棺前,深深地望着棺中人,长叹一声,“娘,且候候,你想要,终归都是会实现的。”
说着,她和慕容承景对着那冰棺磕了三个头。就起身对僧人道,“就麻烦大师再将我们送回去了。”
僧人点点头,“那我们当快些了,因着前一次的剧烈攻击,这山其实已经有了随时都能崩塌的危险。”
慕容承景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看看避过了顶上落下来的一块小石头,“你不早说!”
言讫就将苏云婳护在怀中往上面去。
他们才从祭台下走出来,祭台之下的那个空间就塌掉了。苏云婳看着那个已经塌掉的空间神色十分复杂,只有那戒色和尚一脸淡然的模样,“倒是掐住的刚刚好。那些石柱果真只能维持这么点儿时间。”
苏云婳闻言看向他。
“施主莫误会,贫僧是让那个空间多撑了几日,而非刻意破坏。”僧人道。
“请问大师,您的法号是什么呀?”这么长时间,人家都救了自己好几次了,还这么大师大师的叫,终归是不好,所以苏云婳就忍不住问了一句。
僧人微微颔首,“贫僧戒色。”
闻言,慕容承景和苏云婳皆是一愣,也就是这个愣神的功夫,两人都被戒色带着飞出了那水帘之外,稳稳落在了山脚。
没多久之后,更是回到了村子里。彼时,陈小星和夜风都已经有些急了。荣月儿心中十分清楚那和尚是个好人,和张安两人在屋中围炉煮茶,简直淡定的不行。
一见苏云婳和慕容承景归来,候在屋外的那两人喜出望外,但是对带走各自主子的和尚甚为不喜。
“和尚,你说都不说一句就带着主子离开是个甚么意思?!”夜风不爽道。
这话若是陈小星先说倒还说的过去,可从夜风的嘴里说出来,就差着那么点儿了。两人被带走不假,可慕容承景那是自己贴上去的好嘛。饶是苏云婳,也完全看起来就是自愿的。
不过,也不用等谁吐槽夜风,慕容承景就一句话喝退了他,“夜风,不得无礼。这是清凉寺的戒色大师。”
而苏云婳更是对着门内一摊手,“大师,里边儿请。”
眼见着慕容承景和苏云婳都对和尚礼数有加,饶是夜风和陈小星再没有眼力界,也知道此人不仅是友非敌,还是上宾。
当即又是道歉又是将人往里面引,而僧人一直都是嘴角噙笑的和善模样,丝毫都不介意他们的态度。
以入屋子,张安已经泡好了茶水,见红衣僧人进来,当即便奉茶让坐,说是要谢他的救命之恩。
戒色让了让,终究是敌不过张安热络。只能在上首坐了。
喝了会儿茶,大家都缓过来之后,苏云婳就问戒色,“大师,您如今是要何往?”
戒色浮了浮茶叶末,小饮一口后,叹道:“普佛南归。”
苏云婳想了想,就笑道,“恰巧我们也是要往南去的,与大师同行可好?”
戒色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继而道,“贫僧知施主的意思,然,贫僧另有事要办,恐不能与你们同行。不过,施主也算与贫僧有缘,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便捎信往折花州,天南地北,虽远必至!”
苏云婳也知道,这个请求多半是不能成的。不过能得了他一个承诺,心中还是高兴的,客客气气又心情愉悦地换了个话题,将和谐美好的气氛换了下去。
两盏茶的时间之后,戒色就要起身告辞了。
临走之前,苏云婳和慕容承景去送,但也不过送到门口,转瞬之间,那人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中。
慕容承景望着戒色离去的方向,不无感慨道,“大师的武学修为如此之高。怕是这大昭千秋之间也不过往返也不过一日一夜了。本王原不信这世上有能只身日行千日之人,今日一见,却是信了。”
苏云婳但笑不语,过了好一会才以手肘撞撞他,“行了,回去之后收拾收拾,我们也准备上路呗。”
慕容承景沉吟了一下,淡淡道,“云婳,可还是按着计划的路线么?”
苏云婳一愣,就明白了丈夫的意思,笑道,“当然。我们没有一兵一卒,饶是有心收了小千秋,只恐有心无力。表姐深明大义,而今千秋吞了西梁和灿若,难保不动东面的信和与小千秋,表姐她饶是不愿战,也是非战不可了。”
慕容承景心道她看的通透,便点点头赞同了她的话。
由于是隆冬天气,这不咸山山脚下的小村庄中的装扮多是将人裹地只剩下一双眼睛,也没有甚么要不要乔装的疑惑了。
一行人如约在休整一日之后,就上路了。
启封城在沂水边,几乎是和昊金城平行的一个小城,两城之间只隔着座羽落山。张安之所以说从启封城这里走,概因它离着那只经商用却不过王都的秋水道儿近。
从小村出来后,大路分两边。一边往左去昊金,一边往右去启封。
有计划就这点儿好,遇到选择的时候完全不有犹豫,右边走妥妥的。可见计划这种东西,实在是选择困难症患者的福音。
然,计划这种东西,也是有死敌的,它叫变化。
就在他们踏上了自以为麻烦最少、能到目的地的时间最短的路程后的第三个时辰,他们就遇上了这个计划的死敌。
也就是说,他们从早上走到了日头正好的中午时分,距离启封城还有三五十里路的时候,一行人摊上事儿了。
不,不是杀手。就是普通劫道儿的。
面对乌压压一大片披着貂裘,戴着绒帽,个个都五大三粗地只看一眼就能知道他们的力气肯定一个顶五个的人。
为首的人操着一口十分纯正的东北腔儿,说出了十分经典的劫道台词“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
尽管苏云婳十分想吐槽一句,大哥您这儿除了几棵被雪埋住的小草根儿,没您说的树啊!这路开的也比较牵强。不过,她还有点儿理智残存,没有说出来。
跟劫道儿的讲道理,饶是在文明又发达的现代,那也是十分天方夜谭的事儿,更何况是在这个拳头说话的世界。
慕容承景和其余几个男人将苏云婳和荣月儿围在了中间,愉快地分人数。
“左前方那十一个归我。”慕容承景面无表情道。
夜风不甘示弱,“右前方剩下的归我。”
“左后方那十二个都是我的。”张安摸出腰间铁扇,笑的风流妖孽。
“右后方剩下的……”陈小星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儿,掂量了一下后,眼泪都要下来了,“特么的二十多个!张大哥,不带这样的!”
荣月儿鄙视的看了他一眼,压低了声音小声说,“那一群细胳膊细腿的,一看就是脓包,陈小星你可真没用。”
陈小星面上一红,觉得作为自己作为男子汉的尊严被深深的打击到了。并且还是被这个对自己而言十分特别,特别到自己十分想在她面前好好表现的姑娘。
“小……小月,我的意思是,我其实比张大哥厉害。”少年摸摸头,继而嗷呜一声就要朝着那匹扛着斧子大刀的人冲过去。
然而,这才冲了一步呢,他就无法向前了。正郁闷呢,转头一看是苏云婳,顿时改了脸色,“主子,您不用担心我,我很厉害的!一拳能砸俩!”
说这话的时候,他雄赳赳气昂昂,模样英勇极了。还有意无意地瞥只看着张安背影的荣月儿。
苏云婳看着陈小星的视线,心中为他默哀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命令道,“大冷天的,人家出来劫道儿也不太容易。你可千万莫赢了,输给他们,给他们点儿心理安慰可好?”
陈小星打了个哆嗦,“主子。您病糊涂了吧?”
话才说完呢,陈小星的腹部就挨了重重一记,转头去看,荣月儿晃晃自己的拳头,“怎么说话的你?没大没小!既喊一声‘主子’那就要听从跟从服从,小厮就没你这般样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