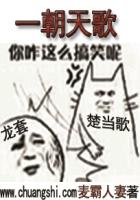我的家在芮儿和东子的协商之下,开始恢复我活着时的模样。那张写字台不知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靠房门那边的一个角上有道很深的划痕,我活着的时候是绝对不存在的,我每天的生活,只要东子不在,基本就是在这张写字桌便度过的。我喜欢阅读,喜欢陷入那种沉思后的疲惫里。我无时无刻不都在等东子回来,我总是会忘记这里还不是真正属于东子的家,他属于另外一个地方,我这里仅仅只是他的一处歇脚的地点。
东子说,要买一张新的,芮儿不同意。芮儿说这张写字台要留下来,写字台是我活着时最爱呆的地方,我的诗,还有那本《欣儿作文》都是在这张写字台上完成的。
第一次自杀的时候,我用一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装好我要交给东子看的《欣儿作文》。我把文件袋的长绳绕呀绕呀绕了很多圈。不知多少圈。我试图数过,数到后来,我就迷糊了。这个和我相爱了两年零三天的男人,我该为他殉情,值得为他殉情吗?并且我的殉情是否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者就是对他的一种要挟,威胁?我不知道,我那样做没有任何意图,我就是感到累,感到失去任何兴趣和勇气。这就和我小时候总是会时常把自己藏到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在黑暗里躲起来一直到睡着;睡着了我就会感到安全,感到世界是温和的,不再那么可怕。
第一次自杀时,我真的没有去想那么多。
那天,我锁好房门。心情并没有多少不平静。
我在街边的药店买了一瓶“******片”和一瓶“佳静安定片”。按有关部门规定此类药物是不允许药房随便而且是不限量零售的,需遵医嘱控制给药量,为防我这样采取不当的轻生行为。但利益这一当今最高的法则才是最有力的规定,人们更愿意本着利益得失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包括东子那个婚姻中的利益共同体的所有关系,压得他,压得我,无处藏身一般。
我要离开这个利益喧嚣的战场。是那些有着不可抗拒利益需要获取的人们帮了我一个忙。两瓶药花去不足10元钱,生命原来如此廉价。
我想,就是如今所有东西再偷工减料,两瓶对于我也够了吧?我听说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人想要自杀,她喝下了一整瓶的农药,结果不但受了不少的罪,还根本没死成。她的丈夫嘲笑她,于是她就去找律师要起诉那家生产厂家。结果律师说对于她的这种行为,厂家是免责的。
我的真实就是绝顶地去爱。不然,我就自行解散。这也是我第一次殉情的理由。不过我自己都清楚,那是遁词,我其实连我的爱本身都生出疑惑,回头想,我只是像一个小孩,要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耍赖一样。我究竟想要什么呢?想要东子离开他的家,只与我一个人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几乎不可能离开他的那个家,至少是短时间里办不到,这点他早就告诉过我,他说自己离开那个家后,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他说他不想那样,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必须拥有它,即便是虚幻的拥有也才会感到踏实。他的处境就是寄人篱下,就是像一个傀儡似的受人操纵着,他没办法摆脱,至少短时间里做不到。我为此感到沮丧和灰心,我有时就会开始恨他,很周围的一切。每次东子开车离开后,周围邻居要是有人顺口问我:你丈夫又要出差了?或是诸如此类的话语,我就会无比地愤怒,就像去伤害什么,毁掉什么。可我谁也伤害不了,什么也毁灭不了,我能做的只能是伤害我自己,和毁灭掉我自己。
我在我常去买日用品的便利店买了它架上最贵的一瓶产自阿根廷的红酒,名字叫做“勇士”。这是东子第一次和我一起喝酒时,为我买过的,那以后我就只喝这种酒。
我让服务小姐帮我拔出软木塞,结果几个小姑娘全不会用这种可以旋转的开瓶器,想必她们粉嘟嘟的青春还没有进入酒的迷乱吧。我对她们亲热地笑笑,自己亲自大力将软木塞拔出。外国的软木塞就是比国产的要韧软。
我提了酒瓶出来。在路口上了一辆红色出租车,我是特意挑选了一辆红色的车况比较好的桑塔纳出租车。我凭影影绰绰的记忆顺着东子第一次也是唯 次骑摩托车带我去他家的路线一直到了他所住的小区门口。
我本不是一个善长记路的人。但这一次我记得一点没错。我多给了司机一点钱。还对他真心地道了谢。
这一天是10月8日,是黄昏以后。离我真正死亡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我用东子第一次在楼下教我的方法认出了他的家。七搂,那一层是顶楼,是一种复式建筑。只有他一家的窗外挂着两部空调。
我多愿那两个窗口都亮着灯。西边的是他的书房,据他说他一直一个人住在书房,东边的是他家的客厅,只有客厅亮着灯。
我在离他家最近的小花园中的一只石桌旁坐下。中秋的天气,已有些凉。尤其是我所坐的夜晚的石头,冰凉冰凉的。我没有顾及屁股底下的冰凉,而是开始对着瓶子大口大口地喝酒。
我直直地望着那个亮着灯的高高的窗口。东子一直很真挚地说在家里,他从来都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书房。我真想哭在这个我即将为东子殉情的夜晚,如果我还有眼泪的话。东子在家,而且东子此刻一定是和他妻子朱小燕,还有六岁的女儿谭楚楚正围坐在电视机旁。
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什么。如此明明白白的不忠,却可以夜晚在一条长沙发上共享同一个无关紧要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电视节目。
人,我越来越不明白。荒谬(无聊?)公式:我知道你知道她也知道。但还继续着在我大口大口喝酒的时候这么想。
在我的经验里,婚姻可以有吵架怄气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在床头发生在床位就和好了。但唯独不能有不忠。忠诚是婚姻中绝对的一块基石,抽走了它婚姻的屋宇必会倒塌。
而我正对着的东子的婚姻是什么呢?仍然让他们同在一个屋顶下,同在一个沙发上,甚至同在一张床,这么想一下我都觉得胃液翻腾,我就觉得死掉比活着轻松,甚至尊严。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这样,会这样而又还是无法摆脱,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往里跳?这不是和别的一样,对待其它的东西和事物,你可以放弃,可以置之不理;但这个你办不到,在这种事情里,是没有理智和意志的空间的。你难道能让梁山伯和祝英台放弃他们的爱?让罗密欧为了家族放弃朱丽叶吗?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荒谬无稽的?
是,尊严。尽管我觉得在除东子和芮儿之外的所有认识我的人眼里,不配谈尊严两个字,一个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人是没有尊严可谈的。我,在人们眼里,充其量就是东子的情人,情人这个词已经泛滥成灾,而我拒绝承认我是东子的情人,我不做任何男人的情人,我,只为爱情而活着。
有一对显然是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的年轻夫妇,从我身边走过两次。我在对着他们的身影想,你们彼此是忠诚的么?你们互相需要么?互相关爱么?互相亲密不可分么?你们平常的说笑间有没有闪躲着第三个人的阴影么?夫妻间又是如何每天绕过那明摆着的第三个人而互相拥抱的呢?
尼采:“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更高的价值不断失去它们的价值,漫无边际,对‘这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无言以对。”是的,这有什么用?我所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这世上任何事物,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样的夜晚,在尼采这段熟悉的语言中,我用酒瓶砸碎装着“******片”和“佳静安定片”的小玻璃瓶,从碎玻璃中拾出每一粒小小的药片,每拾一颗,东子的名字就闪了一下,仅仅只有一下。药片慢慢地在我的手心中汇集成为小小的一堆。我分三次用酒吞下。有点难咽。这是我对死亡的第一个艰难记忆。
我仍盯住那个窗口。我知道他一定在家。他的“家规”,他勉强而又坚决遵从的另一个女人的规定。既然这么怯懦,这么好汉做事无力当,又怎么就斗胆生出来鱼和熊掌兼得的幻想?又怎么口口声声要爱我一生一世呢?先不管他做人形象,仅就他所具有的学识和头脑,他至少应该懂得爱情中三个人永远都有点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