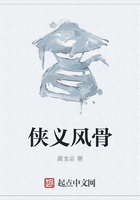米阴阳艰难地攀行在一条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山路两侧古树盛旺,枝干参天,浓荫蔽日。一泓溪水在他的左侧从上游向下游流去,汀汀淙淙,音律奇美,悦耳得很。他心里懵里懵懂的,不知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似被一种神秘之力牵拽着,拥推着。
直走了好几个时辰,不远处出现了几座相连的茅屋,看上去是一处草堂。米阴阳忽觉一种稔熟,难不成这里是自己的家,心中竟生出一种“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慨。
米阴阳又饿又渴,急急向草堂赶过去。
“阴阳先生,快来。”有人叫他。
米阴阳行至草堂前的空地处,发现那里坐着一老叟,白发披肩,白须垂至胸前。啊,这不是常乐宫的玄朴大师吗?他怎么在这里?
“大师,是你啊。”米阴阳激动道。
“我等你好久啦。”玄朴大师近在眼前,可他的声音却像是从天边传来。
“哦,对不住啊,让大师你久等了。”米阴阳抱歉道。
玄朴大师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端起手中一小杯茶,放在嘴边轻呷一口,道:“我已经等了你好几年了。”
“大师有何吩咐,有何指教?”
“你来入坐,与我一同品茗,边品边聊。”玄朴大师指了指自己右手侧的石凳。
米阴阳落坐后,端起面前的小茶杯,一饮而尽。他太渴了,就自己拿起茶壶,朝面前一个大瓷碗里倒了满满一碗水,豪饮下去。
玄朴大师笑了。
米阴阳讪讪地笑了笑,说:“乡野之风难改,乡野之风难改啊。”
玄朴大师递与米阴阳一把蒲扇。
解了渴,又是在这清幽之地,米阴阳重现稳重之色,问道:“大师在此等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自然,自然。”
米阴阳洗耳恭听。
玄朴大师道:“你可还记得有个庄叫槐树庄?”
“记得,记得。”
玄朴大师将桌上一张纸拿起,反过另一面,上面有两个字:静男。他将这张纸拿给米阴阳看,问:“你可还记得这个孩子?”
米阴阳说:“当然记得。不过这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自己作主张把名字改了,叫个刘靖南。”米阴阳用手将“靖南”两字写与玄朴大师看。
“啊,果然是顽劣之徒。”玄朴大师说,“他这么一改,了信法师念的善经,我念的恶咒,全不管用了。”
“这孩子倔得很,他爹娘没办法,再说了,他们都是庄稼人,目不识丁的,听着此‘静男’与彼‘靖南’发音一样,也就由他去了。不过还好,我去过槐树庄,听说,这孩子没有闹出什么祸乱来。”
“我没记错的话,这孩子如今是十七岁了。”
“对,刚满十七。”
“那地方如今民风若何?”
“仍是彪悍。虽则封闭,可人心不古,世事难料哩。现如今,男盗女娼更伤风化,可是一些人为了各自目的,哪管什么风化不风化啊。”米阴阳有些忧心地说。
玄朴大师说道:“昨日我夜观天象,见金星和木星足有半个时辰竟然互相移位,蛊惑太空。此乃不吉之兆。本道算了一课,于是就占出十七年前的事儿。当年我看得清楚,进入那孩子体内的幽冥之灵气是一妖艳女妖,她真气受创,一时难成气候。可这孩子年方十七,青春萌动,若妖女再修炼一世,可能真气再度上扬,必会生出祸端。”
“听闻,那孩子倒是单纯,没什么歪心计,为人十分正派。”
“他只是个载体。”玄朴大师说。
“依大师看,该如何处置呢?”
玄朴大师说道:“青春少男,思春之心萌动,钟情爱恋,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只是,不能让那妖女钻了空子,更不能让那孩子受了妖女的蛊惑。”
“哦。”米阴阳半懂不懂,“大师能否说个仔细?”
“你我非同道中人。你不要太不灵醒。我跟你指点了很多了,已经破了我道家之规。倘若我再多言,天师在上,看得到听得见呢,肯定会怪罪于我。我的符纸上有几句话,你自己看看,慢慢琢磨琢磨吧。”说完,玄朴大师忽然化作一股雾气,不见了。
“大师,大师……”米阴阳叫了几声,却一无回音。
……米阴阳从他的小院里的地面上起了身,揉了揉他的那只独眼。阳光照着他,他看了看太阳,方明白刚才是南柯一梦。
米阴阳侧转他的行动不便的身子,却见面前有两张道家用纸,心里激灵了一下,他彻底清醒过来。心想莫不是玄朴大师于幽冥中为他指点了迷津?
他拿起其中的一张纸,只见上面画有一根绳子,绳子的上面是四个字……口不能言。
绳子的下面有七个字……天上无云不下雨。
何意?米阴阳琢磨良久,不得其解。
他又拿起另一张纸,上面写有一句话……鱼雁互通,一笔写就心中言。
米阴阳转动他那只独眼,想了想,倒是把这句话想明白了。“鱼雁互通”不就是“信”吗?“一笔写就心中言”也是“信”啊。他兀自点点头:前者指的是“相信”,后者指的是了信法师啊。看来,玄朴大师是托梦授意他去天音寺找了信法师啊。
米阴阳喝了一碗水,吃了两块油饼,而后拿起搭链,骑上毛驴,直奔一百里开外的天音寺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