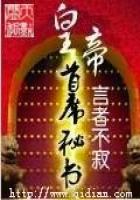“你……你……给我等着,我当家的就要回来了……”杨婶的脸都气白了,却又实在怕了眼前凶神恶煞般的李锦寒,抛下一句话便狼狈的离开了。
“阿寒,你……怎么可以打人的……”杨婶走后,李芷秀心中思绪万千,一下子乱了手脚,一边连连查看着李锦寒全身,“阿寒你没有受伤吧?”
李锦寒已经不排斥李芷秀的关心,没有推开,摇了摇头道:“没事的,是她受了伤而已,我没受伤。”
李芷秀想起杨婶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又有些急了,惊慌道:“这可怎么办啊,杨叔回来要是知道这事,可是会找你拼命的……”她说着又微带责备的看了李锦寒一眼,“你……你怎么可以打人的……”
“他要来便来,我岂会让他讨了好处去……”李锦寒淡淡地道,“那泼妇欺负你,我便要打她。”
李芷秀身躯猛然一阵,她忽然意识到李锦寒刚才可是因为她被欺负才这么愤怒的,她缓缓抬起头来,不敢相信的看向李锦寒,颤声道:“阿寒……你……竟这么在乎阿姐么……”她想起这么多年的心酸,忽然簌簌掉了眼泪来,“阿姐被人欺负了,原来阿寒也不肯的……阿寒心里念着阿姐……阿姐心里好高兴呢……”
李锦寒心中那股微妙的情怀忽然慢慢地弥漫开来,他望着眼前泣不成声的女子,灵魂里的那个心结悄然解开。是啊!既然前世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为什么不珍惜现在的一切,至少这里有真真切切关心他的亲人!
他勉强地笑了笑,柔声道:“你是我阿姐,我自然要在乎你的。”
这么多年来李锦寒何曾对李芷秀假以过半分辞色,李芷秀静静地听着弟弟的那句话,呆呆地站在那里。她整个身体都被巨大的幸福感包围着,这个时候一切恼人的东西俱都与她无关,她直感到周围的一切都仿佛静止了,回荡在她耳边的便只有弟弟那句话。
身后的阿馨却是怔怔地看着李锦寒,呆呆的说不出话来,心想道:“这个恶人……原来却是这般怜惜小姐的么……”她又回想起刚才李锦寒打杨婶时那副凶狠很的面容,暗道:“他竟有这么狠厉的一面么……便是杨婶,他也是从来不曾怕过的……”
既然抛开了心结,便要在这个世界好好的生存下去。第二天李锦寒便不顾他姐李芷秀的反对,要往锦绣轩上班去了。
这锦绣轩本是岭永县南城坊的一家布匹店,规模并不大,却因为东家乃是州府下来,回家养老的蔡老先生,这才给它涂上了一层高贵的气质。
李锦寒三第未中之后便一直是在这锦绣轩内做帐,说起来,这份体面的活计儿还是他未来的岳父,本县魏县尉托面子求来的。
当初李父李重免在世时,魏县尉为了巴结他,曾和他定下了一门亲事,许诺日后要将女儿魏雨雅嫁给李锦寒,尚有押解文书作证,白纸黑字,绝不容有错。
只是随着李家的家道中落,这份亲事在所有人看来都有些微妙了。
魏县尉心中倒也曾想过退婚的,而且自李锦寒县试屡次不中以来这份心思便愈加强烈,然而他在这岭永县内终归是有头有脸的人,做这势利的事情也实在不好下手。再加上李重免当年对他有恩,旧情作怪,故而这退婚之事万万说不出口来。然而眼看当年约定成婚之日日益逼近,他却又绝口不提成亲之事。
李锦寒第三次县试依然不中之后,整个人便陷入了癫狂乖戾当中,心魔入脑。魏县尉倒还好心,托着关系给李锦寒在锦绣轩内求了个体面的做帐活计。他如此做法却还是存了另外一层心思,却是希望李锦寒能上道,和蔡老先生拉上关系。这蔡老先生虽然退下州府,但是身后可是州府参议大人这条线,如果李锦寒能替他搭上这条线,他自然也不介意将女儿嫁给李锦寒。
锦绣轩里包括李锦寒在内倒是有三个做帐伙计,一个是李锦寒自小的玩伴郑建志;另一个是最近新招来的伙计,叫做阿平,和他并不熟。
李锦寒两世为人,气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郑建志外表虽憨,心却不粗,总是隐隐感觉着事情不对,不时好奇地望上李锦寒一眼。不过任他是诸葛在世,也绝对想不到灵魂附体这么荒谬的地方去。
蔡老先生今年刚过六旬,苍颜白发,相貌比实际上看上去还老些,不过双眼中透出的精光倒是向人展示他并非真的垂垂老矣。他一开始便当着众人的面数落了李锦寒一顿。平日里他看李锦寒这个三第不中之人便极为不屑,早就打算过要将李锦寒扫地出门。虽说李锦寒是魏县尉求情安排进来的,但是他又岂会真正在乎一小小县尉的面子!
蔡老先生身体不佳,有积年的病患,在堂前交代了一声,便回内院去了,留下李锦寒三人照看生意。这时节布匹生意倒也清闲,三人也不会忙。
郑建志这次从蔡老先生那里搞了一本账单过来观看,说是用来研究做帐学识。他倒也算认真,拿出自己做的账单一一对照,不时点头。不知不觉翻到最后那几页,却再也看不出和所以然来。
李锦寒问起来,原来这最后几页却是蔡老先生列的一个总帐,他在这里用上了自己琢磨的一种新奇算法,不过他自己也没有研究通彻,列了几个式子,便再也写不下去,只留了几个残缺式子在那里。他将这账本交给郑建志时曾经千盯万瞩不要搞乱了后面的运算。
蔡老先生这个沉浸了做帐运算有几十年功底的老者都琢磨不出来的东西,郑建志自然更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思维一进入空虚状态,人就容易浮躁起来,他抓了抓头,便去内院解手。
李锦寒听郑建志说的神奇,从柜台上将账本拿过来,翻到最后面,仔细看了看,发现蔡老先生琢磨的这种运算和二十世纪发明的筹算算法极为相似,但是蔡老先生这算法却没有筹算算法那般完善,只能算是筹算算法的雏形版本。饶是如此,李锦寒心中对蔡老先生不免也升起一股佩服之情,身处的这个时代算起来不过八世纪,蔡老先生能跨时代想出这种东西来也确实是难得可贵了。
李锦寒眯着眼睛看了会,顿时看出蔡老先生运算卡壳的关键所在,却是对其中梁转换有些模糊。这个问题一看通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东西,说来蔡老先生在那里卡住,也确实是有些可惜了。
心里如此想着,李锦寒下意识的便拿起柜台上的毛笔,将蔡老先生错误的地方改正了下,又在那几页的空白处把未完成的运算式子给补充完全了。这也不费什么功夫,在郑建志回来时,李锦寒已经将筹算算法列完。
账本打开摊在那里,郑建志一眼便瞟见了账本上那没有干涸的墨迹,吓得整个人都跳了起来:“阿寒……你……你怎么能在这上面写字啊!哎呀!你可把我害死了!“他又连忙翻看账本,却哪里还有回救的余地。一想起蔡老先生把账本交给他时的千盯万瞩,郑建志一张脸顿时如同苦瓜一样耸拉下来。
李锦寒不以为意,道:“我帮先生将这式子列完了,先生怎么会责怪你呢?”
郑建志听到李锦寒这话像是听到了世上最搞笑的笑话一般,竟然放下了心中的烦恼,失声笑道:“阿寒,你莫不是大病一场,烧坏了脑子?”他说完又有些后悔话说的重了些,小心翼翼的看了李锦寒一眼,见对方似乎没有生气,这才放下心来。不过他眼光一看到手中的这本账本,却又如何也轻松不下来。蔡老先生多年来研究这种新奇运算,他是早就知道的,这账本后面几页便是先生的思维所在,如今可好,这账本在他借来时被搞乱了,鬼知道蔡老先生知道后会发多大的火!
“唉!”郑建志重重的叹了口气,整个人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耸拉着脑袋,苦声道:“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先生嘱咐再三,绝不能搞乱后面他列的式子的……”
“我真的帮先生将问题解决了,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郑建志恍若未闻,一心只盘算着怎么向蔡老先生交代这事情,喃喃道:“阿寒,我和你自小玩大,自然是不会供你出来的,只是希望我这次不要被先生扒下层皮来。”
李锦寒道:“你不用担心了,不会有事的。”
一边的阿平忽然冷冷地道:“不会有事?哼,这式子可是记着先生的思路呢,弄不好先生这么多年的成果都要被你们给毁了!先生能不大怒吗?”
郑建志尽管知道阿平这小子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他这个时候已是惊弓之鸟,也确实被阿平影响得更加慌乱,对阿平气急败坏地道:“阿寒刚大病一场,正恍着呢,你刚才也在这里看着,怎么不提醒点……我知道了,你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