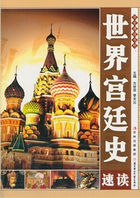周晓京问:“你走的时候她在吃饭吗?”
孙妈妈道:“已经开始吃东西了。”
周晓京问:“那时候她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绪?”
孙妈妈道:“没什么异常的,太太一向对工作很上心,从来都是提早出发。昨天她吃饭前还说,是第一天去‘江畔明珠’上班,不好迟到,要抓紧时间吃饭呢!”
周晓京又问:“从你五点多离开这里,回家之后直到午夜十二点之前,你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证人?”
这是在确认她的不在场证明了,毕竟在真凶落网之前,一切与乔安琪有关系的人,都不能排除作案嫌疑。
孙妈妈道:“我在替儿媳妇带孙子,我们住的是老式弄堂房子,我老伴儿走了之后,就把一层租给别人家了,我住二层,大儿子一家住在三层。后来九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直打盹儿,媳妇就带着他回去睡觉了。我第二天早晨还要赶早市给太太买菜,也早早地睡觉了。”
周晓京道:“也就是说,九点钟之后,你就没有时间证人了!”
孙妈妈急道:“啊哟小姐哦,你不会是怀疑我吧,我一个孤老婆子,哪有胆子去杀人哪!”
周晓京安抚她道:“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您不要激动!”
孙妈妈有些沮丧道:“啊呀啊呀,本来我那个小儿子是跟我一起住在二层,可以给我作证的,可昨天他跟朋友喝酒去了,半夜里才回来,啊呀,这可怎么好?我是真的早早躺下睡觉了,我可以发誓!”
周晓京道:“你放心,我们只是查案,这些都是依照惯例询问的。”霍云帆绷不住暗地里直乐,心想你真敢说,头一回出来查案,还“惯例”!周晓京却没看到他高高挑起的眉毛,又问道:“那么请您说说榴宝的情况吧!”
孙妈妈听周晓京问到榴宝,脸上立时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气,“榴宝么?虽然我跟她一起做事的,可是一老一小,实在没什么话说,这丫头长得有几分姿色,又是伏侍这样的主子,整天打扮的妖妖条条,唉,如今的姑娘啊……”
周晓京怕她越扯越远,连忙打住她道:“她跟乔安琪的关系如何?”
孙妈妈挑起一边嘴角笑道:“榴宝嘴甜舌滑,很得太太信任,关系自然界是好的喽!”
周晓京拿出相簿子,递给孙妈妈看,问道:“这里面的许多相片都被拿掉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孙妈妈皱眉道:“刚才我说了,我在这个家里只管做饭,旁的一概不管——小姐可以去问榴宝呀!这个家的事,她知道的可比我多得多!”
周晓京冲霍云帆打了个眼色,霍云帆立即收到并回复,点点头,意思是说周晓京询问得非常仔细,他并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孙妈妈被带出去之后,榴宝也进来了,她十七八岁,尖脸儿,水蛇腰,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溜溜转,背后垂着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额前梳了虚笼笼的留海,雪青紧身袄子,葱白线镶滚,湖水绿的绉绸窄脚裤,外头套着******地子平金马甲。她脚上好像受了什么伤,走路一瘸一拐的。
周晓京打个手势,榴宝就老实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笑道:“先生小姐要为我们太太申冤哪,我们太太可是个大好人,不知是谁这么狠心竟然下得了手去害她。!”
周晓京道:“看来你们主仆关系不错啊!”
榴宝道:“太太这样体恤下人的主家,真是难找的很!只可惜我没福气,才找到这样一个称心的工作,这就又做不成了!”
这倒大出周晓京意料之外,“什么?你也是刚来的?”一面嘀咕,那为什么孙妈妈嘴里,好像榴宝知道乔安琪多少秘史似的。
榴宝道:“可不是嘛!我姐姐原是贴身伏侍太太的,后来姐姐嫁了人,才把我介绍过来,太太把我姐姐当成心腹,对我也是极好的!”
周晓京马上问:“那你姐姐现在在哪里?”她想乔安琪是个歌女,最了解她的只怕不是家人,而是多年伏侍她的丫头,所以找到榴宝的姐姐就很要紧了。
“姐夫是跑南洋的船员,这几年在南洋混得有点起色了,想要移民,几天前她们就坐船走了。”榴宝好像是知道周晓京心思似的,又说道,“小姐是想向我姐姐打听些事吧,可姐姐走的时候说,她们要到了那里之后才会筹划买房子的事,买了房子才有确且住址,等我姐姐安顿好了,给我说了住址之后,我立刻去告诉小姐!”
周晓京暗暗顿足,心想别说榴宝的姐姐一时联系不上,就算联系上了,南洋距浦江千里之遥,不料霍云帆平静地答道:“好,那就麻烦你了。”
榴宝道:“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太太是个好人,如今这么个结果,也太惨了……”
霍云帆和周晓京同时产生了一个疑惑,是什么原因,让家里的两个女佣对乔安琪的评价完全不同啊!谁说的才是真话?
周晓京问道:“还有一个问题,请你务必如实回答,乔安琪的身份是歌女,她结婚前后,是否仍有追求者对她纠缠不放的?陈敬夫先生对妻子如何?我指的是……”
榴宝水晶心肝玻璃人儿,立刻领会了周晓京的意思,正色道:“我们太太做歌女,当然少不了追求者喽!最近还有几位先生,追太太追得特别紧呢。听我姐姐说,没结婚时更多,但太太是个洁身自好的人,结婚之后,一发更没了来往!先生对太太体贴极啦!原本太太说,要我跟他们住在一起贴身伏侍的,可先生说要享受二人世界,就在后街上给我赁了一间房,只是太太有事时才叫我!”
连年轻的女佣人都不让住在一个屋檐下,看来陈敬夫对妻子果然是忠贞不二。
周晓京又问:“乔安琪的娘家还有些什么人?”
榴宝道:“就只剩下一个妹妹啦!唉,说起她们姐妹,也是叫人叹气,我也是听姐姐说的,太太父母去得早,她十几岁就出来做歌女,在浦江努力赚钱供妹妹上学,本来姐妹之间是极好的,可是后来太太的妹妹听说太太要嫁给陈先生,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不过也难怪哦,太太如今正大红大紫呢,完全可以找一个比陈先生条件好得多的。那时候紫榆小姐,哦就是太太的妹妹来到浦江,跟太太大吵了一架,好像紫榆小姐一气之下,还用花瓶砸伤了陈先生。既然紫榆小姐反对得这样厉害,陈先生跟小姨子的关系也可想而知,所以紫榆小姐连她的婚礼都没来参加。”
榴宝想了一想,又说:“有句话,或许我不该说,不过兴许对查案有好处——太太一向对那些追求者冷冷淡淡的,可是就在前几天,我在路上偶然看到太太跟其中的一位先生手挽手进过吉祥宾馆,我记人记得很准得哦!那个人绝对是来找过太太的人里的一个,可是太太当时理都没理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那个身材不高,是个胖子。”
难道乔安琪红杏出墙?她的死是否跟这件事有关?是情夫的因爱生恨,还是陈敬夫得悉了其中的情况或是自己或是找人来复仇?
周晓京又想到了那些被拿掉的照片,这案子到现在为此,得到的线索一大堆,可惜真真假假,千头万绪,不但没有让案情清晰起来,反起越发得扑朔迷离了!
周晓京的思维一脱缰,就有了片刻的停顿,霍云帆立刻给她补上空档,接着对榴宝说:“你说的这件事很重要,乔安琪的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我们得到的线索越多,才能织出一张更大的网,作到疏而不漏,虽然一时看起来是繁琐了些,可是只要用心思分析,总能把一件件事情理出头绪来。”这哪里是跟榴宝说的,分明就是暗示周晓京,周晓京默默不语,心里却想着,终究只有他,我什么话都不用说,她就知道我的心思。
霍云帆又问榴宝:“你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离开之后到午夜之前做了些什么?”
榴宝道:“先生住了医院,按说我应该晚上住在这儿陪太太的,可是昨儿下午我在街上被一个骑脚踏车的撞了,膝盖上磕破了一大块皮,太太就叫我早点回去休息了,我离开的时候,孙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回到住处,房东家的女儿来找我,叫我教她结绒线,我们一起吃的饭,聊天聊到八点多,她就走了,我就在屋里继续结绒线,到了十一点钟睡的。”
也就是说,她也没有时间证人。
周晓京听她说完,把方才积在胸中的那个问题问了出来:“你看看这本相册,你知道为什么会被抽掉了许多照片?”
榴宝只瞟了一眼,就说道:“还不是紫榆小姐反对太太和陈先生,所以那次吵架过后,紫榆小姐的照片就被拿掉了,这是主人的家事,我们做下人的哪里敢问?”榴宝说着眨一眨水灵灵的眼睛,悄声道,“不过,我猜想,十有八九是紫榆小姐惹怒了陈先生,太太怕先生不喜欢,才拿掉紫榆小姐的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