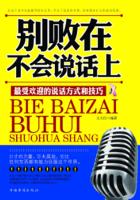苦涩的汤药灌入口中,带来无限的恐惧绝望。
君无双奋力挣扎,终于摆脱了钳制她的人,恢复自由。
她迈步逃跑,不想脚下踩空,咕咚一声摔倒。
无双茫然睁眼,发现自己趴在一张红木脚踏上,旁边是雕花架子床,霞影纱的帷帐未放下,用银钩束着钩在床柱上。
布置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
记忆的闸门随着她的思索霎时开启——
楚曜死后,假扮杂务兵留在军营里的无双与楚曜其他亲信一样,被定为失职之罪。无双试图向行刑者解释清楚她真正的身份,那人笑着说相信,转脸却命人按住无双强灌下毒药……
她不想死。
诬陷她的人还没得到惩治。
名声尚未恢复清白。
她不甘心……
那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她是来到死后的世界,还是没死?
无双犹疑地爬起身,发现自己竟然只比床板高了半个头。
伸出手,那肉乎乎、圆滚滚、藕节似的小短手明显不是她的。
再往下看,上身只穿了件绣鱼戏莲叶的红肚兜,胸前平坦无波,肚皮还微微有点鼓。
她变成了个小孩子?
正思忖着,听得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无双来不及做出反应,门口帘栊已被挑起,身穿天青色对襟襦裙、头戴翡翠明珠钗的少妇走进来,一见她就蹙眉道:“怎么自己下床来了?”
说话间,人已到近前,把光脚站在地上的无双抱回床上躺好,又拉过薄被盖在她身上,十分仔细地拢好被角。
“你呀,病才好了一点,怎么就顽皮起来,光溜溜的跑下床又着凉可怎么办?”少妇假作生气,纤纤玉指轻点无双额头,忽然手上顿住,奇怪道,“这是怎么回事?”问完又笑,亲昵地捏着无双的脸颊道,“你这小小一团的怎么可能自己下床呢?是睡的不老实跌下来的吧,额头都磕青了,真可怜,疼不疼?”
边说边把无双裹着被子抱进怀里,“娘给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
无双看着她怔怔发愣。
少妇三十岁上下年纪,生得甚美,容貌与她还有几分相像。
这是……娘?
无双六岁的时候,生母杨氏就过世了,所以她记不清母亲的模样,无法辨认。
少妇发现女儿呆呆的,故意逗弄道:“摔傻了?可别啊!你爹进山给你抓豹猫去了,让娘想想看,要是双双傻了把豹猫给谁玩好呢?”
无双闻言,全身颤抖。
生病,爹爹,豹猫……
她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这里是她家,眼前的人就是她娘。
她竟然回到了小时候?
四岁那年夏末秋初时,无双生了一场病。药苦难咽,身体难受,小小孩童,自制力不佳,免不了发脾气,哭闹着说要养一只豹猫。爹爹君恕答应了,在休沐时进山狩猎,却因为坠马受伤,昏迷不醒。杨氏衣不解带照顾丈夫,不曾发现自己怀有身孕,结果流产伤了身子,不到两年便香消玉殒。君恕苏醒后,双腿不良于行,身体也孱弱不堪,难复当初康健,在妻子去世后没几年也跟着去了,只留下无双与姐姐无瑕相依为命。
无双越想越心惊,尖声问:“爹爹去了多久了?”
杨氏瞥一眼靠墙条桌上的西洋座钟:“有两刻钟了。双双别急,傍晚前你爹肯定回得来,还会带豹猫一起,双双高兴吧?”
不,她一点都不高兴。
她什么都不要,只想父母双全,一家平安。
无双无助极了,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说得明白。说她未卜先知?说她死后重生?如此荒谬,又出自于一个四岁幼童之口,怎么可能有人会信。
她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一本正经地对杨氏诉苦道:“娘,我刚才做梦,梦到爹爹坠马受伤了。”女童的声音软软濡濡,再严肃认真仍带着几分撒娇似的嗲劲儿,倒是与无双说的话十分相配,而且毕竟是曾经历过的事情,说到后来,焦急混合着伤心,竟然鼻子一酸,眼泪上涌,眼看便要哭出来。
“傻孩子,那是梦,梦都是反的。”杨氏揉着无双的小脑袋安慰她。
如果真是梦就好了。
从小到大,无双不止一次期待过,某天早晨醒来,发现爹娘相继出事只是一个噩梦,她和姐姐依然有父母疼爱、保护,那样姐姐就不会被徐朗那个混蛋欺骗,二婶也不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打算药死她。
“夫人,肉糜粥好了。”梳双髻的丫鬟捧着托盘进来。
无双认得她是杨氏的大丫鬟白露。
白露忠心耿耿,主母去后,她像母鸡护小鸡似的护着无双姐妹俩,因此被总想从大房占便宜的二婶当做眼中钉,被寻了错处强硬地打发出府,无双姐妹俩几次派人去找,始终杳无音讯,恐怕凶多吉少。
无双抿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样一样来。为了改变娘、姐姐、白露和自己的命运,当务之急首先是爹爹不能出事。
她灵机一动,心中有了主意。
“爹爹不回来,我就不吃饭,什么都不吃。”无双踢腿揉眼,装作哭闹。
小孩子讲道理,大人一般都只觉得好玩好笑,不会认真听,那就唯有用小孩子的方式了。
不想杨氏一巴掌拍在她屁股上:“一时要宠物,一时要爹爹,一时让去,一时让回,到底想怎么样?谁教的你这么捣蛋?”
无双捂着生疼生疼的小屁股蛋儿,泪眼朦胧地抽搐。
娘怎么不按牌理出牌呢……
“爹爹受伤了,一直睡一直睡,都不理我,我好害怕。”既然闹不管用,唯有装可怜求同情,无双努力地摇动杨氏的手臂,“娘,求求你,求求你。”
女儿小鹿般清澈的大眼蒙着水雾,娇软童音求得杨氏心都化了:“好好好,这就去把你爹追回来。”
说罢,转头对白露道,“让人到二门传话,叫他们把侯爷找回来,越快越好。”
初秋时节,白日里天气仍十分炎热,房间窗户都支了起来通风,能清楚听见白露在院子里吩咐小丫鬟的说话声。
无双并没有因此放下心来。
他们能及时追到爹吗?
出事时无双年纪太小,还不怎么记事,许多细节都不清楚,若不是后来听人说起,甚至都搞不清楚来龙去脉。再加上这连自己下床都有困难、半点不顶事的小身板,她能做的实在有限,只能干着急。
君恕骑着大宛宝马一路疾驰,直到进了汝南侯府的乌头门才勒马放缓速度。
跟随他出门的四名护卫被远远抛在后面。
“老袁,谁要出门?”他不端架子,进了马厩看到管事正在备马,随口招呼询问。
“侯爷回来啦。”老袁连忙问安,“是小的要去找您呢。”
君恕皱眉:“找我干什么?家里有事?”
“不,是夫人说三姑娘做噩梦害怕,闹着要让侯爷您赶紧回家。”
一听闺女有找,君恕立刻把缰绳抛给老袁,摘下马鞍上挂着的一只藤篮,转身就走。
君恕一阵风似的飙进正院,速度快得守门的婆子才要福身他已走到房门口。
堂屋里,白露问安问了一半,手上就被塞了一只藤篮。
“你先拿着,一会儿听我说话再拿进来给无双。”君恕吩咐完,自掀了帘栊往里去。
无双一碗肉糜粥还没吃完,就见到一个身材魁伟的男子挑帘进来。他浓眉大眼,神态威猛,虽与她记忆中的模样十分不同,还是能够一眼认出是父亲君恕。
“爹爹!”无双激动得跳起来,差点撞翻了杨氏手中的粥碗,也忘记了自己人在床上,迈开小短腿朝君恕扑过去。
幸亏君恕眼明手快,一把抱住无双,将她举得高高的:“双双想爹爹了?”
无双狠狠地点头,张手搂住君恕脖子,依偎着他泪盈于睫。
原来没受伤时的爹爹高大又强壮,说话中气十足,与印象中枯瘦冷漠,只能坐在木头轮椅上,去哪儿都要人推着,连喝一杯茶都不能自理的病人判若两人。
感觉到有泪珠落在自己脖子上,君恕抱着无双颠了颠,问:“怎么哭了?谁欺负我们双双了?告诉爹,爹帮你打他。”
无双蹭着他不说话。
杨氏没好气地嗔道:“谁敢欺负你的宝贝女儿,她在家里向来都是横着走的,她不欺负人就不错了。”
君恕忙于公务,教导孩子的事情自然多由杨氏承担,两人早习惯了配合着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他香了香女儿肉乎乎的小脸,笑道:“我们双双又乖巧又懂事,怎么可能欺负人。”
换了平日,这般夸奖早让无双笑逐颜开,谁知今日却不管用。
君恕只好祭出杀手锏:“双双快看,爹爹给你带了什么回来?”
白露立刻将藤篮拎过来。
篮子里铺着厚厚的红绒毯,毯子上侧卧着一只周身长满铜钱花纹的小奶猫,它明显刚出世不久,眼睛都还没睁开,个头只有巴掌大,全身毛茸茸的,像颗小毛球一样可爱。
“豹猫?”
都说她曾经见过,格外喜爱,才会哭闹索要,可无双自己偏偏没有印象,因而不大确定。
君恕点头道:“以后你可得好好照顾它。”
杨氏的关注点与女儿不同:“你出门都不到半个时辰,进山单程都不够,怎么会猎到的?”
“在城门外遇到郢王,正好他前日才猎了一大两小三只豹猫,就送了我一只。”君恕道。
杨氏奇道:“我们什么时候和郢王府攀上了交情?”
“虽然只是点头之交,但见了面总免不得寒暄几句。”君恕素来豪爽,又是个恩怨分明的性子,今日承了郢王的情,自然少不得美言几句,“陵光卫成立半年多,做出不少惊人之事,让朝中为官者人人自危,生怕被他们盯上全家遭殃。我原也以为他小小年纪,便心狠手辣,定不好相与,不料今日一接触,才觉他十分谦和有礼,待人周到,又博闻强识,难怪陛下看重。”
郢王?
楚曜?
无双抚摸豹猫的小手僵住。
怎么会关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