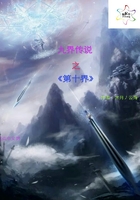邵知理守制期满,将若兰嫁出后,开始重操旧业,行走乡村,占卜堪舆。每日早出晚归,辛勤赚钱养家。
他以前在京城,因有父亲的朝奉托底,成天悠然地在家坐门等客,收入甚是可观。如今换了地方,名气尚未传扬出去,只能四处吆喝,辛苦不少,却收入了了。
天门已懂得体贴父亲,见父亲每日将卦褡朝肩上一搭,便出门去,很是不落忍,劝道:“父亲,你不用这样辛苦,仍和在京城一样,等人上门求你。”
知理抚摸着天门的头道:“为父不觉辛苦啊,我在家关得太久了,出去走走半是谋生半是散心,好得很哪!”
“父亲,你将阴阳之法教我,我来养活你和母亲。”
“爷爷临终前有过嘱咐,待你成年才可学习那些东西。你在家要是觉着闷,就好好把那本《淮南子》参详透彻,将来用得着。”
天门答应着,等父亲出门后,从书架上找出《淮南子》,温习一遍,似有所悟,又觉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只让他读这本书,难道其中藏了什么秘密吗?
天门本不是循规蹈矩的孩子,有疑必猜,凡猜必破才肯罢休。他读到《淮南 子》书中关于阴阳学说的记述后,看不大懂,记起父亲曾手不释卷研读过一本画 了八卦图形的书,便去父亲的房中翻找。
严氏问他找什么。他说书房里的书都看完了,要寻父亲读的书来看。
严氏拦阻道:“你父亲说他的书不许你动。”
天门笑说:“不让动就不动。”
天门出来去找响地。响地已长成大姑娘,在邵家几年,经严氏精心调理,乡野之气尽皆剥去,出落得清新明丽,识书达理,颇具大家闺秀风采。
响地正在练习小楷,天门便站在她身后观看。响地捂了花笺道:“我的字丑,不许看。”
“妹妹在写诗吗?让我看看你写得什么?”
响地偏不给他,天门便去夺,响地站起来闪躲,天闪环臂抱住她说:“看你往哪儿藏。”
响地小脸绯红,嗔道:“给你看便是,用得着这样用强吗?”
天门和响地脸对脸抱着,相持片刻,都有些不自然。
天门在响地腮上亲了一口说:“我看你就够了。”
响地扬手轻轻打了天门一下道:“天门哥哥,你学坏啦。”
天门放开响地说:“妹妹帮我做件事,去咱娘屋里把父亲常看的书偷出来。”
“不去。”
“怎样才肯去?”
“要去你去,我可不做偷偷摸摸的事情。”
天门说:“好吧,等我把娘诓你屋里来,你拖住她,我去找书。”
两人略施小计,将严氏哄到响地屋里。天门便钻进父母房中,从容地翻找起来。
知理的书天门小时候见过,有些印象,如今翻出来,全都似曾相识。
天门望着一堆“推背图”、“河图洛书”“奇门遁甲”倍感亲切,恨不能全抱回自己房中。想了想,怕父亲发觉,先拿了一本《奇门遁甲统宗大全》去看。
自此开始,每日等知理出门后,天门和响地一唱一和,瞒过严氏,将知理房中的书偷出,供天门研读。就这样,早晨取出来,傍晚还回去,数月的工夫,天门把父亲的藏书全都读完了。
中国的阴阳术数学问,博大精深,门类繁多,各类别里又分出诸多流派,极为繁琐。
若是单读一本,或专研一类,常使人陷入困惑之中,并不能轻易参透其中的奥秘,但将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籍通读之后,便可触类旁通,豁然开朗。
天门是何等的聪明,他读书从来一遍便可记住,有生涩的地方,再读一遍也可化解。若是有一本书能让他读三遍,他会对那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除《淮南子》之外,还没有那样的作者。便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天门也只读了两遍。
这一日,天门对《抱朴子内篇》里所述的炼丹术感了兴趣,便找个借口溜出去,跑到药堂买来雄黄、云母等物,再到母亲的妆奁里偷来金银首饰,在院中架起铁锅,抱来木柴,要炼出不老之药来。
严氏好奇,问他:“我的儿,你这是要做什么?”
天门边生火边说:“我给您炼长生不老之药。”
严氏哭笑不得:“你快住手吧,小心走了水。”
响地问:“天门哥哥,世上真有长生不老的丹药吗?”
“我读的书上有。”
“可是那些写书的人也没活到现在啊?”
天门抹了一脸锅灰,仍不罢手说:“你怎知没活到现在?说不定在哪座山里隐着呢!”
正说着,忽然外头传来敲门声,天门开门见是曾国藩。
曾国藩一见他的狼狈模样,笑道:“天门,你这是闹哪样?”
曾国藩一身寻常书生打扮,瞧不出是京里的官员。
天门上下打量着他问:“你被罢官啦?”
“为何这样说?”
“你没穿官服嘛!”
“我不为公事,只为访友,穿什么官服!”
“你不是向来官服整齐,志得意满的吗?”
这句话让曾国藩暗自佩服天门的观察力。一点儿不错,三年前,他在京城生活困顿,举债度日,却顾着体面,不管公差还是私事,全着一身官服示人,半是为遮掩窘态,半是为遇见同乡炫耀。
那时还是年轻啊,爱慕虚荣,注重光鲜。可是初入京城的士子,谁又不是这样呢?怕人看低,才处处朝高了做。如今大不同了,曾国藩经过一番历练,也渐渐在朝廷里有了声望,不必张扬也可自信满满。
曾国藩问道:“我现在这身打扮如何?”
“少了些官僚呆板,多了些儒雅风流。”
“哈哈,天门,真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这才三年的时间,你说话便和上书房那些教授一样的腔调了。”
“是吗?我师傅卓老先生可还好?”
“难为你还记得卓师傅,他已经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啦!”
“阿哥们都好?”
“阿哥们好不好,我可就不知道了,你生了一对千里眼,这事还用问我?”
“你先进屋坐着,我把这锅药熬了再和你说话。”
“你熬什么药?”
响地在旁答:“天门哥哥要炼长生不老丹呢!”
曾国藩大笑不止,笑罢说:“天门,炼丹要用炼丹炉,用铁锅怎么可以。”
“我知道呀,可是找不到那炉子嘛。”
曾国藩上去拽起他道:“客人来了,哪有不待客,自顾自玩的。别弄了,我们进屋说会儿话。”
两人携手进屋,响地端来洗脸盆,天门洗了脸,给曾国藩斟上茶,双手献上,然后一揖到地说:“曾先生,天门有礼啦!”
“这是为何?”
“谢谢当年曾先生的救命之恩。”
“言重了,那是我们的缘分,也是你自己的造化,贤弟,今后不要再提那件事,否则愚兄真要无地自容了。”
两人重新落坐。曾国藩道:“天门,到了石头城,读书的事情没有耽误吧?”
“一刻没有耽误。”
“那就好,赶明儿考个功名,凭你的天赋悟性,拜相封侯指日可待。”
“拜相封侯是你要做的事,我不稀罕那劳什子。”
“怎么?”曾国藩指指院中的铁锅道:“你要炼丹成仙吗?”
天门笑了:“有何不可!”
“令尊大人会瞧着你这样胡来不管?要学你爷爷,学以致用,入朝为官……”
“打住,正是我爷爷不叫我入仕途的。”天门说:“曾先生,你是大忙人,有事快说事,千万别耽误你拜相封侯。”
“这是要赶我走啊,天门,你小小的年纪,什么时候学会说话夹枪带棒的呢!”
天门抿着嘴笑说:“好,好,咱们好好喝茶。”
曾国藩踌躇着,欲借个话题把穆彰阿请托之事引出来,便道:“天门,我听说你曾在上书房和阿哥们摆过战阵,还记得吗?”
“什么战阵,做游戏罢了。”
“你看阿哥们哪个是可造之才?”
“你是要问谁能做将来的皇上吧?”
“可以这么说。”
“皇上问过我,我回答过他。”
“皇上问过你?”曾国藩想,如此看来,穆彰阿的话也并非全是臆造,皇上本就对阴阳之术着迷,敬畏天意倒也不奇怪。
“你怎么回答?”
“谁的年龄大谁坐龙椅啊!”
“皇上怎么说呢?”
天门瞧着门口的铁锅,沉思不语,半晌才缓声道:“皇上也不知道啊!”
曾国藩冲口而出道:“皇上已经手书了立储密诏,怎会不知……”
天门直直地瞪着曾国藩,他才意识到自己失了城府,一时不知如何改口。
天门说:“真弄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何都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之事。”
曾国藩道:“立储可不仅是皇帝家的私事,君强国安,君正民顺,为天下黎民百姓计,做大臣的岂可不关心此事呢?”
“叫你这样一说,是这个理。”天门道:“我用奇门遁甲排盘看看吧。”
“你会奇门遁甲?”
天门刚琢磨透奇门排盘之法,兴趣正浓,难得有机会一试身手,当即便净手焚香,将法盘排出。
曾国藩问:“如何?”
“看这盘口,皇上密诏上定的那人是六阿哥。”
“你再仔细盘算一下,这件事可不能有丝毫马虎。”
天门把玩着胸前的扳指,闭目沉思,却得到另一种暗示,暗示所指分明是四阿哥。
天门认为已识透奇门的玄妙,不疑自己排盘有误,执拗起来,暗道,我偏要说我排盘准。
天门对曾国藩说:“没错,就是六阿哥。”
曾国藩点头道:“好,愚兄明白了。”
天门不语。曾国藩从袖中掏出一张百两的银票,搁在桌上道:“这是穆大人的心意,你收好。”
天门仍在神游之中,曾国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然不知。直到将曾国藩送出门去,才自语道:“若兰姐姐遇到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