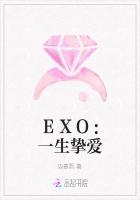今年学校剧场的演出活我理性地推辞掉一些了,我知道那样会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但也会造成长期依赖表演系那个团体,仿佛没有他们我就翅膀长不硬似的。
和罗纱在一个夜店工作的瑞德给我来了电话,我从剧场设计课上直接走出去接听电话了,以前我都是很受规矩的听课做笔记的。
“李柔,这里有个电影的试镜你来么?”瑞德问我。
“电影的,我当然要去啦,不然我这几年的表演都白学了么?”我兴奋地声音扬高,马上意识到是教室走廊赶紧又压低了声音。
瑞德说:“那你就快点吧?我怕过一个小时后机会就被人捷足先登了。”
我心跳的快到嗓子眼了,这多不容易啊,忽然想起一点赶紧地问:“瑞德,我应该准备什么服装或者道具么?具体什么角色。”
“黑帮苦情烟花,快来万华的土地宫门口,导演主要看演技的。”瑞德说完就挂了电话了。
风尘女子,苦情花,那得有多苦啊?生活中我看见的风尘苦情花就是基隆庙口的栅栏屋,那种形同荷兰的玻璃橱窗里面是妖艳女郎待价而沽,而栅栏屋就是很苦情的风尘女子了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我最近剪了包住耳朵长度的鲍伯头,也不知道导演看了满意不?反正影视的试镜我是第一次,心里忐忑着头发的长度还是驱车往市区老街万华。
大叔颜最近又有一个联合名人的摄影美术联展,他一早就去展场布置监督,然后又是在他工作室准备为索非亚洪的巴黎时装秀跟拍制作影像的前期工作。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恋人之间应该分享彼此的兴奋。
“我要去一个电影试镜的片场了,你在忙什么呢?亲爱的。”我戴上无线耳机和他通话。
“哇!我的小柔终于要去电影的片场试镜去了,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我不忙我也过去看看啊。”某人手上忙着事情,听那声音就知道是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位置说话的。
“万华的土地宫,你如果忙就不要来了啊。”我其实不希望他去,毕竟是我第一次去影视的片场。
“会的,那个你的生日也就快了,我还有新的惊喜给你啊。”某人还是手上不停止嘴巴慢条斯理地对我说着话。
四十分钟后到达万华陈旧街道的土地宫庙,很谨慎地把车停好,欣赏了一下街景。
这里最新的房子是三十年前的红砖墙,最陈旧的是六十年前的灰色水泥包裹沙土混合的墙壁屋子,破败当中永远鲜活的七彩琉璃瓦就是各种神明的栖息地庙堂。
我出生的岛屿似乎人们永远都喜欢在这样破败的街巷中取景拍片,说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是这些旧屋子了。
我才刚刚走到土地宫庙门口,瑞德就远远看见我跑来:“你就不会快些么?人家导演现在是完全的新人觉得没有演技,熟面孔么最近都很多人风评很不好,只有你这样的戏剧科班生面孔也比较新,我才大力推荐你的。”
他这样一说,我大概心里有了数,一路甜笑着往导演的方向走去。
“杨导,我朋友李柔,北艺大表演系的。”瑞德把我介绍给清瘦有点酷的导演。
我被导演严肃冷酷地盯着看了十五秒说:“副导演带去剥皮寮,记台词然后过个镜头吧。”
剥皮寮,听名字好让我发怵啊,我在夜总会感觉是刀尖跳舞的日子,这种地方的女人就是直接滚钉板的日子。
据说这里六十年前到二十年前都是站街的流萤和栅栏屋的女人讨生活的方寸之地。
这样的屋子对外只能够看见一个铁条栅栏小窗户,里面是十平方米的地方铺着鲜红床单的大床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
旁边的衣橱连接的梳妆台上烟灰缸和简单的口红化妆品,角色的戏服是一个廉价粉红色吊带背心睡衣,配角是一个烫成花头的老鸨兼管理者阿姨,脸妆把法令纹突出让她脸上颧骨高耸带着狰狞的咒骂我这个烟花。
出场两次,每次的台词不到十个字,但副导演说:“水月是这部戏里的灵魂人物也是唯一的青春角色。”
虽然台词我看一遍就记住了,来到这个房间进入这个氛围我也把角色的悲苦无奈和纯真揣摩到了,我还是有些紧张和我对戏的会是谁呢?
我台词还没有说的时候冷酷的杨导演进来了,他在门口双手环抱着把坐在鲜红床单上的我从各个角度都看了有足足三分钟。
“就你吧,头发的长度不用改变,唇妆不用化,要记得啊。”说完他就出去了。
副导演和穿着怀旧花衬衫手臂画满假刺青的瑞德过来了,瑞德看样子是参验黑帮年轻流氓的,大大的耳环也没有摘下来倒是也很个性,很适合流氓的角色。
副导演也是怀旧的帮派流氓服装,他对瑞德说:“饰演傻三的那个韩国仔叫虾米金成武的有福气啊,这么漂亮的新人和他对戏,要是我多好啊。”
他们似乎有意让我听见,我也是听过有学长姐们说片场的人就手用戏文叫荤话的也是正常的,我笑一笑没有当一回事情。
我的片断因为和我对戏的人听说还在别的片场排戏呢,我就等在旁边看瑞德他们排多人的戏份,今天心里高兴我找个薄外套把戏服裹上走出去买了一箱饮料请瑞德和副导演喝。过了一个小时,剧组写着大字“堂口”的车开过来土地宫庙门口,我看见那黑色的大字才知道这部片名字叫“堂口”。
大车上下来几个演员幕后人员刚从其他片场回来土地宫这个主要片场,我看背着化妆箱的崔和穿怀旧花衬衫的金成武也下车了。
李柔,是你啊!“崔一眼看见我快不走来。
”我就说,我们会互相帮忙在一个圈子里成长的,想不到真的就。“我一时高兴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