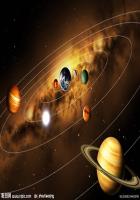房东走后,门刚关上我婆婆就爆点了:“我就知道你这种灾星带不来什么好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就是因为你,我又要没有地方去了!”
“你现在的生活是谁给你的!”我也实在受不了她这样无理取闹了,在我最需要家人支持的时刻,她不但没有给予我帮助和安慰,反而在后院起火。她被我噎了一句,气的不行,抹着眼泪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们就把这笔账算一算,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就把钱算清楚还给我,以后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她说着还真的从衣兜里拿出来一张纸,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我这些年的吃穿以及上学费用,总计三十多万。
好巧合的数字,说到底,还是惦记着我银行卡里的那些钱。
我怒极反笑,看着她问:“你确定,我把钱都还给你,你就再也不来纠缠我?”
我婆婆可能也没想到我能这么说,她愣了一下,然后理直气壮的说:“我确定,绝对不纠缠!”
我以为这么多年,没有血缘关系,最起码的亲情也是有的,可却抵挡不起三十万的诱惑。
我点点头说:“好,过几天我找公证处咨询,如果确实能办理,我们就将这些年来所有的帐都算清楚。”
我婆婆突然又开始啧啧:“到底不是亲生的啊,现在我是终于明白了,外面的野狗喂一喂还能懂得感恩主人,你就是喂不熟的狼崽子,说翻脸不认我们就不认我们了啊!好啊,瞿禾,你翅膀硬了,觉得我们累赘了,好,好,好!”
只有我知道,她好像在谴责我没良心,不过只是让自己的良心不受谴责罢了,说的好像是我没良心抛弃他们一样。但其实,私心又觉得那三十万有着落了,她嘴角分明是带着笑意的。
我懒得和她多说话,天已经快黑了,我穿上黑色的长风衣,戴了口罩出去透气,一直在屋里,我已经受够了。
接近六月,申城天气逐渐转暖了,但我自从生完孩子到现在身体一直恢复的不太好,夜晚的风吹过都会觉得寒凉,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我其实很不喜欢下雨,哪怕夏季的雨带来的只是一天比一天更暖的天气,可每当天空阴沉压抑,我就觉得自己心情也沉闷的透不过气,本来内心积压的阴霾就太多,环境若再如此,就会让人心里更不舒服。
我在外面一直逛到快九点,天晚了,房产公司还有很多家开着,我随意进了一家大概看了看房价,今年房产增值很快,申城的房价几乎在飞涨,至少在靠近好地段的位置,我是买不起的。
我大概说了说我的需求,她说按我现在的状况,首付只能拿出二三十万,可以考虑买靠近郊区的小户型,交通还是方便的,就是距离城里比较远,学区也没有这边好。
我和瞿采生活,也不需要什么学区,反正也不可能会有孩子。
回家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我以为不可能有人继续蹲守,便放松了警惕,却没想到一个戴着兜帽的男人突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站在我面前就问了一句:“瞿小姐么,瞿小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你是和东昭凌之间出什么问题了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是被抛弃了么?”
我站定,平静的看着明显有些焦急的他,浅笑着说:“追明星习惯了是么?”
他有些不明白我的意思,还想继续开口,真的是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说出好几万个字来。
我阻止了他:“你不用问了,干涉别人的生活,侵犯他人的隐私,法律上都讲不通,更不用提道德。”
他这才好像将我的话听进去了,也没方才那么着急了,平静了不少,语速也正常起来的说:“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其实你说还是不说意义也不大,我要是不问那就是我失职。”
我笑着望向他:“对啊,我说不说有什么区别?反正你们早就习惯胡编乱造,愚弄大众了。”
我绕开他想走,他突然拿着相机拍我,我只觉得刚才一番话都传到牛的耳朵里去了,我回头看着他,他还在咔嚓,虽然我不停的告诫自己要忍耐,但脚步还是忍不住的朝着他走了过去。
他第一个反应是想保护相机,我伸手抓住他的相机一扯,相机带子质量太好,没拽下来,他用肩膀撞了我一下,没撞开,便将相机更是直接抱在怀里,一副打死他也不能弄坏相机的样子,我抢了半天都没能成功。
他更阴,也不知道跟谁学的,突然伸嘴就要亲我,这倒是真管用,我猛的向后一退,他彻底将相机抱进了怀里。
他倒是得意的看着我,我尚未发怒,身边突然冲过来一个人,一飞脚就将他踹倒在地上了。
我吓了一跳,待看清来人是东昭凌时,那个记者已经被他几拳狠狠的打蒙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东昭凌怎么会在这里?
东昭凌回头看了我一眼,和我熟悉他的样子完全不同,往日的淡然和温和都不见了,他眼睛闪着野兽一样的光,只剩下凶狠和愤怒,好像还没发泄够,转头抬手又要打那个记者,被我狠狠的拉住了。
“别打了!他已经晕了!”我大喊出声,东昭凌没听到一样,用力推开我,拎着记者的衣服领子将他拽起来,直接将记者扔进了绿化带里,他还要冲过去打,我用尽全力抱住他,险些都没能拖得住。
“东昭凌,别打了!你怎么了,不要打了!”
他带着我向那个记者方向移动,记者倒是有些清醒了,看着东昭凌野兽样的朝他走,吓得不停向后退,腿可能软了,站不起来了。
“你把相机放下,赶紧走!”我对他喊了一句,他下意识的还想保护相机,但东昭凌几乎失控的样子真的吓坏了他,他还是将相机取下来放在地上,连滚带爬的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