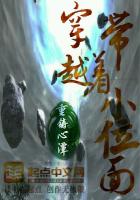他全身****地瘫坐在血液里,泪如雨下。
阿里萨加猛地感受到了别的信号……他不知道那种信号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因为那是被镌刻在血液里的。他也感觉到风了,一丝又一缕的风掠过他的皮肤。这条巷道不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他想起了男人的话……那些盯上他的人,那些人来找他了,他们是来杀他的!
阿里萨加顾不得再流泪,转身就跑。
在人形的时候,阿里萨加从没有跑得那么快过,即使是在最关键的比赛中的最关键的单刀,也没有那么快。他仿佛在这两只腿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自己当成了一台机器。他不再是那只轻巧灵敏的雪豹,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几近****,浑身都是血迹。他知道他已经被路边的几个人看到了。可不管他跑得多么快,跑经的地方是不是有人,有灯,都好像有个影子跟在他身后,不远不近,跟在暗处,就是甩不掉。
他逃回了家,冲进卧室把房门锁上,靠着门剧烈地喘息着。
外面没有声音,好像没有人追过来。
阿里萨加松了口气,转过身就看见一身白衣的男人站在窗外流进来的月光间,手中的刀光无比清亮。
阿里萨加瘫软了下去,无法抵抗,也无语争辩,如同羔羊,任人宰割。
窗户突然破碎了,在纷洒的碎片之间,黑风衣的男人滑了进来。白衣男人的两刀都刺空了,黑风衣的闪躲无懈可击。两个人一前一后,从窗户逃了出去,消失在了十三层,一夜都没有回来。阿里萨加倚靠着门坐在地上,心如死灰地望着窗外的圆月。
一夜过去。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黑衣男回来了。他把阿里萨加从地上扶了起来,如同搀起一具死尸。
“跟我走吧。”他轻声说,“我会教你控制自己的畸变,我会教你怎么在这个世界里存活下去……你会逐渐明白的,我们并不是那种罪无可恕的东西,你有自己的原则对么……那么,就坚持着你的原则活下去。”
似乎,印象里,这是阿比盖尔唯一一次用那样的语气和自己说话。
阿里萨加有些呆滞地看了一眼男人,点点头。
男人没有食言,这七八年以来,阿里萨加一直跟在男人身后,无论发生了什么,男人都没有抛弃诺言甩开他。他始终没有融入种族的圈子里,但阿比盖尔没有食言,该教他的,他全都教给他了。
他不再失控,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畸变过。每次到月圆的夜晚,他仍旧会感觉体内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温柔地冲撞,可是他只会望着圆月失神地发呆。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和阿比盖尔一样,生活在这个种族里,又仿佛独立在这个种族之外。
一晃已经这么多年。
他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他和那个男人一起并肩站在夕阳落下的山坡上,看天边的晚霞。
“零护卫不是失控的种族,”他轻轻地问,“为什么,我们就非要水火不容呢。”
“阿里萨加,以后你会明白的,不是我们主宰着命运,而是宿命困囿着我们,说到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有什么选择的权力呢?”阿比盖尔默默地说,“宿命就是那么无奈的东西。”
如今想起那句话,阿里萨加心中还是深深的悲凉。
烟抽完了。阿里萨加把烟蒂放在脚边,看着它被雨水熄灭。他忽然又掏出了那盒红头火柴,把火柴全部拿出来,攥在手中,然后全部擦亮,轻轻地掷了下去。
那些燃烧着的小木杆,就像山间飞舞的萤火虫。
煊徵和漪亦岚默默无言地伫立在雨中,凝望着眼前的景象。
这座城堡,就仿佛是突然出现在雨夜的森林里的一样,让人措手不及。
谁也不会想到在树林间会有这么一座古老而破败的城堡。它周身灰黑,墙壁上透露出岁月风化的痕迹,仿佛一头沉睡了千年的兽,并让人感觉若不是他们的打扰,它还会一直在这里沉睡下去,绝不醒来,直到世界的终结。
那个时候,它的身躯才会腐化成一堆瓦砾,与它漫长的荣耀的往事一同长眠。
这本来也应该是它的宿命。
可如今,两个不速之客闯入了。
煊徵慢慢地走近,抬手摸了摸墙壁。他想确认眼前的画面是不是真实的,还是他的视觉欺骗了他,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墙壁很粗糙,手指稍微一用力,还能扣下湿润的粗粗的颗粒来。煊徵默默地在指尖碾碎石粒,感受着石粒滚动的触感。抬起头望着城堡的顶端。
他忽然想起了《零夜风瞳录》中的记载来了。书中说,在最古老的年代里,魔护卫为了躲避银瞳战士的追杀,就跋山涉水,寻找一片人迹罕至的深林或者高山上的洞穴,聚群而居,外出觅食也成群结队,以保存种族的火苗。那是银瞳战士最光辉的岁月,几乎把魔护卫一族打回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为了更大效率地消灭魔护卫,颜瞳会成立了“巡猎团”,“巡猎者”们漫山遍野地寻找魔护卫的聚集地和洞穴,然后发送信号,把聚集起来的魔护卫一窝端。
每个银瞳战士都向往着那段荣耀的岁月。
但那几乎就是魔护卫历史中最黑暗的阶段了。书中说,“洞穴深处暗若永夜,惧怕处所为外所知,因无明火”,那就是魔护卫在古老岁月里的聚集之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里面,“以焰作浴,以吼为歌”,等待力量的孕育和恢复,同时期盼着对三族复仇的一日。
书中所说的居住之地都是天然形成的洞穴之类的,十分低调,可从没听说过魔护卫会在鲜有人踏足的地方建一座城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