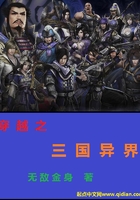我在丹丹家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起了一个大早,丹丹起的更早,她把稀饭做好了,早点也买来了,我与她煞是一对新人甜甜的吃着早饭。丹丹脸上掠过阵阵红润,挂满了欢心的微笑。
我告诉丹丹:“今天我到那两个小队熟悉一下情况,接触一下群众,明天正式上班了,这是大队领导安排的。”
她问我是不是马上就走,我说是的现在就走,过两天再来。她抱着我迟迟不肯放,哽咽着对我说:“我俩刚在一起,你又要离开我,我想你啊。”
“丹丹,我也想念你,我真想和你天天在一起,可我要工作去。你常常到我家去,我也常常到你家来,这样你我一样得到快乐。你也可以到我工作的地方去。那两个小队一个叫花园,一个叫张底,你想我的时候,就到那里找我。开学以后可以在星期六、星期天去,我在那里等你。”
丹丹不断地喊着:“涛涛,涛涛。”
“我会抽时间到你家里来和你在一起。”丹丹送我到雨山头十字路口,我告诉她朝南走第一个村庄是花园,再向南是张底,她点点头。
张底在我家南头,过一个田冲,翻过一个小山坡,再穿过一个田冲就到了。
我在家吃了午饭便去了那里,一路上我心情有点紧张,倒不是怕什么,这是我走出校门后第一次走向工作岗位,我也没学过会计专业知识,能否做好会计工作,心中底气不足。
我到了村头见社员们手拿工具正准备上班,他们中一些人我认识,我与他们每一个人打着招呼说着话。他们见来了新人挺高兴的,有的说新会计来了,有的说十天前就听说你要来,这些天没见到你,都以为你不来了,你还是来了。
有一个老头湊近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涛,家住唐底生产队。”我这样回答他。
老头抬起头,把眼珠一转笑了,他说:“周大财家孙子,小五侄儿。”小五是我姑妈,她家就在这个生产队。
姑妈来了,我叫着她:“姑妈”,她高兴地答应着:“唉,涛涛来了。”
我隨着社员们走向田冲,正说着话,一个人对我说,队长来了,并甩手向东一指,我一看此人大高个四十来岁,头发大背,抹水梳得精光发亮,一身衣服虽旧但整洁无补丁。脚穿一双力士鞋,肩扛一把铁锹。
我向他走去,大声地喊道:“队长你好”!队长笑着答道;“嗳,周涛你来了。”他伸出手与我亲切地握手,他的手粗糙有力,脸上晒得黝黑,满脸的皱纹纵横交错。
我望着他说:“请队长多关照”。
“大队唐书记跟我讲过了,不要紧的,不就是当会计么,慢慢来学习就会了。”队长的话增强了我工作的信心,我顿时感觉到队长对我是真心的,有这样的好领导,我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队长告诉我他姓张叫张传余,原先是副队长,刚当队长两个月。
张队长带着我看了生产队公房,所谓公房就是生产队集体盖的房子,做堆放粮食、农具等用途。走近了我看到公房大约两百平方米,土墙抹得平整光滑,屋顶是小麦麦秆扑扎的。
公房里的四周堆满了农俱,中间空着,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南头拐角放有一张木床,东面向里一道门上了两把锁。张队长说那是粮库,床是看公房的老头晚上来睡的。
张队长打开了西面的一扇门,这是一间办公室,约三十平方米,四面墙壁粉刷一新,南北两面大窗户对开着。一张三抽两柜的办公桌临窗而放,一张木椅配对着办公桌,八张方凳靠墙放着。
我们打开了窗户,一阵阵凉风吹过,我还没来得及感叹,队长说:“这是前任队长的功劳,他当队长的时候,时常来这里歇脚吹牛。”
张队长突然想起什么,一时半会地又想不起具体的,急得拍打着脑门团团转。
我说队长你不要着急慢慢想,队长想起来了,他说:“周涛,我听书记讲你当两个队会计兼阶级斗争观察员?”
我说:“是的,书记也是跟我这么说的。”
张队长笑个不停,足足笑了两分钟,他对我说:“书记不是害你么,他还是你表叔呢,你没想想,你这个阶级斗争观察员职务一旦公布出去,哪个群众敢挨近你呀,都不理你了,你还能站住脚吗,那你回唐底的日子就快了,还当什么会计呢。”
“书记只不过这么说说,也不是什么职务。队长我听你的,不宣布这个职务。”
队长沉思了一会儿,压低了嗓门很认真地对我说:“不但不宣布,而且不能干这个事,哪有阶级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被没收了,谁 跟谁斗哇,那不就是群众斗群众,自己斗自己么。周涛呀,你千万不能干这个事。”
听了队长一席话,我沉思了许久,很多很多人不敢讲的话,他对我讲了,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和他相比我太稚嫩了,我情不自禁对他说“队长,你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扶着我的肩膀说:“没事的好好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