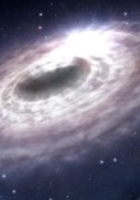列位看官兴味老高,刚听完了杨家将,又想听李师师。既然如此,那就让我这说书人柳麻子再给大伙儿上演一通李师师的传奇。不过这李师师的传奇也是整个盛世末年的传奇,牵连广大,几位关系重大的人物更是非用浓墨重彩宣说不可。
这个故事我已经说过不下十遍,列位想必有不少之前就听过。听过的请先安歇封口,不要多嘴,保证此番说的又不一样。
不瞒列位,我本人可是见过李师师真容的。那李师师名动汴京四十年,却还是跟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样年轻。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李师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第一个李师师红了二十年,之后换了第二个李师师继续红了二十年。花容月貌的女人养护得好,老得也慢,因此上,最后靖康之乱时,第二个李师师实则已有四十,却还像二十五六岁时一样细皮嫩肉。
自古道红颜祸水,这红颜自然是红颜,但被为何却偏偏被称为祸水?古今美人无端都受此妄语,真是有失公道。例如那李师师,这祸国殃民的帽子实在是不能扣到她头上。那徽宗皇帝要宠她,她又有什么办法拒绝呢?皇帝为了她不理朝政,难道也是她的错?就算没有李师师,徽宗也不会打点朝政,只不过换个花样玩儿罢了。
列位看官,你们最关心的莫过于靖康之乱以后李师师的下落。大家猜想,李师师的结局可不会好,南渡的人把她当做红颜祸水,不会接纳她,她到最后无非就是那几条路,要么死于战乱了,要么就被金兵掳了去为奴为婢,要么随便找个人嫁了,要么就出家做了尼姑。不过我此处要演说的李师师却跟常言道的都不一样,列位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说起咱大宋,怎么都觉得脸上无光。积贫积弱,遍受欺负。
凡是做妓女这行的,都有个破瓜之年。什么叫做破瓜之年呢?就是把小女娃养到十三四岁,在妓院里选花魁,高价卖了处子之身。破瓜破瓜,就是见红的意思。那李师师所在的妓院,唤作仙山琼阁,那是全天下一等一的妓院。我十来岁的时候在酒馆当学徒,还见过那妓院。仙山琼阁并不是一栋高楼,而是一整个广阔的大园子,那规模比蔡京的宰相府还大。一进去之后,水榭画舫、戏台歌楼、流水青竹一样不少。那仙山琼阁的规矩复杂得很,雏妓破瓜分作三等,唤作选花魁、花王和花仙。花魁每年都选,一次参选的才十个人;花王每十年选一次,一次参选的有三十人;而花仙每二十年才选一次,一次参选的达到五十人以上。不过外面的人嫌麻烦,也就笼统称为花魁了。仙山琼阁广收天下美人胚子,当上花魁已算不错,花王更是一枝独秀,而如果一旦被选上花仙,那将来必定是仙山琼阁的头牌。两个李师师就是隔了二十年选上的花仙。
先说这头一个李师师。她四岁的时候就无父无母,被一个姓李的老妈妈收养。那老妈妈年轻时也是风尘中出了名的。年老色衰以后也还干这行,只不过成老师了,专门培养歌姬舞女。这女娃聪慧非凡,一老僧见了说她与佛有缘,就取名为师师。她自小就开始学各项技艺,笛箫、琵琶、琴筝、弹唱,无一不精。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仙山琼阁的美人探看中。美人探嘛,是妓院的一个行当,专门去各地网罗美人胚子,带到妓院深造。这样,李师师不久就赶上了选花仙,一夜之间就身价暴涨。你们猜是谁破了李师师的瓜?不是那柳永、秦观,也非苏东坡,而是那“云破月来花弄影,谁人不识张三影”的张先。原来是他,不错,正是他。那张先是何年代的人物?比苏东坡早了四十七年,比后来的徽宗皇帝更是早了九十八年。李师师选花仙那年,张先已经八十余岁,而李师师不过十来岁。老头子爱风流,偏生就有这种艳福。有他的自度曲《师师令》为证:
香钿宝珥。拂菱花如水。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
都城池苑夸桃李。问东风何似。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於珠子。正是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
任谁一看,都知这词写的就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这张三影对这小女娃还深情地很呢。
不过后来却事有蹊跷。列位可知,这第二个与李师师一夜风流的人是个雄武的少年将军。他与李师师共度一宿之后,放话说:“我才是破瓜的人!”此话一出,全汴京城都传开了,说张三影徒有文才,其实是条中空芦苇。
诸位且留笑在后头。古往今来,那些书生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三寸不烂之舌。这回总算是明白了,自古文人多无用,就一条舌头好使,其他地方都是废柴。据传张先听到流言后就整日憋在家里,终于气死了,享年八十九岁。
至于那少年将军,那可是大有来头。他名唤公孙凌,字高冽,是那三国白马将军公孙瓒之后。原先公孙氏一直生活在燕州,但大家也知道,本朝开国时燕云十六州被那辽人所夺。公孙氏这才举家迁入中原,祖宗几代都立志要收复失地,重返家园。公孙氏世代为将,祖上也曾随杨继业杨无敌打过仗。杨家将绝迹后,公孙氏也渐渐不为人知。不过公孙凌这人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将才。他天生神力,使的一把鬼头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在战场上当真是叱咤风云,杀神斩鬼。当年王安石变法,军力大为强悍。征西大将军王韶奉命西出阳关战那吐蕃大军,正当战事胶着之时,蓦地斜地里杀出一彪铁骑,个个手握斩马刀,当先的正是那公孙凌。那一战,杀得腥风血雨,昏天黑地,斩得敌军马碎尸、人断魂。王韶这才得以一举收复河岷五州,辟地两千余里。经此一战,公孙凌大名远扬,胡儿被杀得胆寒,送他一个诨名叫做追魂刀。至今吐蕃国,要是有小儿不乖,他们老妈就吓他们说追魂刀来砍他们了。你们说说,这样的人物,岂不是大大的英雄?
过去的宋兵也有这么威风的时候,我一想起来就心魂荡漾,恨不得立马回到那个年代,披挂上阵,也随公孙凌的骑兵冲杀一阵,死了也痛快!可惜造化弄人,总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倘若当时的皇帝能委以重任,说不定就一举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之后也就不用受那金人的鸟气。可叹那可叹!可悲那可悲!
如此英雄了得,自然也只有美人才能降伏得了。公孙将军自从与李师师一夜春宵之后,心里头就再也放不下她了。加上后来王安石新法尽废,他也被招入京城顶了一个虚职。当年在吐蕃收复的河岷五州两千里地,竟然被那司马光全盘送还了吐蕃。牺牲了多少人,流了几条河的血,才打下了这片地,一下子都白费了。一想到这里,公孙凌就无比烦闷,连做梦都梦见死难的弟兄向他抱怨。你们说他能怎么办?头上挂个明威大将军,一兵一卒没有,整个光杆司令。每日里无所事事,除了喝酒痛饮,就是与那李师师缠绵缱绻。时人有诗单表那追魂刀公孙凌:
追魂刀在手,轻斩万人头。
丈夫百炼刚,只为花月柔。
又有诗曰:
一点绛唇青杏小,春来秋去瘦魂销。
美人如扇易飞雪,遗恨霸王空解刀。
你们说说,好好一个英雄人物,偏生落到这步田地,这到底怪谁呢?幸好这时候啊,出了一件怪事,他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他本来也娶过亲,老婆是枢密院大臣梁纯如的闺女,闺名唤作疏真,娶亲几年却从来没生出过娃娃。这回从天而降一个儿子,岂非稀奇?
那一天,他如往常一样,在城里溜了一圈,灌了两壶酒,还在仙山琼阁与李师师睡了一晚。第二天鸡鸣,睡眼惺忪地起床,却被枕边人一把抓住,听到身边慵懒的声音说道:“怎么回事?这么快就走?”
公孙凌就说:“最近贼寇越来越猖獗了,上头吩咐要一大早就巡城。”
李师师听了,假作嗔怒,说道:“既然有贼,晚上怎么不巡城?还来钻我的被窝。”
公孙凌声音浑厚,得意地说:“身为将军的好处就是可以睡大觉。”
绣床上红浪翻卷,美人手托腮,看着公孙凌背对着自己穿衣服,先沉思了一阵子,而后略显忧伤地说道:“我似乎应该离你远点。”
“为什么?”公孙凌弯腰穿鞋,没有回头。
李师师就笑着说道:“万一你跟贼寇交上了手,一个力乏,岂不是我害你丢了性命?”
公孙凌一听就说了:“这话要说也是由我来说。我本想离女人远点的,除非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
李师师一声娇笑,打了一下公孙凌宽阔的后背。公孙凌一个猛回头,转身就在她****上又肆虐了一番。完事后起身,罩上蓝绸子长袍,佩上腰刀。这时候,李师师就不开心了,嗔道:“你总是不懂温柔。”
公孙凌嘴角一扬,说道:“跟你耍温柔的酸文人还不够少?不嫌烦吗?”说着就要出门。
“你这一去什么时候才来?”
听了这无限伤心的话,公孙凌回头一望,看到李师师略显失落的神情。他便对她说:“我随时会来。只是等我来时,可别又像上回那样失踪了,教我一阵好寻。”
李师师说道:“哎,刚分别了大半年,正想与你尽情缱绻,你又要巡城。”公孙凌没做回应,起身就走,深怕再迟疑一会儿就再也走不开了。
列位,你们可知李师师失踪那大半年确是为何?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先略过不提,日后自有交代。
再说那公孙凌出门时,晨雾还未消散。他手握刀把穿过大街小巷。在一家酒楼停下,买了两坛子酒,十斤熟牛肉,十斤酱猪耳。吩咐一个伙计挑酒,自己一手提牛肉,一手提猪耳,往城防而去。与巡夜的众官兵喝了一会儿酒,对他们说:“最近想来劫狱的贼人不少,别跟卧底山寨的眼目断了线,盯着点那些个不安分的。”这话说的可是威风十足。
然后公孙凌就回自己的公孙府去了。一进门,里面的奴仆就一股脑儿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地说出大事了。
“昨夜来了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死活非要说是跟你生的。”
“还说她养不起,要你留他在身边。”
“少夫人一早就回梁府了,呕气得厉害,整夜都恍恍惚惚的。”
“老爷在城外钓鱼不知道,不然准气疯了。”
“少爷你到底欠了多大的风流孽债啊?”
“老夫人还在堂上等着你呢。”
被这七嘴八舌地一闹,公孙凌好容易才整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二话不说,推开众人,径直到堂上。见了自家母亲坐在上首,端着个茶杯喝茶,神色严峻,连忙一个箭步奔到跟前跪下。他母亲余夫人当年也是将门烈女,如今这幅景象,公孙凌怎么不慌?
余夫人开口了:“怎么不说话啊?”
“孩儿无话可说。”这时候似乎也只能这么说了。
“知道就好,关三天禁闭。”余夫人放下茶杯,依旧不温不热地说:“起来吧。”
公孙凌起身后等着责罚,果不其然,母亲凑近来兜头就说了一大串:“儿子啊,你真厉害,我刚跟你说起我想抱孙子,你就给了我一个孙子……”
公孙凌登时傻了眼,越发不知说什么才好。余夫人还在念叨:“那娃娃跟你一样乖巧,一双眼睛骨碌碌转,跟个玛瑙似的。没错,准是你生的,跟你刚生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也挺好,疏真嫁进来之后还没怀上呢,这样,先有个孙子让我抱抱,平日里,也好有乐子了。就像把我的小凌儿再养一遍,所有没教会你的都可以再补过来教他……”
听着这些话,公孙凌所有的忧虑都一扫而光,春风满面,拉着母亲的手说:“好了好了,娘你别唠叨了,带孩子来的女人呢?我还不知道认不认识呢。”
余夫人一听,故意调笑他:“小的来了,大的你还不放过啊?”
公孙凌就说道:“娘你别取笑了,她人在哪儿?”
一想起自己放浪的生活,他就一阵颤栗,也不知是哪个苦命的少女无路可走只好把孩子托给他养。但他很好奇,因为想来想去他也只是出没于妓院酒楼而已,睡过的女人虽多,但都是歌姬舞女、名妓戏子,不会有良家少女。所以他着实想知道这神秘女子是谁。
只听得余夫人说道:“我也没见过那女人,听李妈妈说,怪可怜的,在府外哭了一夜,求把孩子留下。李妈妈不想惊动我,也不敢惊动疏真。她见那孩子长得讨喜,又念在当母亲的一片真情,就做主留下了。之后,那女子就不知所踪了。”
“是这样。”公孙凌沉默了一阵子,竭力想回想起一年前接触过的众多女子,却怎么也无法勾勒出一副清晰的面容。已经在空中消散的花香,又有谁能捕捉得到呢?
公孙凌问:“那孩子呢?在哪儿?我还没见着呢。”
“孩子在里面睡着呢,你见了准喜欢。”余夫人说完,扭头对身边的丫环流霞说:“带少爷进去看孩子。”
流霞也调皮了,做了个鬼脸,笑着说:“现在该改口叫老爷了吧。”
余夫人一听乐了,却说:“哎呀,那我岂不是成太老夫人了,转眼就成老太婆了啊,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
公孙凌慌忙进屋,看见一个大红的襁褓,就过去抱起那小娃娃。生的是白白嫩嫩,一双小手蜷在胸前,说不出的乖巧可爱。那小娃娃将来也是大有作为,且与那李师师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