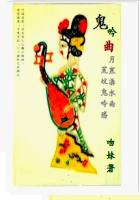堂叔家的地基坑里打过夯了,砖也都排好了,还没开始砌底层。地基坑里发出那光明明灭灭,幽蓝幽蓝。这光的色彩并不奇怪,电子时代什么光都有。奇怪的是这光是从地基坑里发出来的。
我立即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谁的手机掉在那里了,然后有人拨打手机。但马上被我否定了,手机屏幕的光亮不应该这样闪烁。我好奇心陡增,也不管会不会害死猫,甩腿就走了过去。
我走到跟前时,那光还在闪。我在闪光里能清楚看见被夯实的地面,地面上什么都没有。那光就像是从地下穿透地面发出来的。我蹲下来用手去碰触地面时,那光熄了。
我站起来在那儿等了好大一会儿都没有再出现。
只好再回到刘一虎那儿去。刘一虎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边,连鞋子都穿好了。我对他摊了摊手说:“什么都没有了。”
刘一虎松了一口气:“没有就好,那儿就是挖断那条蛇的地方,我真怕有个什么好歹。”
我去!怪不得他一直不敢去看,合着拿我当枪使啊。他穿好衣服鞋子分明是一幅势头不对马上开溜的架势。我心里那个不爽,也怪我头脑发热,当时心念一转煞有介事地对刘一虎说:“叔,你有没有听老人讲的有个说法,就是有些奇宝会在地下动的。有的会变成小鸡大晚上明晃晃的在地上跑,跑到哪里没了,只要有人看见在那儿一挖,那肯定有元宝啊。还有就是这种发出奇怪的光的,不是宝贝还会是啥?”
刘一虎磨磨叽叽地说:“不可能吧,哪有那么多宝物叫咱挖着。睡觉吧睡觉吧,明天还得忙呢。”
就在刘一虎说话的工夫,那地方又亮起了幽光。不过这次时间不长,我俩才愣了一下那蓝光就熄了。刘一虎盯着那地儿看,我觉得他对我的话有些心动了。不由得意地一笑,心说大晚上没事儿你瞎折腾去吧,挖了地基还得重新夯实。明天村里人一见还不得笑死他。我想着那光也没啥大不了,按照走近科学的思路,顶多就是土里有什么化学物质。然后我还很关心地问了一句:“我婶子现在没事儿了吧?”
刘一虎说没事儿了,好好的,要不我也不能放心她一个人在家。
我这才朝我的木板床走过去。
这晚上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我把床铺铺好,往上面一躺很快就迷迷糊糊的了。就在快要进入熟睡的时候,就听见咣当一声响,把我一下子惊醒。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挨着我床铺的铁门开了。
这铁门是上了锁的。白天邻居过来见我放了床板在那还问我,要不要把门打开睡到里面去。我说不用,睡外面就行,方便看工地。这大半夜的门怎么开了?就算邻居过来有事儿,我的床正堵在门前,他不可能不叫醒我啊。
我想着起身进去看看,别睡在人家门楼下面再让人家家里遭了贼。我发现自己根本就动不了。我马上想明白了,我这是被鬼压床了。我只是非常着急,并不十分害怕。因为这时候一只耗子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咬上我一口。
客观地说,发生这种现象时,你以为你已经醒来了,其实还没有真正醒来。我听人说起过,鬼压床时看起来全身都动不了,其实舌头是可以动的。只要用舌头弄出点儿动静,人就会清醒过来。
我试着用舌头抵住上腭,然后用力往外弹,发出得得的声音。我感到浑身一松,真的能动了。我起身下了床,鞋子是放在外面的。我穿上鞋又从床尾上跨过去走进了邻居的院子。堂屋门开着,屋里亮着灯,门口倚着门框侧身站着一个人。我一见那人就张大了嘴巴。
我做梦也没想到,站在那儿的正是救了我两次的女孩儿。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惊喜地问道:“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那女孩儿调皮地笑着:“不是我还能是谁,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帮了你的忙,你也不管我,还好意思说?”
我汗死。第一回在西地坟头那次,我连是敌是友都没弄清楚。这第二回在刘人杰家我连面儿都没见着。我怎么管?但人家对咱是有恩的,这么随便一说总不能一句话给顶回去。
我于是陪着笑说:“哪能不管,我正到处找你找不到呢。”
那女孩儿眉毛一扬,笑嘻嘻道:“哟喝,你这么好心到处找我,不会是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吧?”
我顿时有些吃憋,这点儿小心思尽在别人掌握。自己也确实没想过要帮女孩儿做点儿什么。我本身又不是特别油滑的人,一时倒无言以对。
女孩儿嘻嘻地笑了笑,朝我一招手说:“跟你开玩笑呢,看你这么大个人,真不经逗。进屋里坐坐吧。”
我应和着笑了笑,朝屋里走去。我邻居几年都没在这儿住了,屋里只有一些旧家具,桌子柜子凳子也都有。沙发就别想了,这些都是早些的东西。
这屋里虽然旧些,感觉挺干净。我弱弱地问:“你住这儿,跟我邻居打招呼了吗?要不你住我家,或者我去跟他说一声,在农村住个房子不是问题。”
女孩儿眨巴着大眼睛说:“我才不住你家,我这么漂亮怕你对我有想法。这房子是我今天才租下来的,一天两块钱,就晚上住一下。”
“我靠,一天两块,抢钱呢?明天我去找他!真是什么钱都挣啊。”我一激动口病都带出来了。
女孩儿摆了摆手,说:“我愿意,不关你事儿。”
她说着话从靠北墙的大桌子上拿下碗和茶壶来,给我倒了一碗温开水:“坐下喝口水吧,到这儿你也别想有什么好招待的。”
我忙不迭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要问,女孩儿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会帮我?又怎么知道我在什么时间会遇上什么危险?现在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这节骨眼儿上,我了不好意思这么突兀地问出来。或者问出来了女孩儿也不一定回答。
我端起碗喝了两口水,思量着问道:“你,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我叫刘小帮,网名嗷嗷。”
女孩儿哈哈一乐:“你这么大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还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哈哈哈哈,你直接问我叫什么不就得了,我叫阎小米,你是不是还想问问我的祖宗十八代都做什么买卖的?别问别问,问我我也不告诉你。”
我被阎小米笑得挺不好意思。也被她一句话轻轻巧巧堵住了我所有的疑问。我只得低头喝了口水,嘿嘿傻笑一回。
阎小米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盯得我又开始喝水。她绷住笑意显得认真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大事,今晚上要有人挂了。”
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一口水都喷在了桌子上。赶紧用手抹了一把嘴问:“谁?谁要挂了?”
阎小米一愣,讶然问:“你担心个什么劲儿?我不会让你挂掉的。”
我脱口而出:“我叔我婶也不行啊,你这么好个女孩儿可不能出去害人。”
阎小米又是一愣,还带点儿委屈地说:“我什么时候害人了我?”
“那,是谁在害人啊?”我疑惑地问。
阎小米见我纠结得不得了,就不再兜圈子:“我告诉你吧,是那个张家洼的挖掘机司机要倒霉了。你以为那条蛇是好惹的?想不想去看看?”
我立马同意,说成,去看看。
我心里想的,要是关键时候能给挖掘机师傅提个醒,那一条人命就救下来了。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我相信阎小米,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
阎小米关了灯,和我一起出了门。跨过我的木板床,却不朝南往街里走,拉着我朝胡同北面走去。这胡同往北是通不过去的,往北走经过刘人杰家门口,再过一片没有路的小树林才到田间路上,然后从田间路上走几十步才到村后的水泥路。
我扯了一下阎小米,提醒她走错了。
阎小米说没错,只管走。
我跟着她走到水泥路上,才发现那儿停着一辆小轿车。我一看牌子,奔驰300.那车黑灯瞎火地在那停着,明显是给我俩准备的。我指着那车,有点儿合不拢嘴:“这车,你的?”
阎小米毫不在乎地说:“一辆破车而已,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吗?如果你喜欢,回头就送给你了。”
我连忙摆手,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
我一个**丝哪接受得起这么贵重的礼物。**丝根本无法理解土豪的世界。
阎小米打开车门叫我上了车,自己驾车如飘一样朝前驶去。天黑着,虽然有月亮,这么快的车速下我仍然把握不住外面的景色。只感觉两边的黑影嗖嗖地向后倒去。车子很快就停了下来。阎小米说到了。
我有些惊讶。张家洼离我们八九里路,就农村这水泥路走村过街,曲里拐弯,怎么可能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我疑惑地下了车,发现停车的地方仍然是村头的路上。
阎小米的车子根本不进村。她说是怕别人发现。然后她带着我朝村里摸去。这时我才想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阎小米开车一路上都没有打开车灯,完全是借着月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