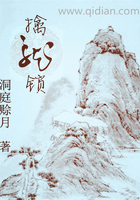一道黑影一闪即逝。夜,仍是那么静谧。
当石华重新坐在“悦来”茶馆这个民间新闻发布中心时,依然只听见说某厂又下岗几百工人;某地一学生考上大学,由于家中无钱而跳了楼;某当官的又养了情妇,建了豪华别墅。
石华有理由知道:自己投下的这块巨石为什么激不起千层浪?甚至连一点浪花也没有?
他静静地欣赏茶客们的喜悦,夜欣赏他们的愤怒;他听他们谈古说今,听他们将现代的许多贪官比作庞太师。有时,他真想也插进去,与他们说说。
然而,他时时都在盘算,家乡那所中学购买设备仪器还缺二十多万元。
石华是山里的孩子,家乡的山是骄傲的,有闻名全国的风景名胜;六十多年前,一群手持梭镖的人在那儿造过反,他们杀了霸田夺地的土豪,分了土豪家的房屋、粮食。这群人中,还出了一位将军。
家乡的山是贫穷的,让人心酸的:五六分薄山地,实在难以让那些早出晚归的山里人富裕起来。现在兴捐赠,那是施舍啊!前年一个阔老板在地区专员陪同下,捐赠了一大卡车月饼,那场面多热闹,敲锣打鼓,事迹还上了省报。可月饼却差点送了两个孩子的命。原来,月饼有霉点了。老板却说:“山里人贪吃”。
他十分赞赏一句歌词:“平地聚起一座金山”,一点也不错,那一座座“金山”不是生出来的,不是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而是“聚”起来的,从亿万百姓的口中、身上,从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起来的。所以,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倪献策、诸时建之类,不就是这些“聚”起的金山之神么?有人将人民币裹在鞭炮上,他们喜欢听那一响,喜欢看那满天纸花;有人在高楼上比赛扔啤酒,他们喜欢听市民的尖叫声,喜欢看那干干净净的一条街变成酒河。他们用“聚”起的金钱包二奶,包三奶;“指点江山”建别墅,买豪华轿车,“粪土当年万户侯”,更不用说一顿饭动辄上千上万。
一阵酸楚强烈从石华心底涌起,流遍全身,终于这酸楚又聚到一起,从他那聪颖的眼眶中涌了出来。家乡还有许多孩子半年见不到油星,拖欠了几年书学费而最终被赶出了光明无限却又破烂不堪的学校啊!而一个孩子一年的书学费加上一般的生活费到底多少钱呢?大不了阔人们几包烟钱一顿饭钱。
难道山区的人就都是些笨蛋么?石华坚决否认这一条,虽同在一个政策下,但“天时不如地利”,远离城市,远离主要交通线,即使有一股黄金白银海洋风吹拢时,也只剩下铁屑风尾了。假若让他们生在沿海,生在大城市,他们一样能活出个人样来。不是有许多人跑到山外,也挣回了令人羡艳的财富么?
所以,石华出了山。
他出山是十分凄凉的:一个带着补丁的被盖卷,裹着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他不是去上学,他是去打工。
家人把他送到村口,两天没说一句话的老父只说了几个字:“记住写信”。
可事与愿违,老板要么嫌他瘦小,“文弱书生干不动重活”;要么嫌他脸有疤痕,“模样不佳会影响客商心绪”。都不看他的毕业证,甚至有人说:“现在什么东西没有假的?人民币都有假的,何况一张毕业证”。
提起脸上那块伤疤,让石华不由痛苦的思绪牵回到五年前,牵回到那破烂的学校教室。
那是一座古庙,据老人们说,有好几百年了,解放后就用作学校,一直到现在,年代久远了,墙壁都裂了缝。乡上想重建学校,可就是没有钱,找上面吧,报告打了好几回,可县财政也十分紧张;集资吧,更好比到沙漠中去寻水。乡上想到了那位将军,可将军去世好几年了,将军的女儿说:她与那遥远的大山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终于,一场暴风雨中,古庙的墙壁塌了半边,飞坠的瓦片给石华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好在脸上的伤痕并不影响他的劳动、生活、学习。
现在看来,脸上的伤痕终究还是影响了他的工作。
苦闷、无助,仅有的一点钱也用光了,石华真的绝望了。
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更使他如麻的思绪不能理清。天下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我生存的空间呢?“茫茫苦海翻天涌,难觅半叶打鱼舟”这两句诗,好像是专为自己写的。
“小伙子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沙沙的声音问道。
“……”
“我看你这几天都到这儿来,气色也不好,是生活有困难吗?”
石华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个瘦小、干瘪的老头。
“这儿危险,前不久还有人从这儿跌下崖淹死了。我们到那边谈吧。”
一老一小两个瘦小的人进了一座雅致的小院。
老头自称“独孤客”,他留下了石华。
“独孤客”爱嗑瓜籽,瓜籽壳总是满地,石华便帮他收拾,每当收拾干净后,老头便十分高兴。
“独孤客”家中从无客人来访。老人高兴时,便要石华陪他下棋。老头棋艺很高,石华总是输。
“年轻人,不能性急,这棋道和人生是一理的,只要你抓住了对方的弱点、短处,你就可以获胜,你就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十分风光。”
“抓住对方弱点、短处,就可获胜。”很值得品味。
石华有时想找些书来看,他想读大学呀!
“读啥书?大学毕业不照样难找工作?现在当了官,发了财的人有几个真正有学问?”
石华心中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但他不好反驳,也就陪着嗑瓜籽。
一年后,“独孤客”病倒了,茶饭不进。石华急了,每天侍奉汤药,片刻不离。他已把老人当作了自己的老父亲。
一天,“独孤客”有了精神,把石华叫到身边说:想收石华做义子,并传他一门绝技。
原来,“独孤客”是一个神偷,偷技很高,足迹遍及了全国。但他有一个原则:不偷百姓;每年只干一次;偷来的钱够用就行,不得贪;不在同一地区干两次。
他要求石华不能违背他的原则,特别记住:不偷百姓。“现在贪官、发黑心财的人很多,偷他们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般说来,他们不会也不敢报警。小偷是很可耻的,但我们不能可耻。”
接过小小的盒子,翻着图文密密麻麻如同天书的本子,石华心中酸、甜、苦、麻、辣五味俱全。
“独孤客”死了,临死,手指颤颤地指着自己的心。石华明白:那是要他千万别忘了良心。
石华突然想家了,安葬了“独孤客”后,石华回到了千里之外,生他养他泥土殷红风光秀丽而又贫穷的山村。父亲混浊的目光越过酒碗盯着他,那么慈祥那么专注。石华不由得想起那个小盒子,心中十分慌乱。
家中依然穷,今年山区干旱,半年多未下一颗雨,田地裂开了,禾苗枯死了,几乎颗粒无收。
看着拿回来的东西,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唠叨着:张二娃出去打工,两年多了,今年想回家,叫家中给寄路费去;李小泉在浙江干活,砸断手臂,现在还在医院;石华的同学杨芳儿在深圳靠了什么老板,每月寄大钱回来;乡上那所学校终于全垮了,还打死了三个学生……
石华心中一震:学校垮了,还打死学生了?那学生们在哪儿上课呢?
烂瓦、断砖杂乱地堆在一起,山岗旁边,新搭着几个草棚,棚中飞出阵阵歌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两个老人的谈话声吸引了石华。
“县上、地区给的钱不够修学校么?”
“还差得远,听说有个马董事长同意出钱修建学校,但学校要用他的名字作校名,而且,以后学校每年给他缴五万元钱。”
“五万元?这钱在哪儿出?”
“学生家长出呗,学生的学费得翻十翻了!”
“商人就是会算帐,他不仅不亏,还赚了呢!可那是榨我们的骨髓啊!”
“要是我们自己能想出办法就好了!”
“是啊,大家都想尽了办法,学校老师还有镇长把工资都拿出来了,可还差得远呢!”
看着眼前的断砖烂瓦,看着老人儿童的焦急,摸着自己脸上的疤痕,石华流泪了。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小盒子。
半年后,在石华的新住所,黄鹤楼下长江边幽静的小屋内,几个纸箱皮箱里都装满了钱和金银首饰。这些钱来自十多个城市,没有一点是普通百姓的。他不敢违背“独孤客”的原则。他几乎毫不费力,便寻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对象,他听到什么“工程”什么“关照”就很兴奋,他知道:这些人又在聚他们自己的小金山了。
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他也很烦恼,因为只能将现钞和金银首饰拿走,那些数目更多的存折他却无可奈何。拿走吧,取不出钱;不拿走吧,又觉得不心甘:这是百姓的血汗钱呀!他就把它们撕得粉碎,觉得解了恨。
但他也违背了“独孤客”原则中的一条:一年只干一次。
这是无可奈何的,他想帮一下家乡那些和自己命运一样的孩子。他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伟大的光荣的,可具体作法呢?慢说法律不认可,家乡的父老乡亲也会认为是可耻的,他们会接受吗?用这些钱修建学校,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坐在里面读书吗?自己这样作,是不是给那块光荣的红土地抹黑呢?
想到这里,石华心里不禁打了几个寒战。
他决定:把学校修建好后,自己必须“金盆洗手”,再去读点书,找个正当的职业干,这样,心里踏实些。贪官虽可恨,但自己毕竟无权去处理他们,党纪国法也不会太软的。
石华被家乡人认为是有出息、不忘本的好青年、好企业家,在乡上捐款办学大会上,石华的脸通红,那块疤痕显得格外鲜艳,那是激动加惭愧,特别当党委书记给他戴上大红花时,原本不喜欢说话的他更觉得挤出一个字来。
学校教学楼、实验楼有着落了,但还缺二十多万元购买教学仪器呢!看来还得干几个回合。他又出了山。
他突然觉得:山里的天比山外的天要蓝得多、美得多。
二十多万终于够了,石华兴奋得很,忙拨通了乡党委办公室的电话。
“是石华吗?你一定要沉住气,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书记几句话,反而让石华急不可耐。
“我们党委政府用人不当,负责修建的李云居然不顾自己是国家干部,不顾山区的孩子,不顾国家克服了许多困难拨出的钱,不顾山区人民特别是你捐献的血汗钱,伙同包工队偷工减料从中谋利。唉,实在对不起你们呀……”
“刘书记,到底怎么了?”
“十天前,学校快完工时,倒塌了,当时就压死了五个民工,还有十多个受伤,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今天,我们去找李云,他跑了。”
石华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顿时觉得眼前全是鲜血,全是不太干净的钱,还有一双双愤怒的眼睛。
他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那所幽静的小屋的。
“你叫石华吧?”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在门前叫住了他。
石华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只那块疤痕倒是血一样的红。
“你居然偷到我们局长家了!真他妈贼胆包天!”
冰冷的手铐将石华所有的打算全锁住了。
他向家乡那个方向望去,楼层很高,天空,云层很厚,怎么也望不到家乡那特美特蓝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