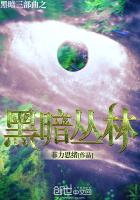春去秋来,一年四季轮番上演。这个秋天来得早,也显得比往年冷。我写作的成绩很不理想,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最近却无法提起精神来。
于慕凡嘲笑我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功人土头顶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他们背后的艰辛和付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说:“写作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苦逼的爱好?”
接下来那几天,绵绵的秋天不停地下着,窗外散发着一股树叶和木头的腐烂气息。仰天长叹,撑开我心爱的小花伞,到雨中寻找感觉。
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春妮的厂门口,与她不期而遇。
她脸上已经褪去了浓装,整张脸干巴巴的,仿佛苍老了十岁。身上再也不是时尚的衣饰,而是皱巴巴的褪了色的工衣。
“春妮。”我忍不住叫道。
她低着头,不理我,继续向前走。
“春妮!”我又叫一下。
她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背对着我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摇摇头。
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与春妮面对面坐了下来。一股浊黄的液体缓缓流入水晶一般的玻璃杯中。春妮眯着眼睛,透过浑黄的玻璃杯看着我,那眼神愈发的忧郁。
酒是好东西,伤心的时候,特别渴望它的麻醉。
阴沉沉的雨天,特别容易让人颓废,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那个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了。”春妮叹着气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反击她。
“他老婆和我打起来了……”
“这种事你输过吗?”
“没有,所以当他看到我揪着她老婆的头发不放时,他气急败坏地过来直接给了我一耳光。这记耳光终于把我打醒。”春去秋来,一年四季轮番上演。这个秋天来得早,也显得比往年冷。我写作的成绩很不理想,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最近却无法提起精神来。春去秋来,一年四季轮番上演。这个秋天来得早,也显得比往年冷。我写作的成绩很不理想,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最近却无法提起精神来。
于慕凡嘲笑我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功人土头顶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他们背后的艰辛和付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说:“写作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苦逼的爱好?”
接下来那几天,绵绵的秋天不停地下着,窗外散发着一股树叶和木头的腐烂气息。仰天长叹,撑开我心爱的小花伞,到雨中寻找感觉。
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春妮的厂门口,与她不期而遇。
她脸上已经褪去了浓装,整张脸干巴巴的,仿佛苍老了十岁。身上再也不是时尚的衣饰,而是皱巴巴的褪了色的工衣。
“春妮。”我忍不住叫道。
她低着头,不理我,继续向前走。
“春妮!”我又叫一下。
她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背对着我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摇摇头。
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与春妮面对面坐了下来。一股浊黄的液体缓缓流入水晶一般的玻璃杯中。春妮眯着眼睛,透过浑黄的玻璃杯看着我,那眼神愈发的忧郁。
酒是好东西,伤心的时候,特别渴望它的麻醉。
阴沉沉的雨天,特别容易让人颓废,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那个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了。”春妮叹着气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反击她。
“他老婆和我打起来了……”
“这种事你输过吗?”
“没有,所以当他看到我揪着她老婆的头发不放时,他气急败坏地过来直接给了我一耳光。这记耳光终于把我打醒。”
于慕凡嘲笑我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功人土头顶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他们背后的艰辛和付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说:“写作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苦逼的爱好?”
接下来那几天,绵绵的秋天不停地下着,窗外散发着一股树叶和木头的腐烂气息。仰天长叹,撑开我心爱的小花伞,到雨中寻找感觉。
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春妮的厂门口,与她不期而遇。
她脸上已经褪去了浓装,整张脸干巴巴的,仿佛苍老了十岁。身上再也不是时尚的衣饰,而是皱巴巴的褪了色的工衣。
“春妮。”我忍不住叫道。
她低着头,不理我,继续向前走。
“春妮!”我又叫一下。
她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背对着我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摇摇头。
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与春妮面对面坐了下来。一股浊黄的液体缓缓流入水晶一般的玻璃杯中。春妮眯着眼睛,透过浑黄的玻璃杯看着我,那眼神愈发的忧郁。
酒是好东西,伤心的时候,特别渴望它的麻醉。
阴沉沉的雨天,特别容易让人颓废,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那个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了。”春妮叹着气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反击她。
“他老婆和我打起来了……”
“这种事你输过吗?”
“没有,所以当他看到我揪着她老婆的头发不放时,他气急败坏地过来直接给了我一耳光。这记耳光终于把我打醒。”
春去秋来,一年四季轮番上演。这个秋天来得早,也显得比往年冷。我写作的成绩很不理想,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最近却无法提起精神来。
于慕凡嘲笑我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功人土头顶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他们背后的艰辛和付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说:“写作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苦逼的爱好?”
接下来那几天,绵绵的秋天不停地下着,窗外散发着一股树叶和木头的腐烂气息。仰天长叹,撑开我心爱的小花伞,到雨中寻找感觉。
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春妮的厂门口,与她不期而遇。
她脸上已经褪去了浓装,整张脸干巴巴的,仿佛苍老了十岁。身上再也不是时尚的衣饰,而是皱巴巴的褪了色的工衣。
“春妮。”我忍不住叫道。
她低着头,不理我,继续向前走。
“春妮!”我又叫一下。
她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背对着我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摇摇头。
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与春妮面对面坐了下来。一股浊黄的液体缓缓流入水晶一般的玻璃杯中。春妮眯着眼睛,透过浑黄的玻璃杯看着我,那眼神愈发的忧郁。
酒是好东西,伤心的时候,特别渴望它的麻醉。
阴沉沉的雨天,特别容易让人颓废,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那个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了。”春妮叹着气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反击她。
“他老婆和我打起来了……”
“这种事你输过吗?”
“没有,所以当他看到我揪着她老婆的头发不放时,他气急败坏地过来直接给了我一耳光。这记耳光终于把我打醒。”春去秋来,一年四季轮番上演。这个秋天来得早,也显得比往年冷。我写作的成绩很不理想,想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最近却无法提起精神来。
于慕凡嘲笑我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成功人土头顶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他们背后的艰辛和付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说:“写作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有那么苦逼的爱好?”
接下来那几天,绵绵的秋天不停地下着,窗外散发着一股树叶和木头的腐烂气息。仰天长叹,撑开我心爱的小花伞,到雨中寻找感觉。
不知不觉地,竟然走到了春妮的厂门口,与她不期而遇。
她脸上已经褪去了浓装,整张脸干巴巴的,仿佛苍老了十岁。身上再也不是时尚的衣饰,而是皱巴巴的褪了色的工衣。
“春妮。”我忍不住叫道。
她低着头,不理我,继续向前走。
“春妮!”我又叫一下。
她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背对着我说:“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摇摇头。
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与春妮面对面坐了下来。一股浊黄的液体缓缓流入水晶一般的玻璃杯中。春妮眯着眼睛,透过浑黄的玻璃杯看着我,那眼神愈发的忧郁。
酒是好东西,伤心的时候,特别渴望它的麻醉。
阴沉沉的雨天,特别容易让人颓废,让人提不起精神来。
“那个男人有老婆有孩子了。”春妮叹着气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反击她。
“他老婆和我打起来了……”
“这种事你输过吗?”
“没有,所以当他看到我揪着她老婆的头发不放时,他气急败坏地过来直接给了我一耳光。这记耳光终于把我打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