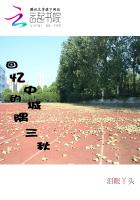那两名被安排在岸上值守的鬼子,好像心情特别的好,一脸的轻松。我们都还没有划出多远,我就看到他们俩一人打开了一罐罐头,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开始大快朵颐起来。
又划了好一阵子,坐在另一艘船上的三木招呼了一声,一扬手,突然将一个小口袋抛了过来。大海一把接住,打开来一看,原来里头装着几副游泳用的普通泳镜。
这家伙想得还真周到!我正准备道谢呢,一回头,却看见那些鬼子们正摆弄着他们的潜水镜,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们。那些鬼子手里头的潜水镜,才是正规的潜水用具,是连鼻子都包住的那一种,而我们手里头的东西,明显跟他们的不在一个档次上。
三木“叽里呱啦”地朝着他们说了几句日语,随后那一群鬼子们就爆发出了一阵哄笑。不用想都知道,三木这老小子一定是在损我们。
“你妈了个巴子的,你小子就给老子笑吧!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这帮王八羔子,总会有遭报应的时候的。”我在心里头暗暗地骂道。
我是真心诅咒这帮小鬼子们遭报应的,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报应居然会来得这么快!那几艘船上的鬼子们肆意的笑声都还没有停歇,远远的,从我们出发的岸边那个方向上突然传来了一声让人听了头皮发麻的惨叫声,紧接着就是“乒乒乓乓”一阵密集的枪声。
所有的人都是一震,连忙一齐回过头,去看在岸上值守的那两个鬼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其中的一个鬼子正端着枪,上蹿下跳地朝着齐腰深的灌木丛中疯狂地扫射着,而另一个小鬼子则是完全不见了踪影。
由于我们离岸边已经颇有一段距离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得出那个小鬼子是在朝灌木丛中射击,但是却完全看不清楚在灌木丛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只是看到那些植物的枝叶一阵阵猛烈地晃动,也不知道是躲藏在里头的东西搞出的动静,还是被那阵如雨点般的子弹给打出来的。
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都忘记了划桨,任凭小船在水面上飘动着,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岸上。虽然我对这伙小鬼子完全没有任何好感,但是在岸上的毕竟是两条鲜活的人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我们之间的恩怨如何,现在大家都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我的心里还是忍不住会为那两个鬼子感到担心的。
不大一会儿,枪声停止了。看那鬼子的动作,显然是枪里头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哆哆嗦嗦地蹲下来,从背包里头摸出了个弹夹,迅速地换了上去。而直到现在,另一个小鬼子始终都没有露面,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那鬼子换完弹夹后,又站了起来。枪里头有了子弹,他的胆子也好像变得大了一些,猫着个腰,探头探脑地朝那丛灌木走了过去。而那丛灌木之中,在这时候也安静了下来,看不出有什么动静。
那小鬼子慢慢地靠近了那丛灌木,他一手端着枪,另一只手从枝叶之间探了进去,似乎在摸索着什么。很快,他的手上就抓住了什么东西,很用力地往外头拉着,将那东西从植物之间拖了出来。
等我看清楚那小鬼子手里头拖着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手里头拖着的并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那位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的鬼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又怎么会突然之间钻到灌木丛里头去了?而且看那个鬼子的状态,情况似乎不是很乐观,他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躺在地上任由同伴拖行着,一动也不动。
拿着枪的鬼子费力地将同伴一路拖到了池边,他朝着我们用力地挥着手,同时大声地喊着什么。不过由于山顶上的风不小,我们之间离得又远,所以他的声音基本上被风声给淹没了,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喊些什么。这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是我听清楚了,我也不可能知道这小子究竟在喊些什么,我又听不懂日语。
就在我正琢磨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从灌木丛中猛地蹿出了几个人形的家伙,闪电般地朝着那那个小鬼子扑了过去。那些家伙的动作十分迅猛,那小鬼子连一枪都没有来得及放,就已经被扑倒在了地上。
“****!又是那些狗东西。”花少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扑倒那小鬼子的正是那些被寄生了的尸体。
你见过非洲草原上的狮群捕猎吗?在一只狮子扑倒猎物之后,周围其它的狮子就会一拥而上,迅速地将猎物杀死。我眼前的情形差不多就像是那个样子,我只看到一只手从围成一圈的尸体之间伸了出来,手指不断地张开、弯曲,似乎是想要抓住什么。不过很快,那只手就没有了力气,软绵绵地垂了下去,再也不动弹了。
也许是条件反射,我猛地捞起了身边的喷子,就想要朝着岸上的那几具尸体射击。
大海一伸手,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枪管,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这么远的距离里,我手里头的喷子根本就伤不到那些尸体半根毫毛。而且搞不好原本那些尸体并没有发现我们,枪声一响,反而把它们都给吸引过来了。天知道在这座山的山顶之上究竟还藏着多少这样的东西,从刚才在岸边草地上发现的脚印来看,这些鬼东西的数量足够把我们这一行人给灭上好几回的。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这种时候都能表现出大海这般冷静。我这边才硬是压下了扣动扳机的念头,另外几艘船上的小鬼子们可是丝毫都不吝啬子弹,跟过节放鞭炮似的就开了火。不过正如我所料,这些都是在做无用功,在这么远距离的情况之下,喷射出去的子弹倒是打得岸边一阵尘土飞扬,却根本就伤不到任何东西。
这一开火可不打紧,不仅那几具尸体立刻就发现了我们,而且我眼看着四周围的山岩上“呼啦啦”地又蹿出了不少衣裳褴褛的尸体来。
这些尸体行动起来可是不带半点犹豫,几十米高的山崖,“咕咚”一声就直接往水里头跳。眨眼之间,就看见远远的水面之上此起彼伏地溅起了大概有十几二十朵水花,所有的尸体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都跃入了水中。这还仅仅是第一波,随着这些尸体的落水,又有不少尸体从密密麻麻的植物之间冒了出来,也是毫不犹豫地纷纷跳入了水中,他们眼里的目标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
“你奶奶的,这下你们可满意了吧?一帮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还不快给老子用力划!”薛忠大声地朝着鬼子们吼道。
三木一看是这么个情况,这时候也慌了神了,赶紧指挥着鬼子们手忙脚乱地划着桨,他自己则抱着一台不知道什么仪器,一边看,一边朝着一个方向指着,让鬼子们把船照着那个方向划了过去。大海和薛忠用力地划着桨,紧紧地跟在三木所乘坐的那艘船的后头。
我则是紧张地端着手里头的喷子,紧张到身体都已经僵硬了,只剩下一对眼珠子还能转动,不断地在周围的水中来回地扫视。这些跳入水中的尸体摆明了就是冲着我们而来的,我现在只希望这些要命的祖宗们生前不要是索普或者是菲尔普斯那样的人物。
好在游泳似乎并不是这些尸体的强项,在三木示意大家停船的时候,我们四周围的水里头还是一片平静,那些尸体并没有赶上来。
天池里的水很清,即使水深起码超过了二三十米,我们还是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水底的情形——在一大片绿油油的水草之中,有一块十分明显的黑乎乎的区域,不用说,在水底下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尽管由于水波的晃动,我们并不能很具体地看出这个东西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大家伙。
三木对着我们招了招手,又指了指水底下的那个东西,然后戴上了他的潜水镜,叼起了一罐子压缩空气,“噗通”一声就跳入了水中。
第二个下水的是小雪,这姑娘像是特别练过,跟条鱼一样轻轻地滑下了船,连一丁点水花都没有溅起。她下了水之后,特地对我们招了招手,示意我们跟紧一点,然后一个翻身,姿势优美地潜入了水中。
我们这边第一个下水的是薛忠,这小子连泳镜都没有戴,“咕咚”一声就如同一颗炸弹般地跳了下去,溅了大伙儿一头一脸的水。等到了水里头他这才想起来要戴泳镜,只好又浮出水面,在捣鼓了一番之后立刻又潜进了水中,追赶小雪去了。以这小子这么庞大的身躯,居然能够在水里头游得那么快,倒也十分难得。
花少笑着对大海说道:“还好你刚才教给了我那师兄那呼吸器的用法,你看这小子猴急得,生怕那日本小妞有个什么闪失。”
“别废话了,都赶紧下水,鬼知道那些尸体在水里头游得能有多快,指不定这时候已经赶上来了。”我看着其他船上如同下饺子一般跳入水中的小鬼子,赶紧催促他们。同时我的手里头也没闲着,调整好呼吸器,带上泳镜,做着下水的准备。
大海一边做着准备,一边将我们的武器全都收了过去,装在了防水的背包里头,再挤出包里的空气,将密封拉链拉上,把背包背在了自己的背上。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我的喷子和手枪也一并装了进去,不由自主地朝着来时的方向多瞟了几眼,心说这下可倒好,大敌当前,两手空空,待会儿若是真的在水中与那些尸体遭遇的话,岂不是得准备上牙口了?不过大海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就算是我的手里还端着那支喷子,到了水里说不准也得成了哑炮。
说话间,最后一个鬼子也下了水了,我们几个连忙咬上呼吸器,做了几下深呼吸,也都翻进了冰冷刺骨的水里。
潜水这件事情,我还真没干过几次,最多就是在游泳池里头玩过几回,下潜的深度还都不超过两米。我倒是一直想去海南玩玩浮潜,可是想了好多年了,每次都是数了数口袋中的银子,就只好作罢。
其实话说回来,本身我的身体条件就不适合做潜水这项运动,你说我一胖子,拖着一膘肥体厚的身躯,这比重明显要比水小上许多。平日在泳池里的时候,我最喜欢跟别人炫耀的动作就是往水面上一躺,手不摇,脚不动,不管怎么着就是沉不下去。这会儿得闷着头往几十米深的水底下扎,对我来讲还是着实要费一番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