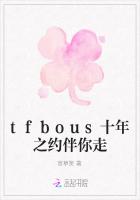酒过三巡,众官员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一个个端着笑脸,脸皮子都酸了,也没有见丞相大人露出半分表情。
众人心中慎然,丞相大人果真与传闻中一般难以讨好,想到皇上派他来巡察土地新改一事,心中更是惶惶不安,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有大批官员丢官贬职;又想到自己,于是愈发的阿谀奉承起来。
酒宴过后,沈沛白一行人入住官驿,吴太守再三邀请沈沛白去他府中居住,然而却被沈沛白一口回拒,众官员见太守被拒绝了,自然不会觉得丞相大人会给自己面子,知情识趣的离开了。
两淮总督早两日来淮南,本来是住在太守家中的,见沈沛白住官驿,他让仆人把东西收拾一下,搬到了官驿中。
吴太守皱着八字眉,心中苦。
他早知丞相大人过来,提前好几天在太守府中准备好了厢房,花了不少的心思,谁料如今不仅丞相大人不住他府中,连原本入住的总督大人也搬走了。
他眼珠子一转,对跟在身边的下人低声耳语了几句。
夜色降临。
总督大人方才在席上喝多了酒,此刻在房内有些燥热,就推开了窗子,结果一推窗子就看到一人带着两名女子从外面行过,那人正是吴太守的属下。
“呵,有好戏看了。”总督大人脸上露出了一个微笑。
他慢悠悠喝完了一盏醒酒茶,算了算时辰,开门走出了院子,才行了没多远,就听到了女子嘤嘤啼哭和求饶声。
走到沈相居住的院子外,总督大人装作无意间路过的样子,故作惊诧地探头看向院内:“相爷,发生何事?”
两个衣不蔽体的女子跪在院子里,娇弱雪白的脖颈上架着锋利的武器,香腮雪泪,好不可怜。
沈沛白神色淡漠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总督大人一眼:“韦大人来得正好,此二人是刺客,还请韦大人告知吴太守,让他派人将犯人收监审问。”
总督大人吃惊道:“这严防禁护的官驿竟然有刺客,这太守大人是干什么吃的?”
那两名女子惊慌失措,一边摇头一边哽咽道:“大人,我们两个是太守大人的女儿,不是刺客!”
一旁的侍卫嗤笑道:“笑话,太守大人的女儿怎么会在官驿之中,你们扯谎也不先打探打探,太守大人都快六十高寿了,你们当他孙女还差不多。”
总督大人嘴角抽了抽,这吴太守政绩平平,全靠一张巧嘴左右逢源,别看他长得像六十的年纪,实际上他还不到五十呢。
话音刚落,吴太守火急火燎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一脸冷汗道:“误会,都是误会!相爷,这两位是下官的女儿、干女儿,下官特意让她们给相爷送醒酒汤来的……”
说完,他又想起了丞相大人在席位上根本就没怎么喝酒,都说丞相大人不好女色,原来这都是真的,吴太守此刻后悔万分,偷偷瞄了一旁看好戏的总督大人一眼,见他丝毫没有替自己开口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道:“她们二人少不更事、天真无邪,不知道有无冒犯到相爷?”
总督大人在一旁差点没笑出声来,这位吴太守还真脸皮厚如墙头,都这般还能让他找出理由来。
总督大人在一旁憋着笑,瞧够了戏,清了清嗓子开口道:“相爷,对方或许只是仰慕大人,用错了办法,你就原谅她们吧。”
“既是总督大人开口,那本相就网开一面,下不为例。”沈沛白像是没有听出总督大人的戏谑,撂下这话,也不管吴太守了,直接进屋。
吴太守一边擦着冷汗,一边跟总督大人道谢:“多谢总督大人求情,下官不打扰您休息,先行告退。”
总督大人看着面皮松弛看起来都快可以当他爹的太守,本想说点什么,想了想还是闭上了嘴。
他转过身,恰好看到怀剑端了一碗药走进院子,疑惑道:“怀剑,你家相爷身体有恙?”
怀剑没好气道:“本来已经煎好了一碗,被那吴太守的好干女儿打翻了。”
这药需要定时喝,一点都马虎不得,而且药材难得,此次出京只带了一定的数量,也难怪怀剑也抱怨起来。
总督大人脸色担忧:“相爷得了什么病,要紧吗?”
怀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开口解释,总督大人虽然与大人是好友,但是这些事情并非他一个做属下的人可以置喙的,只是道了一句:“年关之时,大人被刺客刺了一剑落下的旧疾。”
总督大人跟着怀剑见了屋,屋内的沈沛白正坐在案前批阅着什么。
“大人,药来了。”怀剑将药递给沈沛白。
沈沛白将手中的豪笔放下,接过那碗药一饮而尽,怀剑退下,将门带上。
“这都过了大半年了,伤还未全好?”总督大人忍不住道。
沈沛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用眼神意示他落座,又拿起了方才放下的豪笔。
有些人天生自带气场,就算是不开口说话,也没有会无视他的存在,而沈沛白就是这种人的佼佼者。
还好总督大人了解他的为人,落座之后开口道:“相爷,朝中又发生了何事?你为何会离京?”
这土地改革之时因为旧政党插入,情况十分复杂,进度近乎龟速,沈沛白既为超一品的丞相,在朝中诸事繁杂,这等事情随便委任一个四五品的官员也就罢了,绝不可能会轮到他。要知朝中格局盘根错节,瞬息万变,等闲大臣若非万一,绝不轻易离京,更何况这巡查土地新政之事没有个两三个月也完不成,等三个月之后回京,朝局很有可能发生异变。
他又想到了刺杀之事,皱眉问道:“莫非与刺杀之事有关?”
沈沛白停下笔,将手中的宣纸换了一个方向,推到总督大人的面前。
总督大人低头一看,面色一震:“这是建州的驻军地图,莫非安平王……”
建州是安平王封土,安平王赵业为先皇之弟,也是当今皇帝的亲叔,世袭亲王,手中握有三万兵权,人数虽少,却是个个精兵,一直是皇帝的心头大患,莫非这次沈沛白离京是为了调查安平王。
总督这么想着就这么开口问了出来。
沈沛白道:“近几个月来西川关战事骤起,上个月德牧失守,两位将军也战死沙场,皇上怀疑朝中有奸细,命我调查,我几番调查之后发现安平王似于西厥有所联系。”
总督大人皱眉道:“这安平王的确不是个能安分守己的主,只是要抓住他的狐狸尾巴也不容易,相爷准备从何处下手?”
安平王的王位可是太祖皇帝赐下的,手中又有丹书铁劵,就连先皇见了他都要可客客气气的,皇上一直想要削他的兵权,却一直无从下手,因为这个安平王平素行事十分低调谨慎,从未留下任何把柄。
“这就要麻烦总督大人了。”沈沛白道。
“下官能帮到相爷什么?”总督大人语气有些激动,说完这句又道:“相爷快别这般称呼我,你我二人相识十多年,叫我士章就是。”
总督大人姓韦,名金平,字士章。
沈沛白点头道:“既然如此,士章也直呼本相表字便是。”
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未见,以前在书院的时候关系交往只是平平,若不是楚岫玉,估计不会深交,韦金平与陆茗不一样,他为人圆滑,又深谙为官之道,所以如今他已官至二品,虽不是朝中,却也算得上位高权重。
韦金平也是少数知晓当年沈沛白和楚岫玉之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去年的时候他也接到了沈沛白的请帖,只是那时他腾不出时间,所以没能赶上婚礼。
沈沛白道:“听说尊夫人的出身柳台厉家?”
……
烛火摇曳,不知过了多久,韦金平恍然惊醒:“时辰不早了,屹之,你的脸色不太好,还是早些歇息吧。”
沈沛白脸色有些发白,本想站起身,却晃了一下,险些被桌案绊倒。
“你没事吧?”韦金平连忙扶了他一把。
韦金平知道他身子不好,连忙问道:“不会是又犯旧疾了吧,带药了吗?”
沈沛白摆了摆手道:“无妨。”
韦金平只好往外走,走了两步,又想起了什么道:“对了,都忘记恭喜你成婚了,恭喜恭喜,尊夫人定是位佳人吧。”
沈沛白苍白的脸色浮出一丝笑意,只是不知想到了什么,片刻之后就收起了表情。
六月的天,天色说变就变,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到了下午又下起了瓢泼大雨。
苏映雪坐在堂上,下面站着白玉点心铺的伙计。
那伙计满脸气愤,恨恨道:“夫人,那牢头收了银子之后,却翻脸不认人,怎么恳求他也不让我进去!”
又道:“不仅如此,连长风镖局的人他们也通通挡在外面,说是杀人重犯,闲杂人等不得探监,这也太过分了,退一万步讲,就算袁镖头杀了人,那临死也总得让亲人见面不是!更何况袁镖头为人和善,从不会用武功欺负别人,我绝不相信袁镖头会杀人!”
丫鬟小桃点头赞同:“是啊,袁镖头是沧州远近闻名的善人呢,长丰镖局都已经开了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出过什么事,怎么会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