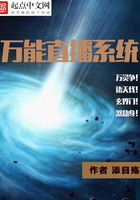萨满和天巫结仇这是人尽皆知的事,虽然天巫身份尊贵,但萨满跳神是在中土延续数千年的风俗,就连秦皇嬴少苍也只是废了巫皋的大祭司身份而已,废不了百姓的信仰。慕容恪在阿拉耶识床边犹豫着说完了对她夜惊魔怔的担忧,特别期待她能同意请萨满驱邪,他再三保证自己请的人绝对可靠。阿拉耶识抬起因整夜发噩梦而疲惫瞌睡的眼帘,漠然地看着他,片刻后才阖上双眼,冷冷地下了逐客令:“我累了,走开。”
这个多天来阿拉耶识第一次开口说话,长身跪坐于地的慕容恪激动地挺直身躯,旋即又被她冷若冰霜的姿态浇灭了满腔欢喜。室内火墙散发的热气令从外面进来的慕容恪浑身灼热,细细的汗冒出额头,他顶着内外冰火两重天一步挪一步往外走,行到堆砌满积雪的木质走廊上时,寒风夹着雪花袭上头脸,他冷得皱紧眉头,就在这瞬间他转身往回跑,直奔阿拉耶识的床边扑跪于地,哀恸喊道:“妹妹,如果你还当我是慕容哥哥就动手吧,你诛心也好,杀头也罢,求你给哥哥一个痛快!我害了冉闵性命,请让我以死抵罪,求妹妹成全!”
不等阿拉耶识有所表示,慕容恪喝令左右取皮鞭。左右取来皮鞭后,慕容恪跪在屋门口阿拉耶识刚好可以看见的地方,命令侍卫对自己用鞭刑,打满三百之数。冉闵死前被鞭三百,浑身皮肤无有完好之处。阿拉耶识密合的羽睫几不可见地动了动,在皮鞭响起时也没睁眼,任由皮鞭在慕容恪身上发出啪啪闷响。几十鞭下去,慕容恪华贵的夹袄皮袍已经被打得翻开了花,鲜血顺着挥动的鞭子甩在雪地上,星星点点格外刺眼。慕容恪依旧稳稳地跪在门口,双手牢牢地撑在膝盖上,双唇紧闭一声不吭。
阿拉耶识翻身朝里而卧,眼泪顺着眼角淌在枕头上,她死死咬住被子角,拳头握得直接发白。那沉闷的皮肉响好像打在她的脑袋上一般,她只觉得头脑里嗡嗡作响,撕心裂肺地疼。“这是棘奴受过的苦楚,我不能哭,不能哭……”她一遍遍地对自己重复这话,阵阵的心慌胸闷使她几乎无法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那令人窒息的皮鞭声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慕容恪已经成了血人,双手再也无力支撑上身,整个人半跪半伏在门廊上,唯有眼神坚如铁石。廊外突然传来杂沓慌乱的脚步声,一个王府侍卫追赶着一个粉妆玉琢的小团子闯到行刑现场。
“爹!”小团子发出稚嫩的惊呼,“爹你怎么啦?”
这突如其来的幼儿喊话把沉浸于痛苦中的阿拉耶识惊得打个激灵,不由自主转身、睁眼,与那小团子对上彼此惊异的眼。那惊扰了行刑的小团子四五岁年纪,戴着灰色绒帽,露出乌溜溜如黑炭般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嘟嘟胖,挺翘的鼻头,不算特别漂亮却非常健康可爱。小团子惊愕地盯着阿拉耶识不转眼,稍后,他微微翘起的鲜红小嘴逐渐拉长变瘪,突然之间爆发出高音的哭喊:“娘——娘——,你为什么要让人打爹爹?你去哪里了呀,我想死娘亲了……呜呜呜……”小团子一边哭喊,一边扑在阿拉耶识身上挥动粉嫩的小拳头捶打她。
“啊!”伴随短暂的惊呼,阿拉耶识哧溜地从床上坐起,惊悚地推开小团子,尽量将缩回手脚:“这谁家的小孩?快带走快带走,娘都可以乱认的吗!”
小团子黑炭般的大眼睛眨巴两下,哇地哭得更厉害了:“娘不要我了,娘我要娘啊……爹爹——”
“世子爷!”追到屋门口的侍卫急得直跺脚,地上的慕容恪强忍剧痛朝小团子伸出双手:“楷儿,过来,你认错人了,这是天巫。”
慕容楷?阿拉耶识反应过来小团子是慕容恪与段希钰的儿子,她在三年前曾见过一次,那时尚在襁褓中,如今已能满地跑了。大约是慕容恪浑身鲜血的可怖模样吓住了慕容楷,他本能往后退缩,返身拉扯住阿拉耶识的手臂大哭:“娘,求你别打爹爹了,爹爹会死的!”
“住口,休得冲撞了天巫!”慕容恪顾不得伤痛,挣扎着要过来抓慕容楷却被他滑开,灵巧地钻到阿拉耶识的床上。
“爹爹你骗人!”慕容楷从阿拉耶识里侧探出小脑袋,小手在衣襟里掏呀掏,终于扯出一张三尺长、一尺宽的帛画来,气呼呼地抖散给大家看:“你们别想骗小孩子。这是我在爹爹书房发现的娘的画像,里面还有好多副哪!爹爹骗我说娘死了,其实你是把娘送去看病了。娘一定得了不认识人的怪病,你就把她送走,让楷儿没有娘亲了,爹爹坏……”
那幅帛画上画着一双男女并坐共弹一琴,男的英武雄杰,女的姿容绝世,居然是慕容恪与阿拉耶识。阿拉耶识顿时什么都明白了,顿时羞恼万分,眼看就要发作,慕容恪牢牢将其抱住,连哭带撒娇,说什么也不肯放手。在侍卫的搀扶下的慕容恪失血的脸此刻红得如块红布,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阿拉耶识没法对一个在自己怀里乱拱的幼儿动手,目瞪口呆地看着慕容恪在自己身上尽情地撒泼,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慕容恪想将慕容楷从床上揪下来,阿拉耶识横了他一眼,低声威胁:“矗这儿好看哪?还不快滚——”
慕容恪如得敕令,刚欲转身又被她眼压切齿叫住:“去把你书房里的画都拿过来!”
“呃好——”他边答应着边抹着一头一脸的血汗,身体虽痛得要散架了却无端地觉得脑子清明,心胸宽泰许多。
自家爹前脚刚走,床上的小团子马上作怪,他还挂着泪花的小脸蛋已经笑开了花,,小脑袋更是对着阿拉耶识歪来歪去的,黑葡萄样的眼睛弯成豆荚儿。这孩子又哭又笑的,阿拉耶识只觉莫名其妙,她很不喜欢被人赤裸裸探究的感觉。
“下去。”阿拉耶识拉着脸命令小团子,并用手给他指了指门口。
小团子慕容楷露出两瓣圆润的门牙嘻嘻笑:“娘长得真好看,难怪爹爹那么听你的话。”
“哈?”阿拉耶识的嘴唇可笑地咧开一道缝,有点跟不上小团子的思路。
“娘,别生爹爹的气,他是王爷、上将军,要做大事,肯定没法和娘总在一起。”小团子亲热地挽住她的胳膊:“喏,爹爹老不在家,给我请了好多教习先生教我习武,我早晚都要园子里扎马步。你看——”慕容楷在床上摆出马步姿势,双手臂向前平举伸直,他的手指头长满了红红的冻疮,看着像两排小胡萝卜,而且有的还破皮溃烂了。阿拉耶识下意识地偏头避让那过于接近的“胡萝卜”,这么严重的冻疮肯定会让小孩儿抓心挠肝地痒,令阿拉耶识快速从21世纪社工守册中关于提取“儿童疏于照顾”的虐待罪名来。
只见小团子脸上露出既骄傲又委屈的神情,紧绷嘴唇给自己鼓劲道:“长冻包太讨厌了,医官敷的药根本不管用,我想要一副金虎头戴的那种手套爹爹都不许,还说我堕怠……”他说完后收了马步,急急地抓挠双手,显然痒得难受。
侍女忙道:“我去拿冻疮膏来搽。”
“等一下,把他领走。”阿拉耶识对着慕容楷直摆手,恨不得将其塞回他亲娘肚子里。
“不!”慕容楷跳着闹将起来,阿拉耶识刚想制止他,他竟然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蹬腿撒泼,敞开嗓门就嚎哭。
王爷好哄,世子难缠。阿拉耶识昨晚夜惊梦魇本是极度瞌睡的,先是被慕容恪自罚鞭刑勾起恨事,继而被小团子慕容楷搅局平白多出个大胖儿子,简直内伤到极点。那副神仙眷属的帛画暴露的隐秘私情让当事双方都下不了台,刑罚搞成欢腾闹剧,阿拉耶识一个头两个大。
“你起来,堂堂世子坐地上撒泼成何体统,缺礼少教!”阿拉耶识皱着黛眉,着实烦恼。
“不起来,娘让我留在这里,我才起来。”慕容楷毫不退让。
“我要睡觉——我昨晚一夜没睡,眼睛都睁不开了,你找乳母去。”
“那我陪娘亲一起睡。”
“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你娘。你娘叫段希钰,燕国芊红郡主;我叫阿拉耶识,是中国人。那幅画是你爹画着玩的。”看着慕容楷骨碌转动的小葡萄充满早熟儿童的慧黠,阿拉耶识就知道必须讲点真话,她压低声音道:“好吧,我说实话。男人呢,都是喜欢美色的,你爹他画我的画像算不得罪过,顶多是风流韵事。你不能凭几幅画就乱认娘亲,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你必须得有孝心,不然长大了朝廷不给你当官的。”
整段话小团子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懂得的部分让阿拉耶识差不多要暴走了。慕容楷把头摇得跟拨浪鼓样,很认真地对阿拉耶识讲:“你肯定是我娘亲,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一定是。”不等阿拉耶识露出“这孩子脑子坏了”的可怜神情,小大人慕容楷一板一眼地道:“身为王爷会有很多女人,女人都会生孩子,可是他们都只能认王爷正妃为娘,其他的都是下人,不配养孩子。我记得小时候有个女人说是我娘,可是她很少和我在一起,那她肯定就不是正妃,她就不是我娘!别以为我是小孩好骗,爹爹的书房美人能进,这东院没人能进,只有你才能打爹爹,你肯定会做我娘的!”
阿拉耶识完全傻了,她这时才想起中国古代贵族们严苛的等级尊卑制度里,庶出的子女只能称正妻为娘,妾只是比婢女稍好的下等人,可以被正妻发卖甚至处死。这个观念从小被灌输给贵族子弟,慕容楷身为太原王府的唯一嫡子,此类规矩早就谙熟于心,他的娘亲称呼并非孩童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