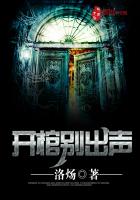我是刚天黑就到空屋里的。空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连个坐的凳都没有,我总不能席地而坐闹一身灰吧。好在我是有准备的,前去时带了几张旧报纸,又在弄堂外的矮墙上拆了几块砖头,在里面叠起来铺上报纸聊充凳子。
我选择的位置是在天井矮墙朝北那一面,这里是一个角落,这样如果有鬼物从天井里下来,不会马上发现我,而我在他进入后半间时,就可以迅速站在矮墙前挡住他的逃路。
不过那也只是我的想法,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吧,鬼灵来去有踪吗?我挡在矮墙前能挡得住他的逃路吗?
在平时,这种空屋令人恐怖,像我这样的少年一个人黑灯瞎火呆在里面一夜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为了找回杜大保的魂儿,恐怖不恐怖都无所谓了。我只担心这种蹲守有没有效果。
前半夜很平静。我一直在黑暗里睁大眼睛。
到了后半夜,我的眼皮涩涩的,呵欠也一个接一个地打开,想想平时躺在床上懒洋洋有多舒服,真想马上回家美美地睡觉。但还得硬撑着坚持。
不知什么时候传来扑通一声响,我一下子惊醒,才发觉自己居然不知不觉打瞌睡了。
我竖起耳朵仔细谛听,感觉刚刚那响声来自屋顶上。
有东西出现了?
立刻眼前闪过一个可怕的影像,一个青面獠牙的东西已经落在屋脊上,像猴子那样蹲着,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他会不会揭开屋顶的瓦片,悄悄向屋里窥看?
我没有敢站起来,以免使自己的目标变大。我尽量将身子缩起来。可是如果上面的家伙要揭瓦片窥看的话,我是隐身不了的。空荡屋子里没有地方可以躲藏。
我仰着头审视上面,听听那种声音是否有变化,揭瓦片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出来的。
等了一会果然听到揭瓦片的声音。随即屋顶上出现了一小片光亮,这片光亮并不那么明显,只是淡淡的一点点,说明外面的夜色也是挺暗的,不过比屋内稍亮一些。
我心里说不出是恐怖还是气恼,反正是挺紧张的,接下来肯定是一张鬼脸贴近那个揭掉瓦片的小洞往下窥视。
果然那片光亮出现后又显得暗了,说明有东西又贴到洞口挡阻了光线。
我是彻底不敢动了,只睁着眼睛紧紧盯着,不管那里出现什么恐怖的面孔都不能避而不看。
可惜只有光线暗下来,我由下向上望是不可能望见什么面孔的。其实我带着一个手电,要不要突然朝上照一下?
如果拧亮手电就把那东西给惊吓了,有可能他立马就窜掉。我不是把鬼物吓掉就算了,而是要想逮住一个审问的。
保持静默一动不动。
马上上面的光亮又出现,说明那张脸稍稍离开了小洞。
他是不是窥见我了?我虽然处在黑暗里,但鬼物的眼睛不是人的眼睛,黑暗对他们来说不是屏障吧,他们本来就是在黑暗里游荡,能看不清屋里有人吗?
接下来他会干什么?
我设想他一定会跑了的。
但就在这时,突然上面又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声音,似乎是有两只爪子在抓着瓦片,然后是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直接从屋顶的洞口掉落下来。
啪的一声那个东西砸在离我两三米前的地面上。
落地声既不很重也不很轻,从屋顶到地面有四米左右高度,给我的感觉那个落下的东西不会超过一斤的。
鬼灵有份量吗?他从那个洞口挤下来,会直接坠地吗?
但既然有东西砸下来了,我全身都忍不住一缩,下意识地将手电紧紧攥着,随时准备开亮了照一照。不过我还是拼命控制着,要看看那个东西砸地后是什么动静。
等了一会没感觉到有动静。倒是屋顶上又传来了诡异的声息。还有东西留在屋顶上呢。
是他的同伙吧?
下来一个进行侦察?可是搞侦察的怎么没有动静呢?掉下来后溜到角落里去了吗?
我想到的是更加恐怖的情形,也许那个鬼物落下后正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呢。
他距离我可能不止两米了,可我根本就看不见他。更可能他在一步一步朝着我走近,而我感觉不到他的任何声息。而上面的同伙故意弄出一些响动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说不定马上有一双毛绒绒的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我一下子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连忙把肩膀往上扛而把脖子往下缩。其实这样做有用吗?我能保证不会被鬼物掐着脖子吗?
这时我产生了重重的疑惑,我不是练出觑灵功来了吗?昨天在外面隔着门都能看到屋里的情景,今夜怎么好像失灵了?都有东西掉下来了,我却依然什么也看不到?
难道,我的觑灵功被剥夺了?
或者是鬼物知道我有觑灵功,把他自己给屏蔽起来了,我的觑灵功在他面前失效了?
我还是忍耐着不动,也没有开亮手电。既然要跟鬼物打交道,那一定要有足够胆量才行,要不然即使不被吓死也会吓傻。
怕个球球,老子既然答应帮远甜和小练找回她们的魂,还怕三怕四干什么,如果我是个没用的人,她们也犯不着费尽心机求我出面了。
我倒要看看特么的鬼物会有什么动作。
又过了一会后仍没什么动静。屋顶上的响动持续了一会,又向着远处滋溜溜地窜去。那是一种很轻柔的脚步声,像是一只小兽踩动瓦片远去。
我实在不耐烦了,决定开亮手电让屋内的情景显形。不管多么可怕我也认了。
手电一拧亮,照出前面地面上躺着一个东西。
一下子我就看清了,是一只老鼠!
这是一只肥大的老鼠,没有一斤但估计有半斤以上,它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不动,只有四只脚偶尔稍稍抽动一下。
它的喉咙边流着血,看样子被什么东西咬破了。
我又将手电光朝上照一照,结果看到屋顶贴着洞口露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在手电光的照耀下发出晶晶亮的反光。
很快这个东西离开洞口,屋面上又传来一阵脚步声,这回的脚步声比刚才远去的粗重一些。
尼玛,分明是一只猫。
我总算搞明白怎么回事,先是有两只老鼠在瓦片沟里嬉戏,那只猫搞了一次偷袭,当它猛地扑上去时踩滑了两块瓦片,使屋顶露出一个洞,其中一只老鼠被它咬中,另一只吓傻了不敢跑了。
但这只猫显然太粗心,嘴巴松了一松老鼠就脱了口,从洞口中掉了下来。老鼠本来就受了重伤,摔下来就奄奄一息,所以连挣扎的劲也没,一点声息也发不出,而那只猫舔着嘴巴口的血很不甘心地朝下张望,想跳下来又不敢,犹豫着迟疑着,另一只吓傻的老鼠趁机飞也似地跑掉。直到我的手电亮开,那只猫估计吃不到下面的老鼠了只好悻悻离去。
等了大半夜只等到猫抓老鼠的闹剧?
估计此时已经是凌晨,鬼物即使想来也不敢再来了。这一夜也就这点情况了。
可是仔细回想一下,又觉得情况很怪异,这两只老鼠是怎么回事呢,它们哪儿不好玩偏跑到这个老屋顶上玩,偏偏又经过了一只猫,这只猫在扑捉老鼠时又正好踩滑了瓦片,使得屋顶上开了一个小洞,而猫猫明明咬中老鼠了怎么又脱了嘴让老鼠掉下来?
猫猫这么粗心大意呀?
反正就像一台早就准备好的大戏,等我出现在这个屋子里的后半夜如期上演。如果真是一台戏,那么是谁导演的?是鬼物吗?目的就是要把我从这里吓走吧?
天亮后我从容离开。我去找到蓉香把一夜的过程简略讲一下,说明并没有遇上鬼物。
接下来我在老屋里又守了一夜,结果再没有任何动静出现,连猫抓老鼠的戏都没有了。我白白地牺牲了两夜的好睡眠。
蓉香父母十分着急,他们把杜大保送进了医院,结果医生不能确定杜大保是什么状态,他的身体在正常运转,新陈代谢并没有停止,而大脑经过CT扫描、核磁共振造像也没发现异常,而且脑电波清楚显示他的大脑是处于梦境状态。
而他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当把食物放在他嘴边时他会张嘴,喂到他嘴里会正常咀嚼和吞咽,然后要便便了还会抬起屁股做出要求,好像他明明是清醒的,这方面跟睡觉的人明显不同。
不过只有我知道他这个人产生两种状况,灵魂离开了身体,那些反应是身体机能维持正常,身体本身有着正当的调节作用,而大脑也是具备生理上的反应。
只是他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没有幸福和悲伤,作为内核的灵魂缺席了。
医生给不出恰当结论,只好不予收治,蓉香父母只能把大保又弄回家。他们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
我去上学时,碰上了白校长。大前天夜里那番遭遇对他的刺激还没有消退,脸色苍白的样子。他一见我就很想跟我说点什么,无奈校园里人太多,他也不可能把我私自拉到某个僻静角落里去窃窃私语,那样肯定勾引出学生强烈的好奇心来,反而招来过多的关注。他只是轻声问一句:“这两天在干什么?”
我也不好直白告知,只说在研究有关方面的问题。他正想再说什么,有老师来找他有事,他只好匆匆走了。
白校长刚走,白瑶就出现了。她急急问道:“我叔叔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这几天在干什么?”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在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白瑶问我那个觑灵功练得怎么样了?我对白瑶是不必隐瞒的,就直说我练出了一点名堂了,但目前的功力还是浅显阶段。
她惊喜地问:“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能看到那些……东西了?”
白瑶还是不敢说出个鬼字,她的脸上浮现着一层恐惧之色。
我说确实能看到一些影子,但也只是影子而已,而且有时也会失效,可能功力根本就不够,就像深山里的电视信号一样时显时没。
这时上课铃声响,白瑶说放学后她还有话要跟我说。
到了放学时间,我准备叫上白瑶一起走出教室,但忽然发现白校长在窗口向白瑶招手,白瑶就背着书包出去了。
我连忙跟出去,但白校长带着白瑶进了校长室,关上了门。看样子白校长好像有很要紧的事要跟侄女说,我也不便进去打扰就在外面等。
一会儿白瑶出来了,她的脸上神态相当复杂,见了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们一起走出学校大门,到了外面后我问她,白校长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白瑶看着我说道:“我叔叔的行为怪怪的。”
“什么地方怪怪的?”我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