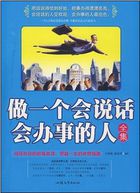一诺哆哆嗦嗦地爬上了岸,揉了揉磕碰得生疼的脑袋,没好气地白了隐云一眼,紧闭嘴巴,生怕一不小心就把他给骂了,到时再求他救苏辰就彻底无望了。
隐云见她脸色难看却强忍着不发怒的样子实在好笑,偏过头抿嘴偷乐。末了,正了正下巴,干咳了两声,说道:“如你所见,七色彩蝶遇火即燃,发出的光亮能让人于刹那间产生幻觉”,说着递上一片七色彩蝶,“以我当下的状况是没有体力助你劫狱的,这片七色彩蝶你收下,可用来扰乱守卫牢房的官兵。切记七色彩蝶的致幻能力只能维持半炷香,而且在半柱香内,被施术者的触觉、听觉并没有被完全封闭,很容易被惊醒。所以你的动作一定要快!”
却说这日何绍霆接到线报,沙茶酒馆的掌柜小姐去牢里探望了陈尧,两个时辰后才离开。
说起这沙茶酒馆就是何绍霆也要忌惮三分——与旁的酒馆不同,沙茶酒馆门前往来的人物既非名门望族,又不是富庶人家,却又确确实实因着这帮人物让沙茶酒馆举国闻名。
细说起来,要说到二十年前,那时沙茶酒馆的老板(赵四小姐的父亲)还是一个心性慈明、有着侠义心肠的年轻后生。
他走遍了名山大川,阅尽江河湖海,常常在路遇不平时仗义救急,在江湖中流传下了令人啧啧称道的好名声。
后来在他从父辈手里刚接过酒馆时,有不少来自天南海北的江湖人慕名前来捧场。
所以沙茶酒馆做的是江湖生意,四季来来往往的也都是些快意恩仇的江湖中人——因为有这些人罩着,沙茶酒馆几十年来一直过得顺风顺水,一片祥和。
何绍霆手提三寸狼毫,望着文卷出神——自从陈老将军去世后,他的不肖子陈尧没人管束,纨绔本性变本加厉。他生性嗜酒好色,俸禄微薄却出手阔绰,日子久了,身边尽是些贪图他钱财的蛀虫,没几年光景就坐吃山空了。
他又吃不得苦,一旦手头拮据,就厚着脸皮向陈老将军的那些个旧部讨要,起初大家念在陈老将军旧日里的提携栽培多多少少都会给些。后来发现那混小子愣是把他们当成了钱库了,隔三差五就登门刮刮油,渐渐地,他在大家眼里俨然成了人见人嫌、人见人怕的瘟神,人人唯恐躲之不及。
听说后来他求财无门,一怒之下,搬到青峰崖上,扬言不练就惊世骇俗的高深功夫绝不下山,有生之年再不为财去求那些无情无义之人。
他脾气不小,只是没什么骨气,不出几日就张罗了一群狐朋狗友在昱河泛舟漂流。
昱河水流湍急,暗礁遍布,他坐的那条船就是撞上暗礁后散了架。整条船的人都死了,唯有他落水后被冲到了下游,被人救起,方才捡回一条性命。
而这救他的不是旁人,正是线人嘴里的掌柜小姐——如今沙茶酒馆的当家人,赵家排行老四的赵四小姐。
赵老板总说赵四小姐是他五个孩子里脾气秉性最像他的,虽出身商贾世家,却生就一副侠肝义胆,年纪虽轻,但在那些江湖人眼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
“粗略算算,眼下开封府里可供她差遣的江湖人有千人左右。按照你的要求,开封府府君将陈尧关押在了西牢房。西牢房地处偏僻、守卫薄弱,以赵四小姐的实力别说抢出一个囚犯,就是踏平西牢房都不算妄言。可是赵四小姐去牢里探望他后,却没有什么动作,可见他们并没有外面传得那样情深意厚。”殷晴撩开长褂,躺倒在了卧榻上,翘着二郎腿,嗤之以鼻地说道:“男女之间哪有什么至真至纯的朋友情谊,以他二人来说,断然就是一场露水姻缘,哼,竟被市井小民传得圣洁无暇。”
绍霆搁下笔,淡淡地说道:“你帮我盯紧赵四小姐,劫囚这出风头还轮不上她。”
殷晴意味深长地将他望着,“若莫淇真得出现了,你……会怎么做?”
绍霆只觉得喉咙发痒,咳了一阵后,觉得肺都要烧着了,“只要她愿意回来,怎样都好。”
殷晴仰躺在卧榻上,顺手扯了一本文卷盖在脸上,十分不解地说:“你说你和少卿脑子里整日都在想些什么,抬头看看吧,天大地大,处处都是芳草连天蔽日的,何苦为难自己呢!”
说完等了半天绍霆都未搭话,涨了一肚子的牢骚,掀了文卷准备与他辩上一辩,未料想绍霆早已弃了他而去,只能长叹一口气,无奈地摇头。
再说赵四小姐,自那日一诺许诺必然要去救苏辰,她就没有再放出一兵一卒去营救苏辰。不是她怕事,而是她有另一番谋划。
下月初七就是她爹爹的六十大寿了,她爹爹素日里最爱结交的就是这类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重情重义之人。
这次劫狱是她的心上人在她爹爹面前露脸的绝佳机会,她绝不能横插一杠。
如果她的心上人能顺利救出苏辰最好,若是没救出苏辰,还不小心被抓捕了,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她只需有意无意地将一诺劫狱这出感人事迹传递给她爹爹,她爹爹一定会心生怜悯,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二人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