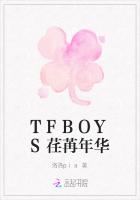修罗界,西方荒芜的戈壁滩。
烈日灼烤着大地,戈壁中腾起缕缕虚烟,灼热的空气使得一眼望去,觉得整个世界都随之扭曲了。
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只有几抹无精打采的绿色,还有几只沙蜥踩踏着滚烫的砂石,摇头晃脑地左顾右盼着,寻觅着一点仅有的阴凉。
在戈壁滩的外围边缘,一座破败的酒庐歪歪扭扭地躺着,破烂的木门随着吹拂过整个沙漠的热风轻轻摇晃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吱嘎”声,令人有些牙酸。
酒庐前一杆酒旗高高地竖着,约摸有三四丈高,旗面脏污不堪,在不知道堆积了多久的油污中勉强能认出一个修罗界的文字“酒”。
酒庐中仅有的三张桌子坐了三个客人。
坐在最角落里,端着酒杯仔细把玩的是一个红衣红发,戴着红色面纱的红瞳女子,体形很修长,但在习惯保持修罗相的修罗族人中这个体形则实在有些矮小。
女子露出的上半脸皮肤很白皙,一双眼睛似乎写满了灵性,眉间一团火焰印记,显示着女子不凡的来历。
与女子隔了一张桌子,临着窗坐着的,是一个保持着修罗相的男人。
在修罗相下,男人坐着时身高都足足有两丈许,勉强躬着身子才没有穿破酒庐腐败的屋顶。
男人眼中没有瞳孔,却有蓝色的火焰燃烧,火焰不时跃出眼眶,令人有些骇然。
男人口很阔,也很方,两根尖锐的獠牙紧贴着上唇,显得有些凶恶。
男人的桌上放着的是一只烤得流油,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野兽。
但是男人似乎没兴趣吃,放在桌上的右手,不断地轻轻敲击着桌面。
夹在那壮汉与女子之间的桌子临着门口,坐着的是一个很俊秀的男人,一身白衣,一头打理得干干净净的银发,一丝不苟地被一顶古朴的发冠束缚住,一支乌木簪子则水平地簪在发冠上。
男子很斯文地用着桌上的一只烤野兽,很斯文地用刀,很利落地下手割取肋排上最鲜美的人,每一次下手,切割的程度都刚刚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这个男人也很斯文地用着餐,细嚼慢咽,毫无声息。
这个男人一眼望去一定会认为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间公子哥,只有人间才有那么多繁文缛节。
但是酒庐里的其他三个人却不会这样认为。
因为在男人的右手边放着一个用粗布裹了的高大物件。
这个物件比一人高还要长些,宽也比一人左右肩宽还要宽些,上大下小。
让人一眼看过去,就会下意识地认定,这个男人带着的是一口棺材。
实际上,那的确是一口棺材。
因为这个人,整个六界不会有第二个。
那是一个死而复生,寻找着自己来历的人。
酒庐的老板,是一个很矮小,很瘦弱的老人,形神枯槁,就像是一盏风中的油灯,随时都将熄灭。
但是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因为这个老人是这方圆千里的唯一一家酒家。
在这死亡之地,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平凡的老人,能够支撑起这样一个酒庐,尽管它很脏,它很破败。
老人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人间才有的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不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烟雾缭绕在空中,久久不肯散去。
而老人则露出很享受的神色,轻轻将烟袋在地上磕了磕,倒出燃尽的烟丝,再将新的烟丝填入,开始新的一轮吞云吐雾。
“叮铃铃——”一阵清脆的铃铛响声,三个客人的耳朵同时微微一动,女子依然把玩着酒杯,神色漠然。
壮汉则把头扭过去,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望眼欲穿。
那个男子则取出一方白色的手帕,缓缓擦了擦嘴,才轻声道:“油脂略多了三分。”
透过蒸腾的空气,可以看到一个小黑点忽然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坡上。
伴随着一阵阵清脆的铃声,那个黑点逐渐放大,渐渐可以看清是一个人骑着一头小毛驴。那个人侧着身子坐在毛驴身上,将头微向下埋着,似乎在看右手里的什么东西。
老人眯起了眼,缓缓吐出一口烟圈,轻声道:“你们要找的人回来了。”
壮汉皱了皱眉,女子微微侧过了头,男子点了点头。
小毛驴不急不慢地走着,似乎还要很久才会从天的那边走到酒庐。
于是女子又低下头开始把玩那个已经被她把玩了无数遍的酒杯,壮汉焦躁地用右手中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男子闭上眼开始养神。
女子在这里等了二十天,壮汉在这里等了七天,而那个男子,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他们都是时间很宝贵的人,但是他们却愿意用这么多时间来等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值得他们付出这么长的时间等待。
那个骑着毛驴的人,是一个超乎他们想象的人。
也许要动手,那个人甚至连他们的小指头都打不过,但是要问一些问题的话,那个男人能回答很多问题。
至少,现在六界都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人,他能回答很多问题,就算他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至少也会告诉你一些有关的线索。
所以很多人都在找这样一个平凡人的线索,有的人只是想问他一些问题,有的人,则想把他带回自己的门派。
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找到他的踪迹,在那些找到他的人中,也没有人成功过,除了那些失败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连一个凡人都捉不住。
这个男人,自称为风。
风就是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深浅——甚至没有人知晓他真实的面貌——如果不是一个凡人行走在五界之中太过耀眼,只怕世间没有人能够寻找到他的足迹。
除了那些被他刻意留下的痕迹所引导的人。
“叮铃铃——”银铃清脆的响声愈来愈近,风终于近了。
女人放下了酒杯,壮汉扭过了头,男子睁开了眼。
他们透过窗看到风。
风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一身的粗布衣服,除了浆洗得很干净之外毫无特别之处。
他的气质,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儒雅,粗鲁,野蛮,几乎所有可以形容人的词汇似乎都与他的气质无关,也许,只有平凡才是真的合适。
至于他的容貌身形,则更是稀松寻常,毫无特点可言。
什么浓眉大眼,剑眉星目,都与他无关,只是看到了他的眉毛,才知道原来这是眉毛而已。
风终于到了酒庐,他从驴背上走了下来,他们这时候才看到,风手里拿的是一卷书。
一个这么喜欢看书的人,能够知道很多事情,似乎理所当然。
“老丈我回来了,感谢您的毛驴载我一程。”
风把书卷随手塞在了腰间,笑着和老人打招呼。
一个月之前风正是从这里离开进入了死亡之地。
老人眯着眼看了看楚风,牵过毛驴的缰绳,道:“我去喂草。”
风笑着道:“那有劳老丈了。”
说着,风迈进酒庐中,很自然地在男子对面坐了下来,似乎根本就没有刻意地选择桌子,一切都很自然,自然得让人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妥。
风微微向男子拱了拱手,道:“打搅了。”
男子还了一礼,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
壮汉很想过来,但是他才站起身,头便猛地撞穿了酒庐的屋顶,想要挣扎出来,又怕毁了这座酒庐,一时进退不得,卡在那里。
风有些忍俊不禁,露出一分笑意。
最先动起来的是那女子,那女子缓步上前,走到风身边,轻轻一揖,道:“见过风先生。”
风急忙起身还礼,道:“见过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