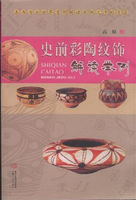他在城里没工作,没亲人,要去投靠谁?邓志超早没了影儿。他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不可能无限期无偿照顾一个精神病。更何况,听闻他的特殊嗜好后,他那些同事和朋友个个避之不及,遑论照顾。
林俐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偏远、荒凉的小山村。秋意深浓,一间杂乱低矮破败的小房子由远而近。任军他妈出现在了黑洞洞的房门口,身上是破旧肮脏的衣裤。昨夜似是下了一场秋雨,她的旧胶鞋上沾满了黄泥和杂草。
从画面上判断,应该是深秋了。院中的歪脖树上,树叶已经脱得一干二净。任军他妈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黑瘦多皱的脸上,再不见当初的刁蛮与霸道。
“军啊,妈上山打猪草去了!你在家好好呆着,妈中午回来给你作饭!”任军他妈从廊下拿起一个竹编的大背篓,背在背上,走出了院子。背有些弯,脚步有些蹒跚。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黑洞洞的房门里走了出来。林俐认了又认,才勉强认出那是任军。
一个潦倒、落魄、颓废、蓬头乱发,满脸胡渣的任军。衣衫肮脏不整,目光呆滞,如果不是他还戴着原来的眼镜,这个任军与那个大学讲师任军压根儿没有丝毫相象之处。
直着眼,任军一步步走下湿滑的石头台阶,走到老树跟前,围着老树开始一圈接一圈地转。口中念念有词,“我是教授……我是教授……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不来看我……”
所有的“教授”和“为什么不来看我”声音都比较小,像在低声念经,又像在自言自语。只有中间的某一声“为什么不来看我”任军是仰着脖子,冲天吼出来的。这一嗓子穿云裂雾,惊起远近一阵高高低低的狗吠。吼完这一嗓子,任军咳了两声,又恢复了先前的音量,接着转,接着念。
如此转了能有十来圈,任军贴着树皮,在老树下蹲坐下来。直着两眼抱着膝盖默默坐了一会儿,他又直着眼睛站了起来,开始动手解裤腰带。
银幕上出现了特写,任军的手和任军的裤腰带。手黑脏粗,裤腰带跟手差不多,是一根没锁边的破布条子,不再是先前的名牌皮带。
拎着解下的腰带,任军仰起头去看老树的枝桠。木着脸看了一会儿,他把裤腰带向其中一根枝桠抛去。一次,没挂住。再抛,又没挂住,再抛……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六次的时候,他终于让裤腰带和老枝桠成功对接。
被他妈接回农村后,任军的头脑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任军情愿自己永远糊涂,不再清醒。清醒,对他而言,是份太过痛苦的煎熬。
清醒时,他会想起儿时过的苦日子,想起十年寒窗苦读的艰辛,想起自己站在大学三尺讲台上的意气风发,想起城里气派的楼房,通透的落地窗,想起邓志超,那个发誓要和他一生一世在一起的亲密爱人。
后来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脸没有了,爱人也没有了。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他又回到这个他为之厌恶的穷乡僻壤,又回到了这个穷得叮当乱响的家,又躺在了他曾经躺了十八年,吱嘎乱响的破烂木板床上。
永远下不完的雨,永远不见放晴的天,永远光线阴暗充满了浓重霉味的老房子。他曾以为再不会回到这里,结果又回来了。
任军把裤腰带挽了个活套,双手拉着裤腰带的两端,直着眼睛愣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他闭上眼,把脑袋伸进了活套。双腿一屈,任军的身体向下矮去,活套也随之拉紧,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任军死了。
画面一转,转到了张家宽敞明亮的客厅。张父、张母、张佳佳和一个气质斯文的男人,一个可爱的胖娃娃,出现在了银幕上。
张家父母轮流去抱那孩子,又逗又亲,逗得孩子舞着小手,叽嘎有声,张佳佳和男人望着孩子笑,张佳佳不时抻一下孩子的裤腿。
林俐不解,“张佳佳不是死了吗?”
三女神中最矮的那位告诉她,“原来的张佳佳是死了。但是我们让另一个人在你走后,附在了张佳佳的身体上,代替原来的张佳佳继续活下去。”
“那她以后的人生会一直很好吗?”
“对,会一直很好。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个画家,非常爱她。”最胖的女神告诉林俐。
林俐盯着银幕,没出声。幸福就好,如果在自己离开后,没有新的灵魂进入张佳佳的躯壳,那么张佳佳就算真的死了。她的父母该是多么凄惨!虽说那副躯壳中的灵魂不再是最初的张佳佳,对不知情的张家父母而言,并无分别。
“想不想知道,我们给你什么奖励?”三女神中声音最好听的那位问林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