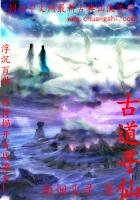这一生从记事起,再没有人敢这般近他的身。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是嫌恶惧怕甚至憎恨,犹如看一件本该早早弃如敝履,却因某个缘故不得已只能放置眼前的脏物。
他起初不懂为什么,哭闹过抗争过呵斥过,他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对他?
直到那一天——
穹顶之上,沉沉风雪呼啸而下,遮不住满庭血光残肢。他在雪地里嘶吼,如魔神初临世,漾开第一缕惨厉的笑。
没人相信他也在害怕也在哭泣,地上是血肉混合着那残雪,竟交融出异样的堕落与魅惑之感,如地狱魔鬼伸出罪恶之手,桀桀嘶笑,幽幽召唤,叫人忍不住沉沦。
雪贯长空,血色殷然,可疑的碎肉残渣铺满整个庭院,那恍如地狱的一幕,人群里毫不掩饰的嫌恶与惊惧,还真是,想忘记,都做不到呢。
鎏金面具下的眼眸寒沉如雪,细碎的光芒流转如碎钻如浮冰,如满天星光忽然降下,看见一场神迹。
宁朵忽觉有些冷,身子忽然动了动,一条腿啪一下搭上某人的大腿,脸往胳臂窝里钻了钻,手却无意识拉住一抹袖子,又往嘴角擦了擦。
看来她还知道自己睡觉如此无状!
他忍了又忍,极力忽视了玄衣上那一块深色水渍,转眸望住宁朵满足的睡颜,忽然觉得,似乎也只有她这样的女子,才堪配这鲜明开阔的个性?
不知不觉中,面具下冰绝般的神色,渐渐变得柔和。
这一次她似乎没有做什么乱七八糟的梦,也不如上一次那么警醒,睡得很平和安详,纯净如同婴儿一般。
==
马蹄声依旧“得得得”敲击着青石铺就的街道地面,低调奢华的马车里,司陵无极手握一卷书漫不经心看着,动作只是稍稍随意,便带了些缱绻慵懒之气。
紫色原本是那样尊贵冷艳的颜色,穿在他身上,却衬出一身如仙如梅的高华气质,叫人觉着这颜色和他那般契合,再没有别人,能把紫袍穿出这样的风姿。
他忽然微微皱眉,远远缀在后边那辆马车,规律的车轮轧地的声有一瞬间重了些许,但立刻恢复了正常频率。
抬手,书册轻轻敲击窗柩,不多不少正三下,声音微不可计。
然,逃不过真正武功高强之人的耳朵。
鎏金面具下优美的唇线微微抿起,勾一抹冰冷弧度,那个人——感觉一向敏锐,他不过一瞬间心神失守,露出些微破绽,马车遥隔半条街,竟也第一时间被察觉?
可见他的武功,又精进了。
倒也不算枉费那每月一粒的凝血丸,十几年如一日,天天不间断滋养。有人每月割血,痛不欲生狂性大发;有人以血入药,鲜血浇灌体质完美。
得他人以身饲功,练武永远事半功倍,武道巅峰指日可待,不是么?
嘴角微勾,一抹冰寒笑意。
他最后望一眼宁朵不算优雅的睡颜,轻轻拉开她缠住他胳臂的手,身形微微一晃,错眼便消失在马车内。
凌无涯消失在车内那一刻,隐在暗处的稚生也听到讯号。
他豁然起身,身形暴起飞掠如蝶翼,几乎瞬间就来到宁朵的小破马车上,大手一挥掀开车帘,只见——
宁朵正抱着背包睡得鼾声四起,两条腿交叠缠住坐垫,睡相十分不雅。
稚生微微一怔,随即目光一掠,马车里除了宁朵,什么都没有。而马车空间就这么大,决计不可能藏住人。
但老实人稚生坚信少君的判断不会出错,他正要进去查问宁朵,赶车的青衫弟子终于回过神来,伸手一拦,喝道:“你你你,你要干什么!须知这是凌云天门的马车!”
这厮是庆州凌云分部新近入门的弟子,没有见过少君身边这位武功出神入化的护卫,见对方身法诡异骤然出现在身边,心中甚是忐忑。
稚生默不作声,一把将人拨开,探头往马车里钻。
宁朵睡穴适才已经被解开,这一声大喝吵醒了她,迷迷糊糊中一仰头,便看见一颗大好头颅出现在眼前,什么鬼这是!?难道又有偷袭!?
上次在马车上差点被砍死的后遗症发作,她顿时一个激灵,抬手一巴掌就呼了上去,顺道大喊一声:“救命啊——有刺客——”
“啪!”巴掌声清脆回响在马车里。
稚生不妨她突然动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有点蒙,一时间竟是愣住了。
自他跟随少君行走江湖这么许多年,江湖中能动他的人已经十分少有,更遑论被一个没有丝毫武功的人打脸。
简直是……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