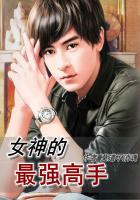女孩按照医嘱脱了裤子躺到了床上,两脚放到了架子上,因此胯部大开,这个动作好像使她想起了什么事,一张脸羞得更是通红,目光无处着力,只好轻轻闭上,既然来都来了,那就豁出去了,治病要紧。
女孩的下体被自己抓伤了,留下许多抓痕,新的,旧的,严重的出了血,旧的结了疤。
“这样很久了吗?”张芬芳问。
“有两个多星期左右,刚开始只是一点点痒,后来是越来越痒!”女孩仍闭着眼睛说。
“结婚了吗?”张芬芳又问。
“结了!”女孩在张芬芳的眼里顿时升级为少妇。
“就是毛发周围痒是吗?下面痒吗?”张芬芳问。
“下面不痒!”少女老老实实的回答。
张芬芳对着病症位置仔仔细细的检查了起来,然后拔了几根少妇的****,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了起来,不一会她皱起的眉头便松开了,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少妇病症的源头。
“你得的是阴虱,可是照道理来说你不应该得这种病的啊,你那么年轻,年轻人爱漂亮,爱干净,很少会得这种病的,一般是上了年纪的妇女,而且是极不注意个人卫生的才会得这种病!”张芬芳很是不解的说。
少妇闻言无奈的叹了口气,这才娓娓道来。
张芬芳听完少妇叙述后,让她穿回裤子,带着她一起出去了……
“医生我不舒服!”
小冲正洗手的当下,一个患者走了进来,他没回头看就闻到了异味,一股很难闻的馊味,就如隔了好几夜的饭菜一样,小冲赶紧带上了口罩这才转过了身。
来者是一个披散着长发,胡子长过头发,穿着黑色魔鬼图案的T恤,一条灰旧得根本就分不清什么颜色还破了无数大洞小洞的,不修边幅颓废得不行的男人。
“哪里不舒服啊?”小冲看了眼男人不禁皱着眉,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实在太熏人了,只怕是至少三五个月没冲凉了。
“下面痒得要命啊!”男人说着便无所顾忌的去解那巨大虎牌金属头的皮带。
“等一下,等一下!”小冲赶紧去关门,这个人连基本的廉耻都没有了,不死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原本赤条条的来,又何惧赤条条的显露于人,医生太拘泥于世俗了!”小冲关门的时候,男人解裤子的动作并没有停,等小冲把门关好的时候,男人已然把下半身脱得赤条条的了,小冲看到了他肿大的下身,病情已了然于胸。
“行了,穿回裤子吧!”小冲说着坐回座位。
“医生,你看清楚了吗?”男人没有穿回裤子,这才一眼,他有点不放心医生是否真的了解了他的难处。
“看清楚了,很大很肥壮!”小冲没好气的说。
“不是的,我是说痒的原因!”男人又道。
“放心,也看清楚了!”小冲说着脱下手套扔到垃圾桶中。
“那有得治吗?没得治我就不治了!反正痒点,痛点,苦点,累点,饿点,饱点,冷点,热点,日子还是一样过的!”男人的话与他的人一样颓废。
“有得治,出来填个病例吧!”小冲说着却在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过法,可是像这样的人这样的活法,他却是第一次见,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小冲摊开病例问。
“叶听雨,叶落归根的叶,小楼一夜听春雨的听雨!”叶听雨报上姓名。
“多大了啊?”小冲又问,心里暗骂:我不识字吗?要解释得这么清楚。
“二十五,去年二十五!”叶听雨道。
小冲正想填下二十六的时候,叶听雨却突然又说:“前年好像也是二十五!”
“无语了,你以为你是谭校长年年二十五吗?”小冲忍不住来气了,原本他身上的味道就熏人,还要纠缠不清,实在让他受不了。
“医者父母心,医生必须有耐心,忍世间不能忍之事,戒骄戒傲戒浮燥啊!”男人说话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种威严,让人不得不正视的威严。
“先生教训的是,不过你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重!先生,还是注意点个人卫生比较好,以免滋生细菌,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小冲见他是个阔达不拘小节的人,也懒得与他转弯抹角,直话直说了。
“医生,这些都是浮云,生活中到处都是细菌,让人难以反抗的!”叶听雨人虽糟蹋,但话却说得甚有哲理。
小冲把口罩紧了紧,没有犹豫的在他的病例上填上二十五岁,然后又问:“先生现在从事何工作!”
“嗯,这个不好说!”叶听雨偏着脑袋,捋了捋遮住了眼睛的长发说。
“怎么会不好说呢?”小冲奇怪的问。
“我给中文系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叫我哲学家;我搞画展的时候,他们又叫我画家;我去神农架寻找野人的时候,他们又叫我动物学家;我跟着别人去盗墓的时候,别人又叫我考古学家。我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你现在做什么啊?”小冲再次耐着性子问。
“我三个月前从神农架回来,暂时在家里,还没想到去做什么!”叶听雨说。
“那现在别人应该叫你坐家了!”小冲给他想了一个贴切的词。
“对对对。医生的话太有建设性了,我该写作,对我该写一部书!医生你真是我的知音啊!”叶听雨说着伸出手就想去握小冲的手,小冲却极敏捷的躲开了。
“你有多久没冲凉了?”小冲问了关键问题。
“我算算,从去神农架到回来,可能有一年多了吧!”叶听雨说。
“那为什么不冲凉呢?”小冲再问。
“好像在神农架的时候养成习惯了,回来后一直不想冲凉,我本是个率性而为的人,既然不想冲,何苦为难自己呢!生活中让我为难的事已经够多了!”叶听雨说。
“那你又来为难我?你不想为难自己,现在却为难你自己的身体了!”小冲没觉得这家伙有多高尚,反而觉得他愚不可及,这样的行为艺术家在街上随随便便一抓就能抓住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