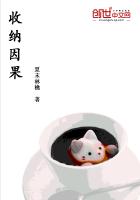戴氏所以能超出当日无数“襞绩补苴”的考核家而自成一个哲学家,正因为他承受了清初大师掊击理学的风气;正因为他不甘学万斯同的“予惟穷经而已”的规避态度,而情愿学颜元“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攻击态度。
段玉裁虽然终身佩服戴氏,但他是究竟崇拜程朱的人;他七十五岁(1809)作《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十三~十五页),自恨“所读之书又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又说朱子此书“集旧闻,觉来裔,……二千年贤圣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怪不得他不能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戴震同时有一位章学诚(1738~1801),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他颇能了解戴氏的思想。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朱陆篇书后》)
章学诚最佩服他的老师朱筠;但这段话却正是为朱筠等人而发的。章氏也是崇拜朱子的,故他虽能赏识戴氏《原善》《论性》诸篇,却不赞成他攻击朱子。他说戴学本出于朱学,不当“饮水而忘源”。他作《朱陆篇》说明这一个意思:
……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想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
这一段赞扬戴震最平允。他说朱学的传授,也很有理:
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已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即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
章氏说戴学出于朱学,这话很可成立。但出于朱学的人难道就永远不可以攻击朱学了吗?这又可见章学诚被卫道的成见迷了心知之明了。他又说:
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
这也是似是而实非的论调。新历之密可以替代旧历之疏,我们自然应该采用新历。但是,假使羲和的权威足以阻止新历的采用与施行,那就非先打倒羲和,新历永无采用的希望了。颜李之攻程朱,戴学之攻朱学,只因为程朱的权威太大,旧信仰不倒,新信仰不能成立。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翁方纲(1733~1818),他对于戴震的考订之学表示热烈的崇拜,但对于他的哲学却仍是盲目的反对。
翁方纲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书法大家;但他无形中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对于金石文字很做了一点考订的功夫,成绩也不算坏。他作了九篇考订论,颇能承认顾栋高、惠栋、江永、戴震、金榜、段玉裁诸人的成绩。
有一次,戴震与钱载(字萚石,是当时的一个诗人)争论,钱载排斥考订之学,骂戴震破碎大道,——这件事也可见当时对考据训诂之学的反动,——翁方纲作书与程晋芳,为钱戴两人调解。书中说:
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
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复初斋文集》七,二○)
这话几乎是偏向戴学的人说的了。然而他虽然说“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他却只许戴震讲考订,而不许他讲义理。这种不自觉的矛盾最可以考见当时的学者承认考订之学本非出于诚意,只是盲从一时的风尚。
当他们替考订学辩护时,他们也曾说考订是为求义理的。及至戴震大胆进一步高谈义理,他们便吓坏了。翁方纲有《理说》一篇,题为《驳戴震作》,开端就说:
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
这就是戴震的罪状了!考订只可以考订为目的,而不可谈义理:这是当时一般学者的公共心理。只有戴震敢打破这个迷信,只有章学诚能赏识他这种举动。朱筠、翁方纲等都只是受了成见的束缚,不能了解考订之学的重大使命。
翁方纲驳戴震说“理”字,也很浅薄。他说戴震:
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其反覆驳诘牵绕诸语,不必与剖说也。惟其中最显者,引经二处,请略申之。
一引《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试问《系辞传》此二语非即性道统挈之理字乎?……
再则又引《乐记》,“天理灭矣”。此句“天理”对下“人欲”,则天理即上所云“天之性也”,正是“性即理也”之义。而戴震转援此二文,以谓皆密察条析之理,非性即理之理,……可谓妄矣。
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假如专以在事在物之条析名曰理,而性道统挈处无此理之名,则《易·系辞传》、《乐记》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复初斋文集》七,十九)
戴震引《系辞传》在《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引《乐记》在第二条,读者可以参看。他释“天下之理”为“天下事情,条分缕晰”;他释“天理”为“天然之分理”,引《庄子》“依乎天理”为证。这种解说,本可以成立。翁氏习惯了“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理字解,故绝对不能承认戴震的新解说。
这班人的根本毛病,在于不能承认考订学的结果有修正宋儒传统的理学的任务。若考订之学不能修正义理的旧说,那又何必要考订呢?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篇篇皆归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一句话(《复初斋文集》七,六~十八)。他说:
学者束发受书,则诵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迨其后用时文取科第,又厌薄故常,思骋其智力,于是以考订为易于见长。其初亦第知扩充闻见,非有意与幼时所肄相左也。
既乃渐骛渐远而不知所归,其与游子日事漂荡而不顾父母妻子者何异?考订本极正之通途,而无如由之者之自败也。则不衷于义理之弊而已矣。
这样看来,“义理”原来只是《章句集注》里的义理;不合这种义理,便等于游子不顾父母妻子。怪不得翁方纲一流人决不会了解戴震的哲学了。
同时,还有一位姚鼐(1732~1815),是一个古文家;曾从戴震受学,称他为“夫子”,戴震不受,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后来姚鼐竟变成一个排击考据学的人,他主张: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
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吾大不以为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耳。吾亦非谓宋贤言之尽是;但择善而从,当自有道耳。(《惜抱尺牍》,小万柳堂本)
这些话还算平易。但姚鼐实在是一个崇信宋儒的人,故不满意于戴学。他说: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因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正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赠钱献之序》)
反对宋学的人,如费密、颜元等,都说明朝亡于理学;然而姚鼐替理学辩护,却说宋学之效能“使明久而后亡”。这都是主观的论断,两面都像可以成立,便是两面都不能成立。姚鼐晚年最喜欢提倡宋儒的理学,如他说:
士最陋者,所谓时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读书者,又相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尝(常?)不免猥鄙,行事尝(常?)不免乖谬。愿阁下训士,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尺牍》五,七)
他在1808年还有“内观此心,终无了当处,真是枉活八十年也”之叹(《尺牒》六,二八)。所以他晚年又常学佛,并且吃斋,自称“其间颇有见处”(《尺牍》五,二〇)。这样的人怪不得要攻击戴学了。他常有不满意于戴震的话,如说:
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尺牍》六)
他本去考量戴氏讲的“义理”究竟是怎样的,却先武断戴氏不配讲义理,这岂不是“愚妄”吗?
他又说:
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
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复蒋松如书》)
为什么不可跨越宋儒呢?姚鼐的答案真妙: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再复简斋书》)
程晋芳说诋毁宋儒的要得罪于天;姚鼐说诋毁程朱的要“为天之所恶,身灭嗣绝”。可怕呵!程朱的权威真可怕啊!
然而这种卫道的喊声却也可以使我们悬想当时程朱的权威大概真有点动摇了。反对的声浪便是注意的表示。颜李攻击程朱,程朱的门下可以不睬他们。
如今他们不能不睬戴震的攻击了。程晋芳、章学诚、姚鼐出来卫道,便可见正宗的理学有动摇的危险,有不能不抵御的情势了。章学诚的说话更可以表示戴学的声势的浩大。他说:
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朱陆篇》)
他又说:
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而诽圣诽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朱陆篇书后》)
章氏作书后时,自言“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十余年的时间,已有“流风大可惧”的警言,可见戴学在当日的声势了。
方东树在十九世纪初期作《汉学商兑》(见下文),曾说;
……后来戴氏等曰益寖炽;其聪明博辨既足以自恣,而声华气焰又足以耸动一世。于是遂欲移程朱而代其统矣。一时如吴中、徽歙、金坛、扬州数十余家,益相煽和,则皆其衍法之导师,传法之沙弥也。(《汉学商兑》,未刻本下,二八)
这话可与章学诚的话互相证明。戴震死于1777,《汉学商兑》作于1826。这五十年中,戴学确有浩大的声势。但那些“衍法的导师,传法的沙弥”之中,能传授戴震的治学方法的,确也不少;然而真能传得戴氏的哲学思想的,却实在不多,——几乎可说是没有一个人。
大家仍旧埋头做那“襞绩补苴”的细碎功夫,不能继续做那哲学中兴的大事业。虽然不信仰程朱理学的人渐渐多了,然而戴震的新理学还是没有传人。
戴震死后六年(1783),他的同乡学者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1755~1809)到北京。凌廷堪也是一个奇士;他生于贫家,学商业,到二十多岁才读书做学问。
1781年,他在扬州已知道他的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了;他到了北京,方才从翁方纲处得着《戴氏遗书》;过了几年,他又从戴震的学友程瑶田处得知戴氏作学问的始末。从此以后,他就是戴学的信徒了。
他曾作一篇《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叙述戴氏的学问,最有条理;戴震的许多传状之中,除了洪榜做的《行状》,便要算这一篇最有精采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