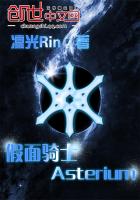山凤醒来的时候毛蛋站在床头。毛蛋眼中含着泪说,都是因为山凤太劳碌,平时不注意休息,大夫说怕累出其他病,要做全面检查。山凤说:“不会的,只是娃儿不听话,一时气晕了,挣挣就好了。”
医生护士来来去去地走着,一个医生用关注的目光不时地向张山凤这边投来,他是对病人的病有所怀疑,似乎不能确诊。
“姐,身体要紧,你真的不敢太劳累。医生那样说是有道理的。”毛蛋劝着说。
“医生说的话你也信,医生会把芝麻大的病说得碗口大,哪个医生不是为了挣钱……”
“你还是好好歇息吧,饭店有我呢,你以后不要太劳累。”借着下午有些空闲,麻秆子特意来看她。
麻秆子安慰她,却悄悄地告诉她,听说春喜的媳妇玉锦最近张罗着结婚,这婆娘好像忘了春喜妈和小泉泉,说是没有了春喜,就没有了主心骨,她要找个能给她遮风当雨的人,清苦的日子她是过不下去了。
“都是谣传,信不得。”张山凤说。
“你不信,是你还蒙在鼓里,无风不起浪,说不定这几天会有人来找你。”麻秆子神秘地一笑,好像自己也是算命先生,能预测着事情的发展。
“把孩子让她带走,她的孩子她不管,你凭什么管?不能苦了自己,舒服了别人。”毛蛋快人快语地说。他觉得姐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再增加两个人,这日子就更加难过,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姐姐受罪,如果姐姐不愿意,他决定悄悄地打听到那女人的住地,把孩子送过去,自私的人就要用自私的办法整治,不能把自己的包袱甩给别人。
“不能相信谣言,不会的,她不会是那种女人。”
“你还是不相信?社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人都是在为自己着想……”
“你——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不信。”张山凤看着毛蛋,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觉着他似乎不像是自己的弟弟,小小年纪,居然有这样一些自私的想法。
“有啥信不信的,如今的社会,啥样的事都可能发生。”麻秆子却赞同毛蛋的观点,“这女人过去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突遇变故,没了生活来源,就要想想其他办法,一个女人家那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也不能丢下自己的孩子。”毛蛋很是生气。
“也许是生活所迫……”张山凤说。
“这不是理由,人生谁不遇到一点坎坷。”
“可她到底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麻秆子说。
果然,过了几天,毛蛋领着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来找山凤。那女人脸上露出悲凉的笑意,见了春喜妈泣不成声,几乎要跪了下去。她拉着春喜妈的手说:“妈呀,媳妇对不住您老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是没有办法,春喜一年多了没有音信,人们都说也许不在人世了,也没有地方去找,我如今也没本事养活你们,就起了……再嫁的念头,妈呀,你要谅解儿媳妇,这清苦的日子实在难熬啊。”
“你——早就串通好了的,你当我不知道,那野汉子是谁,你说?”春喜妈听着李玉锦的话,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儿子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她正为儿子的事情堵心,媳妇却在追寻自己的幸福和欢乐。这样的女人让老人打心眼里感到讨厌。
“你去找你的野男人吧!我祖孙俩用不着你管……”老太婆捣了捣手中的拐棍,对着玉锦恨恨地说。
“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只是,这日子难过……”
春喜妈抡起了手中拐杖,在空中胡乱划拉,情绪非常激动,失明的眼睛无神地大睁着,看得出她已经非常愤怒。
“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你别看我老婆子眼睛瞎,心里可亮堂着哩,你是早就串通好了野汉子,你当我不知道,只可怜我那孩子……”
“春喜不会有事,等灾区秩序正常了,他也许就回来了。”麻秆子劝着那女人说。
“你这样做不好,应该等等。”张山凤对那女人说,“时下里政府正在全力救灾,乱也不会很长时间的,说不准春喜哪一天就会回来,眼下你只要挺过这一关……”
“我老婆子快死的人了,日子难不难的无所谓,这一辈子都是在坎坎坷坷中过来的,只可怜我这小孙孙。”
“是啊,人活世上,谁不遇个七灾八难,你这样做,万一春喜回来又咋办?”麻秆子还在一旁劝说着那个女人。
“可,我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女人,我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何况他们祖孙俩……”
那女人彷徨着,不知所措地在自己的选择中纠结。
“我是想啊……可是这日子我是实在没法挨啊……春喜猴年马月能回来,谁也不好说,要不我就……再等一等。”这女人一时也犹豫起来,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在张山凤手中说:“我的好姐姐,这是两千元,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好人做到底,让他祖孙两个待在你家,等我有了历程,或许春喜子回来,我就接他们回去。”
儿子泉泉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就是不近前。这女人眼睛里满是殷切的疼怜,她似乎希望儿子能够近前,母子疼爱一番,她柔声地叫着儿子;“泉泉,过来让妈看看。”
大家用热切的眼光看着孩子,期望母子拥抱疼爱的场面。
“我没有你这妈。”那孩子一脸的怨气,脆脆地回了一句,好像眼前的女人并不是他的母亲。他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笔和本子,旁若无人地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做起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那女人不知所措,眼睛红红的,心里好像真的疑虑着,眼前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你这是咋说话哩,妈是你亲亲的妈,你是妈亲亲的娃,你咋也不理解妈,妈也是没有办法管你呀,这几天把你放在外边,妈的心都疼碎了……你,你的心咋就变狠了呢?”那女人鼻子酸酸的,悲凄地看着孩子,那孩子却无动于衷,只是做着自己的事情,对自己母亲的呼唤甚至不正眼看一看。
毛蛋和山凤也过去哄着孩子,希望孩子能够叫一声“妈”,以缓和母子之间的这种尴尬。那孩子却一头扑到老太婆的怀里,埋着头,抹起了眼泪。
李玉锦静静地看着,脸上表情木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她惊恐地觉着,在孩子的心里仿佛已经抹去了母亲神圣的形象。她呆呆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面对眼前的情况。孩子对她的淡漠和痛恨,像一把无形的情感之剑,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孩子家不懂事,也不知道大人的难处,你就别往心里去。”张山凤劝着她。她知道孩子的冷漠使这女人痛苦万分。
“小孩子谁养谁亲……可是你总归是孩子的妈。”麻秆子想给那女人宽宽心。
“你也算是孩子的妈?”半天没有言语的老太婆说话了,虽然眼睛看不到,耳朵却灵着呢,只管听几个人说话,心里却满是愤恨,“你把我们祖孙俩往心里去过,你对得住春喜子么?我的儿子命大着呢,告诉你,他会回来的,你要找你的相好的,当心受到报应。”老太婆捣了捣手中的拐杖。
这一场婆媳大战将要爆发,张山凤赶紧示意毛蛋把老太婆扶到里屋去,再打发那女人快点离开。
李玉锦心中也着急,她那位老情人正等着她赶快回去。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她想了想说:“妈呀,我这不是说了吗,等春喜回来我就接你们回去……”
“你哄谁呀,你当我老婆子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你想的就是你的那位相好的……当心受到报应。”老太婆边往屋里走边回应着。
“如果你实在有难处,他们就在我家吧,”山凤边推却李玉锦递过来的一沓钱边宽慰她说,“你现在困难,你的钱你拿上。”
“不,那是我的一点心意。”
李玉锦走了,当她回头看时,张山凤还拿着那一沓钱向她招手。
“使不得,你得拿着,我总得对住我的良心。”那女人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县城医院大厅里,挂号看病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龙,上午一般是医院最忙碌的时候。而且,即使挂上号,轮到看病也得等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各个科室都是人满为患,所以病人要有极大的耐心等待。
一直到了十二点以后医生才给张山凤看病。检查程序繁多,也是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等待。因为平时没有到医院看病的习惯,有了小病的农村人一般只是自己对症买药,或者按照医生吩咐,去附近的药店买一些自己需要的药,这样的等待让张山凤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她有点不耐烦。
“等着吧,耐心等待,现在的医院就是这个样子。”毛蛋和小锁子劝着山凤。给张山凤检查完后,医生的情绪怪怪的,他对毛蛋说:“明天来取结果,这病需要进一步检查。”
毛蛋和小锁子陪山凤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夕阳的余晖洒在喧哗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人们显得匆匆忙忙。小锁子眼尖,突然看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熟悉身影一闪,钻进一个小胡同。他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惊叫,因为这个人曾经是他最熟悉的人。
“咦,这不是赖子叔吗?他咋变了样儿。”小锁子用手指着一个身影,口气肯定地说。
“你不要认错了人,看那模样,是个叫花子。”毛蛋说。
“他就是赖子叔,烧成灰我也认识他……”小锁子还是不改口,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不会因为一个人外表的突然改变而认错这个人。
“不要乱说,你赖子叔可不是一般的人。”张山凤也有些不太相信。毛蛋盯着那身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就是三赖子。”
他这样肯定,是因为三赖子那张三角脸,在趾高气扬的时候总是高高地扬起,看人时眼睛向上翻着,让人觉得他是居高临下,这是他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因为是个习惯动作,一下子让毛蛋看了出来,所以毛蛋确定他就是三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