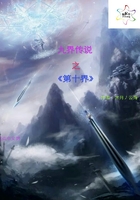荣华还未说什么,碧秋倒是有些怒了:“你这老汉,我家夫人蒙面而出,你竟能看出面善与否么!”
“看你们这穿着打扮也并非是不知礼之人,为何对我家夫人目光灼灼?”
欧阳鸣一介大儒,尚不曾被一个丫鬟如此嘲讽过,偏生说的是事实,心下便有些尴尬,见自己的徒弟还在打量,心下便是不满,若不是傅文景先对这位夫人打量频频,他又何至于丢此脸。
只见他面上肃穆了神色回道:“在下欧阳鸣,曾任国子监祭酒一职,今日乃是为故友扫墓而来。”又侧身示意一旁沙弥道:“刚刚听这位寺院师父道,夫人也是前来为苏大人扫墓,误以为是旧交,这才冒然相问。”
“若是有所唐突,还望见谅。”
众仆妇自然知道荣华来此为何,碧秋听得此言还要再说,荣华抬起手示意退下,只见她上前一步,却又迟疑着后退了些,白纱后一双美目轻撇了欧阳鸣一眼,道:“原来您便是鼎鼎有名的大儒,欧阳先生……”
“想来此事不过是一场误会,倒是奴家的下人不知原委冒然驳斥,失礼了。”
欧阳鸣见这位夫人这望来的一眼,熟悉感愈发深刻,心下疑惑,道:“老朽不敢担鼎鼎大名四字,在下的徒儿失礼于前是实,文景,还不向这位夫人赔罪?”
自知失礼,又被撞个正着,如今师父已点出,傅文景面上发烫,低下头去施礼道:“在下失礼了,还望夫人见谅!”
荣华侧身受过这一礼,也不说什么,只突然高声对着欧阳鸣问道:“您说您是为苏大人扫墓而来?”
欧阳吗不知这夫人是何意,便道:“是,老朽与苏大人相识于年轻之时……”说到这,他似乎有些感慨道:“他骤然离世,老朽骤失一知己……每每想到,心下悲痛。”
“哦?既然是知己,又这般悲痛......”
“今日乃是苏大人的忌日,您为何这时才到呢?”
荣华白纱覆面,遮去了那冷漠的面容,可这话语一出,仍然让四下一静。
荣华似乎不觉,又抬头看了看天,日光炽炽,叫人忍不住眯了眼。她借这刺目的日光叫眼里含了泪,这才双目直直对着欧阳鸣道:“古语有云,士为知己者死,这其中不光指知遇之恩,也未尝不是指的是朋友之谊,非比寻常。”
“欧阳先生既然与苏大人有旧,但苏大人已身故,先生连扫墓一事都要姗姗来迟,却大谈知己二字,若是旁人见了,误会先生如何是好?”
“你!”傅文景听这讽刺之语,心下气愤,忍不住道:“家师与苏大人乃是多年至交好友,世人皆知!夫人还请慎言!”
欧阳鸣一把拉住傅文景,摇摇头道:“文景,不可无理……”
他心下黯然,抬眼见这位夫人虽然言辞坚厉,看向他的目光却隐隐含着泪水,这眸子这般哀怨婉转,似乎透过这双眼睛,能看见她心中已是哀痛欲绝!
心下怔忪,道:“我......的确愧对苏兄。”
他忍不住上前几步,想靠近这位夫人,却被围绕在荣华身边的仆妇拦下。
荣华见状心下着急,这欧阳鸣难道老眼昏花了不成,比起傅文景难得见苏芷几次,作为苏父好友的欧阳鸣每次来家中,苏芷都会去请安,虽然未曾交谈过几句,到底应该是认得出她的面目才是!
苏芷生的这样一双好眼,又天生这般仪态,竟然叫这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老人都认不清么?!
若是此时揭开白纱,又过于刻意。落了下乘。
荣华想了想,作势欲离开,待得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有些迟疑道:“碧秋,我适才好像将我的荷包落在墓前了。”
“啊!是那个装有诗句纸条的那个荷包?”
碧秋想着自家夫人似乎很重视那个荷包的样子,道:“奴婢现在便回去取!”
“唉,等等!”荣华一把拉住碧秋,感叹道:“罢了,他曾希望我,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我既未能做到,又何必还将它们带在身上。”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主仆二人又未走远,动静自然不小,听得此语,别人不知,欧阳鸣却是一惊,这句话不是当年苏兄曾对他的女儿说过的话么?
难道……
“你是......你难道是苏兄的女儿,苏芷?”欧阳鸣急急喊道。
来了。
荣华忍不住想笑,脚下步伐一顿,轻轻转过身,发丝如墨,一身白衣,清冷若雪,话语更是冷淡。
“苏芷?原来先生记得我,还以为先生早已经忘记了家父还有我这个女儿了。”
“你这话是何意?你父亲临终前为你百般筹谋,托付于我,我自然记得。”欧阳鸣见她承认,言辞却这般晦涩讽刺,心下不快。
免不得想起苏芷如今的名声,有些不愉道:“今日你既然来扫墓,便也算是有几分孝心,当初为何行事那般不济!”说到这里,看荣华如今似乎过得还不错,心中便有些感叹。
“我行事不济?呵,先生是说我与下仆苟且一事?区区一件小事,有何不济之处”荣华笑道,轻轻揭开面纱,露出那如花面容。
傅文景未曾想到那印象中十分不堪的前未婚妻竟然是如此美人,一时间被容颜所慑,回神见她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苟且”二字又这般无所谓的模样,突然生出几分难言的怒气,便道:“住嘴!你……你好不知羞耻!”
“羞耻!?”荣华看向他。
“我为何要羞耻!”
“当初你与我有婚约在身,却不自爱,竟然在父孝期间与下仆作出那等龌蹉之事,竟然不以为耻吗?”傅文景想到此事,便感到屈辱,虽然退了婚约,自己却也是被戴了绿帽子,免不得被人风言风语几句。
想到这里,他不屑道:“真真是个荡\\妇!”
此言一出,赵王府众面面相觑,她们虽然对这位苏夫人的事情略有耳闻,却不想今日直面到当事之人,心下不由有些浮动,思量回到王府该如何给自己的各自的主子汇报此事。
欧阳鸣听得傅文景之言,也是心头腻烦。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你确实是不配此句。苏兄一生清名,皆是毁在你这个不孝女身上。”他不愿意在与此继续于苏芷纠缠,便道:“只是你如今既然已经嫁人,日后便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好一个好自为之啊!”荣华低下头去轻轻一笑,因着苏芷本来面目,显出有几分落寞:“父亲一生清名,却不曾交了个真正的好友。连着自己生前最喜爱的女儿,也因着未找到一个好的托孤之人,害的自己声名狼藉。”
这寺院偏远,树影婆娑,云雾穿梭不定,这树影暗沉之色斜斜印在院墙之上,徒留一团团暗影,只听得这院中女子轻声如碎,在这寂静之所清晰无比。
说到此,她悲痛的高声向着山上喊道:“父亲,你若是泉下有知,可会知道女儿这一生有多么冤屈痛苦!?您将我托付给这些背信弃义,不仁不义之徒的时候,可有想过今日!”
“女儿怨您啊!”
说完,便是泪如雨下。
众人被荣华这突然的一喊吓了一跳,碧秋连着一旁的嬷嬷见状,连忙劝道:“夫人!夫人这是作甚?莫要伤心坏了身子!”
欧阳鸣听得此言回过头来,大怒道:“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荣华素白着一张脸,扯开一抹冷笑,面上依旧是泪水涟涟。
“我说你枉为人师,不仁不义,我说他傅文景背信弃义!怎么?我说错了不成?”
“你若是仁义,怎会置我父亲临终托付于无物?叫我被继母陷害,落得一个水性杨花的名声?你若是仁义,我父生前为我定下的婚事,你怎不让你的徒弟履行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