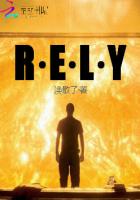潘党一见桓齮落水,顿时大惊失色,可他也是在秦国山川之地长大的秦人,也不通水性,所以即便是焦急万分,却也无济于事,只能在皮筏周围往下四处观望,不住寻找桓齮的身影。蓦地,他猛一抬头,发现正在皮筏之上的戎人梢公,便急忙朝他大喊道:“快快下水救元帅!”
那戎人起先先是一愣,因为他好似并未听懂潘党的呼喊,不过见那潘党双手不住地往水里乱指,仿佛也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只一点头,便扑通一声跳下溪水去了。
皮筏上没有了桓齮和戎人,便只剩下潘党一人,再加上水面上也没了动静,周围又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潘党不住地扒拉着皮筏的周围,四处乱转,以望能看到这落水二人的身影,可是过了半晌许久,依然不见有丝毫动静,顿时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本以为可以借此讨好一下桓齮,图个飞黄腾达,哪想却弄巧成拙,要了桓齮的性命,这如何向秦廷交代?
他正暗自伤神之际,忽然皮筏后侧“哗啦”一声水响,他立刻转头望去,却见水面上浮出两个头影,前面那个是气喘吁吁的,便是戎人的头影,后面那个半耷拉着脑袋,仿佛是昏了过去,不过从装束和轮廓看来,定是桓齮无疑。
潘党一见那戎人救得桓齮起来,顿时惊喜万分,可那戎人贴近皮筏之时,只因桓齮体格较大,戎人很难将他托举上皮筏。于是那戎人便只好搭拉住皮筏边缘,又朝潘党咿咿呀呀一番,一手拉住桓齮,一手连连指了指木桨。潘党虽在慌乱之中,却也一下子明白了戎人的意思,戎人是要他划桨靠岸,自己则拉住桓齮借助皮筏的浮力一起靠岸。
潘党既已明白戎人的意思,却丝毫不敢耽搁,生怕耽搁久了桓齮性命不保,于是便连连抓起木桨,奋力划了起来。说来也奇怪,不知道是不是这潘党生怕桓齮有什么闪失而连累了自己,却是不一会儿,这皮筏便划过了左耳溪,到达了对岸陆地。
到了岸边,那戎人急忙将桓齮翻身过来,双手抱住桓齮腹部,用了向后挤压了几下,只见桓齮咳咳咳嗽了几声,几口积水从口中吐出,随即也便清醒了过来。潘党见桓齮死里逃生,更是喜出望外,正要上来跟桓齮打些招呼,却见戎人又朝他咿咿呀呀了几声,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拱形的弧,随即朝桓齮指了指,又朝弧形中间指了指,示意潘党做些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戎人手势打得好,还是潘党悟性高,这次他又很快会意了过来,这戎人的意思是岸边风大,落水之后容易着凉,便要他搭个帐篷,好将桓齮安置其中,以免受了风寒。 可潘党尽管已经会意戎人的意思,但是之前坐皮筏涉水显然要比徒步涉水要快许多,况且秦兵又多不习水性,涉水过溪自然要慢许多,所以到目前为止,涉水过了左耳溪的人便只有他们三人,要自己徒手搭起一个帐篷却是何等困难。
但困难归困难,此刻保住桓齮的性命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潘党也不由分说,从身上脱下自己的衣服来,示意戎人为桓齮先挡挡风,自己则只穿了件单薄的内衫,去寻树枝树皮这些搭帐篷的材料去了。
待那潘党寻了一圈,取了些树枝回来得时候,却见岸边已经稀稀落落支起了诸多军营来,且军营边上有绣有“秦”字的旌旗,看来桓齮的部众已经顺利渡过了溪流,便就地开始扎营休憩了起来。
潘党一见这情势,心中正待起疑,忽然有一军士瞧见了潘党,便上前向他奏报道:“启禀将军,将士们的军营已经开始驻扎的差不多了,请问将军还有何示下?”
潘党一听此言,不由得勃然大怒道:“混账!是何人教你将大营安扎在此处的?”原来潘党本欲趁着今日渡过溪水,直取九夷城,好打樊於期、司马空一个措手不及,可不想这秦军却就此驻扎在了此地,岂不是白白延误了战机?所以这才恼怒不已道。
“这…”那军士却也不知为何无缘无故受了这一顿怒骂,只是支支吾吾道,“属下方才听闻桓大元帅落水受了风寒,想必是…是元帅下令就此驻扎休憩的吧。”
军士这番话倒是一下子提醒了潘党,桓齮在自己眼前落水自然不会有错,上岸后寒风正紧,兴许也是受了风寒之苦,如此看来,这军令多半就是桓齮下达的,想到此处,他满心的怒气顿时也不得不咽回去许多。可他转念一想,如若此时延误了突袭九夷城的大好时机,那么他们此行不但会功亏一篑,而且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想到这里,他便立即起身朝军营走去,定要找桓齮将此中利害禀报清楚。
潘党刚走到营寨附近,便见其中有一座营堡甚为宽广,显得大气许多,料定那定是元帅的中军大营,于是便加快了步伐走了过去。走进帐门之前,见有门外有两名军士把手门户,上前朝那两个军士随口打了声招呼,便准备直入帐门。
“慢!”他哪里知道,那两位平时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守卫,忽然双手一伸,拦住了自己的去路,这倒让潘党又惊又怒。
“混账,你们两个难道不认识本将军吗?”潘党横眉一竖,低声怒道。、“属下不敢,只是元帅现在受了风寒,正是休憩之时,没有元帅的允许,属下不敢放任何人进去。”那两名守卫朝潘党抱拳施礼道。
“任何人?难道本将军也不可以?”潘党听得这守卫的解释,顿时一阵惊疑。
“正是,元帅是这么吩咐的,请潘将军恕罪。”那两人倒是不依不饶地回了话。
潘党向来都是桓齮的心腹爱将,如今忽然受了这般冷落,自然有些极为不习惯,于是便将一腔怒气朝他二人发作道:“本将军可记住你二人了!”
哪知道话音刚落,忽然听得帐内有侍人问话声音道:“帐外可是潘党潘将军?”
潘党一听里面突然有人问话,心中一惊,急忙用极为恭敬的语气道:“莫将潘党正有要事要向桓元帅通禀,鲁莽之处,还望元帅体谅。”
“潘将军一心为我大秦,其忠心可表日月,元帅自然不会责怪,还请将军进来一叙。”帐内那侍人继续接话道。
潘党一听桓齮有意盛请,心中顿时一喜,连忙躬身施礼应了一声“诺”,随后穿过两位守卫中间,掀开帐幕缓步走了进去。
可潘党自入了营帐中,迎面却只见一扇屏风挡在了眼前,一名侍人站立在侧,见了潘党入内,笑脸相迎道:“潘将军,桓元帅方才落入凉水之中,又受了冷风,身体有些不适,所以这才拿了屏风挡住凉气入侵,以免再受寒风侵袭。”
潘党听罢,哦了一声,以示会意。
“不知将军有何要事要向元帅禀报?”那侍人见潘党会意,又继续接着问话道。
潘党本想将出奇兵突袭九夷城一事亲自向桓齮奏报,现今多了一个侍人在侧,所谓军机不可泄露,所以觉得有些不便,于是便向侍人发话问道:“军机事大,不知元帅可受得此劳累?”言下之意便正是有意要撇开侍人,只向桓齮禀报。
哪知他此话刚出,便听得屏风有人后面“咳咳”咳嗽了几声,随即端坐而起,而后略带沙哑的言语道:“潘将军有话…咳咳,直言便是。”
那人声音虽有些沙哑,但中气十足,确实不乏元帅的威严。潘党透过屏风的薄纱,见得那位从卧榻上端坐而起的身影,正是和桓齮一模一样,于是便急忙施礼答话道:“末将遵命。”礼毕之后,接着缓缓而道:“元帅,我军已经悉数渡过溪流,再往前十里便就是九夷城了,若是要出奇兵以制敌,机会便在此一举,不知元帅是否要下令进军?”
屏风后的桓齮听罢,哦了一声,随即又连连咳嗽着答话道:“咳咳,虽然制敌时机不错,只是…咳咳…”,那桓齮一句话没等说完,便已经连着咳嗽了好几下,似乎看上去伤病不轻。
那身在一侧的侍人见此情景,便插话道:“哦,潘将军,元帅当下身体虚弱,恐怕不宜受行军劳累之苦,若是在两军对垒之时体力不支而倒地,也容易伤了我军士气,我看将军是否可以暂缓一宿,待明日一早元帅元气恢复了些,再行进军不迟。”
潘党听了那侍人此言,虽心中自知多耽搁一日便会多冒九分风险,可是当下之时桓齮确实身体抱恙,如若强行行军,拖垮了这位元帅,自己可是吃罪不起,于是只得唯唯诺诺道:“那…那就依大人之言,暂缓一日,明早再行进军吧。”
“嗯,如此甚好。”侍人见潘党依然应允,便也顺着话接道。
“那如若没什么事情,末将便先行告退了,元帅需好好歇息。”潘党既然已经无功而返,自然也不好再多留,便就此告退道。
“嗯,咳咳…”那屏风后面又发出了几声声响,却不知是答了何话,只听得阵阵咳嗽的声音。
“老奴会好生照看元帅的,潘将军请吧。”那侍人随后也随手一扬,打发了潘党离开。
潘党随意施了一个薄礼,口中只道“有劳了”,便兀自退了下去。
左耳溪是九夷城天然屏障,当地人除了拿它当作保护自己的工具,也是取水饮水的最佳地点。这里的溪水养育了九夷族这么多年,早已成为了九夷族的衣食父母一般。而如今,它连连遭遇了不明身份的外族人士的入侵,这又岂能让九夷族的族人忍耐?潘党桓齮虽懂得行军作战讲究一个神速,但他们却实在是低估了对手的智商。
桓齮的大营傍溪水而驻扎,虽然有利于士卒取水所用,可这毕竟不是阵地后方,而是需要两军争锋相对之地,潘党贪功冒进,或许忽略了这一点,但桓齮也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怎么突然也视若无睹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受了风寒而神志不清了?
军营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潘党自命军士们不准生火,可他倏然不知,黑暗虽然隐藏了自己的行踪,却也隐藏了敌人的行踪。此刻整个军营之外早已有一团团黑影窸窸窣窣地穿梭在了各个岗哨的周围,而此时守卫岗哨的士卒,则因为白日里涉水渡过溪流,已经累的筋疲力尽,早已倒在一旁呼呼大睡了,全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临近。
潘党白日里受了桓齮的命令,就地驻扎在此,但是深更半夜之时,他忽然觉得心中十分不踏实,因为此役原本是他向桓齮提及的,若是不能取得突袭的效果,那便成了孤军深入,必有覆没的危险。他越想越觉得心不安,于是便起了身,披了铠甲,提起狼牙弓和青铜剑,准备出外巡视一番。
哪知道他刚刚出的营门几步,便立刻察觉到了情况不妙,原来这原本在岗哨之上看守的戍卒却空无一人。潘党大惊之余,急忙准备奔回营寨,传令三军提高警惕,忽然只觉头顶“嗖嗖嗖”一阵阴风划过,便见数百道流星一般的箭雨落入了自己的大营之中。那箭头之上因个个燃有棉油,所以划空而过之时,便如同流星坠地一般。
数百道火箭从各个方向齐刷刷一齐射来,落入营帐的顶棚周围,瞬间都引燃了营帐的幕布。而此时的秦兵却大半都因白天涉水太过疲乏而沉睡在睡梦中,对这突如其来的噩梦浑然不觉。
潘党此刻已经料到大事不妙,立刻抄起手中的狼牙神弓,拉弓搭箭,朝悬挂于营门一侧的金锣射去。这金锣原是两军对战之时鸣金收兵之用,如今潘党为了尽快散播军情,不得已而用了此法。箭到金锣之处,忽然又有一道疾风飞过,却不偏不倚正好将潘党的狼牙箭给半道截了开来,箭矢未中金锣,只偏向一旁,钉在了木桩子上。
这一声响动虽被人给打断,可毕竟还是发出了“噔”的一声,总算将几个正准备轮夜的守卒给惊动了。这些守卒一看,营帐周围火光冲天,顿时大惊失色,急忙拉开嗓门大声嚷嚷起来:“有敌军偷袭!有敌军偷袭!”
守卒的这几阵呼喊声,率先惊动的不是睡梦中的秦兵,而是隐藏在周围的戎族人和樊於期的上庸军。这些人听闻敌军已然引起了警觉,便呼喝了一声,如同幽狼一般冲向了秦兵大营。这一下子的呼喝,倒是惊醒了不少睡梦中的士卒,可是慌乱之中也是不知所措,不待整装,只穿了内衣先跑出营帐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