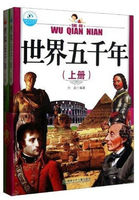不觉之间,渡船行到江心,真宝却一惊一乍跳起来:“阿唷,船家,我和尚忘了物件在岸上,快转头回去!”
见识了和尚的骇人功夫,船老大敢不从命,指挥船工欲返航。
渡客们不由嗡嗡一片,十八铜卫亦忿忿然望向沙都卫,显是欲教训这不讲理的和尚,沙都卫摇摇头,示意不可生事。
偏有人不服,一庄稼汉挺身而出,正是君不见伯仲的老二:“咄!你这和尚好不晓事,岂有船行一半又掉头的道理,又不是你家开的!要想回,也须到了对岸,放我等下去,再回不迟!”
众人皆觉这和尚不通情理,见有人出头,纷纷附和。
真宝大怒:“我和尚要回,船家也无意见,尔等生何事端?”
庄稼汉也是火爆脾气,亮出手中锄头:“出家人与人方便,与世无争,我看你这秃驴不是正经来路,偏不让你!”
出家人最恨被人骂做秃驴,真宝哇哇直叫,抖起禅杖:“大粪秧子,我和尚要教训你!”
明日正在冲穴的要紧关头,亦受到干扰,脑中滑过一个意识:他俩分明在演戏,倒与智取生辰纲的手段相近,现在也是动手的好时机……
一言不合,二位已交上手来,周围的渡客惟恐殃及池鱼,纷纷避往高益恭一行所在的方向,其余五侠亦夹在人群中接近。
正点子来了!明日心神一分,冲穴失败,瞧见十八铜卫一副看热闹的模样,肚中那个急啊,苦于不能发声警戒。
庄稼汉自不是和尚对手,倒拖着锄头便跑,跑到桅下大嚷:“老子偏不让秃驴得意!”
庄稼汉说了便做,亦无道理地一锄头刨断扯帆缆绳,“哗啦啦”,缆绳断开,帆布应声而落。
渡客们皆抱头惊呼,这下渡船在江心打转,哪边也靠不了,船家吓得躲到一旁。
高益恭眉头一皱,此时方觉不对,忙与沙都卫耳语几句,沙都卫亦神色一紧,正待说话,却已迟了一步,呼哨顿响,眼前人影闪动,五侠自人群中暴起,齐齐发难!
正是有心算无心,一个照面间,十八铜卫被撂倒一半,事起突然,可大内侍卫也不是吃干饭的,不等沙都卫发令,尚余的铜卫抽出随身兵器,与对手斗将起来。
和尚与庄稼汉也不作戏了,转身加入战团。
渡客们方明白和尚与庄稼汉是一伙的,再看高益恭一行是行商打扮,皆以为是打劫,皆暗叫一声苦,怎地江面上碰到了强人?
几个军卒看双方都不好惹,亦不敢妄动。
对方来势凶猛,沙都卫发出指令:“都不要散开,保护高兄!”
高益恭更是情急:“保护贱内更要紧!”
敢情,真宝与六侠的压力都集中在高益恭身上,对明日这个“病妇”看都不看一眼。
明日生出侥幸——最好不是冲自己来的,心上这般想,一双眼睛却甚为关切地注视着“夫君”高益恭,大半出于关切自身。
渡船摇晃不停,君不见七侠出自江南武林,水上功夫当然不弱。
而高益恭与十八铜卫皆是北人,武艺大打折扣,被对方不慌不忙地收缩包围圈,自然认准此点,水遁也不怕。
渡客们战战兢兢,或伏或蹲,只求刀剑长眼,不要落在自己身上。
几个回合下来,铜卫们又倒下几个,数量上也处于劣势。
沙都卫一根生铁棍抡得呼呼响,高益恭朴刀舞得水泄不通,虽也是高手,但对上更高的真宝与君不见七侠,只赖对方不下杀手,才勉强支撑,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沙都卫一棍逼开众人:“且慢,我有话说!”
真宝与六侠交换眼色,停手罢斗。
沙都卫喘口气,无奈亮出御制金牌:“实不相瞒,我等乃大内官差,乔装执行朝廷密务,若误了国事,只怕你们当罪不起!赶快罢手,便不追究。”
真宝一吹胡须:“找的便是尔等,执行甚么密务,只恐是卖国密务吧,交出向鞑子的求和书,留下议和物货,便放过尔等!”
高益恭与沙都卫大惊失色,须知这任务乃赵构亲派,朝廷上下知情者不出一、二人,连左相吕颐浩都瞒过,怎地流传到江湖中,如此看被人盯上已久,只是对方一直在找时机下手。
可不是,如果在岸上,他们自可寻官兵相救,惟有在江舟之上,才插翅难飞!
君不见翁一抖破剑,转向满船百姓,徐徐接道:“枉那朝廷,亏我义士男儿铁血抗金,如今形势稍好,便不思进取。这和议书乃奸相秦桧所拟,赵官家瞎了眼,信任这奸贼为相,初时尚沽名钓誉,蒙蔽一时,入相后竟提出甚么‘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亡我大宋之策,真真狼子野心,天下人恨不能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这和议书欲尽弃河朔之地,赵官家应承,我大宋百姓应承么?”
君不见翁竟连和议书的内容都晓得,这个密可泄大了,一定是赵构身边的正直官宦所为!
明日这才确信真宝与六侠的目标不是自己。
渡客们也听出大概,原来这些人乃抗金义士,不甘朝廷向金人割地求和,才冒死阻拦,一时义愤填膺:“这些狗官差,竟要出卖祖宗土地,将他们扔下江喂鱼!”
十八铜卫个个有如大梦初醒,满面羞愧。
沙都卫则为之一颤,望向高益恭,他只知要运送一批物资与挞懒,履行淮南撤军之协议,素来大宋以财物换和平,对辽、夏、金莫不如此,虽是上命不可违背,倒能接受。
却没想到还有和议书一事,沙都卫联想起一路来的神秘鬼祟,和赵官家的特别指示,虽奇怪对方怎晓得这绝顶机密大事,料也不应有假,毕竟其跟了赵构这么久,对这位皇帝的禀性还是了解的。
在这等大是大非面前,沙都卫面色灰败,犹豫半晌,终于放下棍,长叹一声:“高兄,沙某已经尽职了!”
“施主迷途知返,阿弥陀佛!”真宝合掌道贺,双目精芒大盛,瞪住高益恭,“你便是随奸相南归的燕人高益恭么,你也是汉人,为何为鞑子卖命?乖乖交出和议书,饶你不死!”
高益恭毅然举刀:“某所在燕地,从不受大宋衣食,甚么祖宗之地,守不住也是枉然,我奉令行事,书在人在,书亡人亡!某只有一个请求,各位不要为难贱内,能否将她送回燕地?”
明日大为感动,心知高益恭宁愿战死也不辱命,还要保全他的性命。
因为一旦明日的身份暴露,一定不会活着离开这条船,残杀君不见君与义军的罪名足够他死一百次了。
“好汉子,我和尚成全你!”真宝亦赞一声,宽大的僧袍飘飘欲起,下了一击必杀的决心。
“贼秃做梦!”蓦地一声冷笑,渡客中缓缓步出一个书生。
甚么人如此大胆?真宝一愕侧首,杀气顿受牵引而弱,六侠亦好奇转向来者。
此人头戴方巾,身着蓝袍,体形单薄,表情木漠,约莫二十来岁——正是那不时注视明日的书呆子。
明日心道:“兄台,你想英雄救美么?也不掂量自己,果然是个书呆子……”
蓝袍书生翩翩而来,距离这边本有十多步远,不知使了甚么身法,已挡在高益恭身前,好轻功!
看不出是个会家子,明日大跌眼镜,当然,这时代是没有眼镜的。
真宝亦现出诧异之色,沉声问:“阁下是何来路,要为金奴出头么?”
蓝袍书生负手而立,并不应答,背在身后的双手做个奇异手势,这角度只有高益恭可以看到,还有……明日。
本一副视死如归的高益恭一见这手势,当真又惊又喜,不理大敌当前,恭恭敬敬地单膝跪倒,行个大礼,便撤刀退到他跟前,好像跟眼前之事无关了。
君不见伯仲见状嚷道:“这两个鸟男女是一伙的,大师莫手软!”
蓝袍书生竟是高益恭的接应者,怪道对自己留意,但那奇异手势令明日满头雾水,要说是金人的联络暗记,他在金营那么久,怎会没见过。
这书生是何身份,当得高益恭如此大礼?
“阁下既藏头掩尾,我和尚就不客气了!”真宝直来直去,左手持杖,右手一指戳去,暗留几分余力,不欲取对方性命,毕竟其身份不明。
蓝袍书生只微一晃身,明明人在原处,真宝这一指竟戳个空!
一时六侠皆色变,个个自度虽能应付这指,但如此不着痕迹万万做不到。
渡客们却看不出来,纷纷催促:“大和尚莫要慈悲,拿了这酸丁!”
蓝袍书生依旧负手,眼睛并不看他人,掠向江面,隐隐一代宗师。
正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真宝面色凝重:“六位兄弟请退后。”
君不见翁会意真宝要倾全力,这种顶尖高手之争,帮手反而碍事。
一则深信真宝身手,二则若有意外,六侠再接应不迟,对付金贼,自不须讲甚么江湖道义……怀着这心思,君不见翁挥手,六侠齐退。
明日也想不到这书呆子身怀绝技,难怪高益恭对其放心。
渡客们方有些猜到来者不善,忙不迭往外移动,空出一块阔地。
只闻真宝大喝一声,双臂一挥禅杖,照蓝袍书生当头击下,再不留余力,隐隐伴随雷霆破空之声,正是佛家降魔的“当头一棒”!
蓝袍书生微微颔首,下身依旧不动,双手伸将出来,轻飘飘画了一个圈,长袖一带,真宝的禅杖偏过去,似被磁场的斥力牵引一般,往船板落下,眼看穿个大洞。
“嘿!”真宝吼一声,于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掉杖尾回敲,似拙实巧,扫向书生下盘,这个变式由强击转成软打,极高难的一个转换,真宝收发自如的内力可见一斑。
六侠不由喝彩,皆以为蓝袍书生必狼狈而退,真宝这一敲可顺势攻向高益恭,不愧“横扫千军”!
那蓝袍书生脆哼一声,双臂一张,立起脚尖,有如后世天鹅舞般地旋转个三百六十度,衣袂如水,煞是好看。
六侠眼一花,见其仍在原地,而禅杖已经扫个空,喝彩变成不信:不可能!
自两人交手后一直目不转睛的明日,亦是满心震撼!
今非昔比的他,目力变得敏锐之极:刚才,禅杖即将扫到蓝袍书生的双腿时,其利用身体的旋转,跳皮筋般地双脚交替点起,刹那叉过禅杖,因此看起来好像原地未动,如此而已。
然而,这一切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有一点差池,代价将是腿折骨断,只能证明蓝袍书生艺高胆大。
以真宝的功夫,两招无法逼退对手,这个对手未免太可怕了,这厮是?一个恐怖的影子滑过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