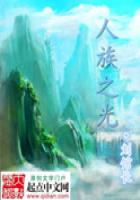我度过了一个寂静的冬夜,醒来时依稀记得,仿佛有人向我提问,比方说,什么啦——怎么啦——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睡梦中我很想一一回答,结果还是徒劳。但是,黎明时分,万物须臾不可离的大自然,脸呈宁静、满意的神情,直望着我那宽大的窗子,她的唇边倒是看不出在提问。我意识到了那道答题,意识到了大自然和天光大亮。大雪深深地覆盖着幼松点染的大地,我的小屋所在的小山坡,似乎在说:前进吧!大自然并没有提问,对我们凡夫俗子的提问一概不予回答。她老早就下过决心了。“啊,王子,我们两眼欣羡地在凝思默想,将这宇宙间奇妙多变的景象传达给灵魂。毫无疑问,黑夜掩盖了这光辉的创造的一部分;然而,白昼来了,给我们显示了这一杰作,从大地一直延伸到浩茫的苍穹。”
然后,该是我早上忙活儿去了。首先,我拿了一把斧头和提桶,外出找水去,但愿不是在做梦吧。度过一个寒冷的雪夜以后,找水还真少不得有一根占卜杖才好。平日里湖面水波荡漾,对一丝微风都很敏感,常常映现出闪光和倒影;但一到每年冬天,湖里冰凌结得很坚实,深达一英尺或者一英尺半,就算是最沉重的马车都能承受得住;也许大雪覆盖得跟冰凌一般深,你很难识别是在湖上还是在平地上。像周围群山中的土拨鼠,它闭着眼进入冬眠,可以长达三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上。站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好似在群山中的一块草场,我先要穿过一英尺深的雪地,接下来是一英尺厚的冰凌,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口,跪了下来喝水,俯瞰水下鱼儿们宁静的厅堂,那儿充满了柔和的亮光,好像透过一块磨砂玻璃窗照进去的,亮闪闪的细沙湖底跟夏天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里,常年水波不兴,始终是一片静谧,就像黄昏时琥珀色的天空,这倒是跟水中居民的冷静而又和顺的气质息息相通。天空在我们的脚下,也在我们的头上。
大清早,经过霜冻后天气显得格外寒冷,人们带上钓竿和午餐便当,把钓线甩到了雪地下面去钓狗鱼和鲈鱼;这一拨野腔野气的人,看来不像是他们的城里人,他们本能地采用别的生活方式,相信别的权威,他们就这么着来来去去,把好多城市部分地缝合在一起,要不然,这些城市相互之间还是不搭界的。他们穿着厚实的粗绒大衣,坐在湖边干枯的橡树叶上吃午餐,他们一说到自然知识总是头头是道,就像城里人会矫揉造作一样聪明。他们从来不求教书本,他们的动手能力大大地超过他们所掌握的并可传授的知识。他们做过的好多事,据说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这儿就有一位,常用大鲈鱼做诱饵去钓狗鱼。你看着他的木桶好不奇怪,就像看到了夏日里的湖,仿佛他把夏天锁好藏在自己的家里了,或者说他知道夏天已躲藏到哪儿去了。请问,隆冬季节,他怎么会逮到这么多的鱼呢?哦,地上到处冻了冰,但他从烂木头里寻摸到虫子,所以,他管****得到那么多鱼。他的生活原本就是在大自然里度过的,比博物学家的研究还要深入得多;他本人就是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博物学家轻轻地用刀子揭去苔藓和树皮,从里头寻找虫子;可他只消一斧头下去,就劈开树芯,但见苔藓和树皮一下子飞得老远老远。他就靠剥树皮为生。这样的人就有权钓鱼,我很喜欢看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显灵呢。鲈鱼吃蛴螬,狗鱼吃鲈鱼,渔夫吃狗鱼;生物等级中所有空隙就是这么着给填满的。
雾沉沉的天气里,我沿湖溜达,有时看到一些比较粗犷的渔夫所采用的原始方式,我觉得倒是挺有趣。冰凌上有好多个小窟窿,各自相距四五杆远,离湖岸也有那么远吧,也许他就把一些桤树枝搁在小窟窿上面,把钓线的一头拴在一根树枝上,以免被拉下水去,再在冰凌一英尺多远处,将松散的钓线挂在桤木的一根树枝上,上面系一片干枯的橡树叶子,只要这钓线被拽了下去,就说明鱼已上钩了。这些桤木树枝在迷雾中时隐时现,间距相等,你沿湖溜达,走过一半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了。
啊,瓦尔登湖的狗鱼!我看见它们躺在冰凌上时,或者,我从渔夫在冰凌上开凿小小的一眼井里看它们的稀世之美,常常使我惊异不已,仿佛它们是寓言里的神秘之鱼,在市街上,乃至于树林子里都是见不着的,而且在我们康科德的生活中,也像见不着阿拉伯半岛一模一样。它们具有一种亮丽夺目、超凡脱俗的美,这种美使它们与灰白色的鳕鱼和黑鳕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可后两种鱼在我们市街上却是响当当的。它们没有松树那么绿,也没有岩石那么灰,更没有苍穹那么蓝,依我看,它们的色彩,很可能是举世无双,像花朵,像宝石,它们俨然珍珠,是瓦尔登湖水中生物凝结的晶核或者水晶。不消说,它们是地地道道的瓦尔登湖;在这个动物王国中,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小小瓦尔登,好一个瓦尔登派。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却在这儿被人逮住——这种金翠色大鱼原本畅游于泱泱深水之中,远离瓦尔登大路上辚辚声响的驮畜、轻便马车和铃儿叮当响的雪橇。这种鱼我在市场上从来没见到过;如果上市的话,它管保吸引住人们的眼球。它们只消身子痉挛似的扭动几下子,立时抖掉它们湿漉漉的鬼相,就像一个凡夫俗子,虽然时限未到,却已进入了天堂。
那消失已久的瓦尔登湖的湖底,我真恨不得它早点恢复,所以,在1846年初,趁湖里冰凌还没融化之前,我就带上罗盘、测链以及测深绳,对它仔细地进行了勘探。至于这个湖到底有没有湖底,历来传说纷纭,当然也都是一些无稽之谈罢了。令人蹊跷的是,人们自己既没有测量过湖底,却长期以来相信它是无底之湖。我在这儿附近一次散步中就曾经到过两个所谓的“无底之湖”。许多人相信,瓦尔登湖一直通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有的人趴在冰凌上老半天,透过那梦幻似的媒介物向下俯视,也许还看得眼里水波荡漾,又因害怕胸部着凉,就急吼吼地下了结论,说他们确实看见了许许多多巨大的窟窿,“里头可以填塞大量干草”,如果真的有人下去填塞的话;这儿无疑就是冥河的源泉,地狱的入口。还有一些人,从村子里拉来一个标重“五十六磅”的铁疙瘩和满满一车子绳索,可他们并没有探测到湖底;因为他们把这个“五十六磅”的铁疙瘩搁在一边,将绳索慢慢地全给放下水里去,结果还是徒劳,怎么也都够不着这神奇的深不可测的湖底。我可以确切地告诉我的读者,瓦尔登湖有一个紧密得合乎常理的湖底;湖的深度虽然深得非同寻常,但也并非不合常理。我只消用一根钓鳕鱼线,线头上拴一块一磅半重的石头,扔到湖水中,很容易就能测出它的深度,因为石头落到湖底后缺乏浮力,再往上提要费更大劲儿,所以,石头什么时候离开湖底,我管保说得十分精确。湖的最深处,正好是一百零二英尺;也许还得加上后来上涨的湖水五英尺,总共是一百零七英尺。水域如此逼窄,却有这样的深度,确实相当可观,但是,光凭想象力,你也断断乎不能再减去它的一英寸。如果说所有的湖都很浅,那又会怎么着?这不会在人们心灵上产生影响吗?我真心感谢瓦尔登湖,这么深,这么纯洁,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既然有人相信无限,就必定有人相信有些湖是无底的。
有一个工厂主听说我测出了湖的深度,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根据他所熟稔的堤坝来判断,湖底细沙没法堆积在如此陡峭的坡度上。但是,即使是最深的湖,跟它们的水域相比,也没有大多数人所想象那么深,而且,要是把湖水排干,再来看一看,也断断乎不会成为深不可测的谷地。它们不像群山之间的杯状物;而瓦尔登湖从它的面积来说,确实深得出奇,但从湖中心的垂直剖面来看,也不过像一只浅盘子那么深。大多数湖泊,排干了水,就呈现出一片草地,并不比我常常见到的那么低洼。威廉·吉尔平在描写景色时既令人赞叹,而又十分准确,站在苏格兰法恩湖湾的岬角上,他是这么描述的:“一个咸水湾,六七十英寻深,四英里宽”,大约五十英里长,群山环抱;他又评论说,“如果说我们能在洪水泛滥之前,或者在受到天灾之前,或者在大水鲸吞之前就看到了它,那么,它定然是一个非常骇人的缺口啊!
高高隆起的群山啊!
谷底却又那么低,
庞大的河床,宽阔而又深沉”。
我们已经看到,从垂直剖面来看,瓦尔登湖只是一个浅盘子,可是,如果我们拿法恩湖湾的最短一条直径,按照相应比例来估算瓦尔登湖,那么,看来瓦尔登湖还要浅四倍呢。法恩湖要是湖水排干,它的缺口所增加的骇人程度,原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毫无疑问,许多山谷好像笑吟吟似的,一直伸展到玉米地里,正好成为大水退去之后这么一个“骇人的缺口”,虽然这还得要有地质学家的远见和洞察力,才能使那些没有料想到的居民相信这一事实。凡是特别好奇的眼睛,在地平线的小山上,常常可以发现一条原始湖的堤岸,平原后来就算升高了,也没有必要去掩盖它们的来历。但是,经常在公路上干活的人都知道,大雨过后看一看哪儿有泥水,就最容易发现低洼地了。这意味着,只要允许,想象力稍微放纵一下,就要比大自然下潜得更深,升起得更高。因此,人们会发现,海洋的深度若跟它的面积相比,也许是浅得微不足道了。
我已通过冰层测量过瓦尔登湖水的深度,现在我就可以确定湖底的形状,这比测量没有冻冰的港湾,可能还要准确得多,总的说来,湖底齐整匀称,使我惊讶不已。湖底最深处有好几英亩地都是一溜儿平整,几乎胜过所有风吹日晒、被犁过的耕地。举个实例来说,我随便挑选了一道线,在三十杆以内,深浅不同程度不超过一英尺;一般说来,毗邻湖心一带,不管向哪个方向移动,我都可以预先算出,每一百英尺的变化,在三四英寸以内。有人常说,哪怕是像这样平静的细沙湖底还有好多又深邃又危险的窟窿,但是如有这种情况,湖水早已把湖底的坑坑洼洼通通给端平了。湖底齐整匀称,与湖岸以及毗邻山脉保持着一致性,真是如此完美,即便在湖对岸,照样能测量遥远的岬角,而且只要观察一下对岸,也可以确定它的走向。岬角成了沙洲和浅滩,溪谷和山峡成了深水和峡湾。
我按照十杆比一英寸的比例,绘制了一幅湖的全图,在一百多处标明它的深度,我发现了这一惊人的一致性。注意到标明湖水最深处的地方显然位于这幅全图的中心,我用一根尺子在全图最长的地方竖着画了一道线,又在最宽的地方横着画了一道线,我吃惊地发现,这两道线恰好在湖水最深处相交了,尽管湖中心几乎是平坦的,但湖的轮廓远不是齐整匀称,最长的线和最宽的线是通过测量湖湾才得出来的。我自言自语道,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暗示海洋的最深处与湖泊或者水塘的情况如出一辙呢?这一规则是不是也适用于高山,把高山与山谷看成相对的?我们知道,一座山在它的最狭处,不见得就是它的最高点。
五个湖湾里头有三个,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湖湾我全测量过,它们的出口处都有一个沙洲,里头湖水比较深,看来这沙洲的走向不仅向内陆扩大水域,而且还向深处扩大水域,形成了一个盆地或者独立的湖,两个岬角的走向正好表明了沙洲的这一进程。每一个海港的入口处,也都有一个沙洲。湖湾的入口处,宽度大于长度,沙洲里头水也要比盆地里头水更深些。既然已经洞悉湖湾的长度和宽度、周围湖岸的特性,你几乎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列出一个公式来,对所有情况均可适用。
根据这次经验,我就在湖水的最深处观察它的平面轮廓和湖岸的特性,查看一下我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何;我还绘制了一幅白湖的平面图。白湖占地面积约有四十一英亩,跟瓦尔登湖一样,湖中没有岛屿,也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入水口或者出水口。由于最宽的线和最窄的线挨得非常近,就在这里,两个遥遥相望的岬角也越来越近,而两个相对的沙洲相距越来越远;我在最窄的线上标上一个点,但仍然落在与最长的线的交点上,作为湖水最深处的标志。果然发现这最深处离这个点不到一百英尺,比我原定的方向再远一点,深度只有一英尺,换句话说,是六十英尺深。当然,如果说有一道溪涧流过,或者说,湖中有一个岛屿,问题就会更加错综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