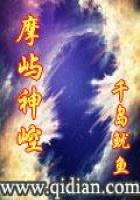要是我可以相信自己对日期不太准确的记忆的话,那一定是在我结婚后一年左右。一天晚上,我独自散步回来,一路上思索着当时我正在写的一本书——由于我孜孜不懈的努力,我的成就也在不断地增加,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斯蒂福思太太的住宅。在我住在那附近时,我经常经过那座宅子,虽然可以选别的路时,我就决不从那儿过。可是有时候,不绕个大圈子,要想找到另一条路,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总体说来,我从那儿经过的次数,还是相当多的。
每逢从那座宅子前经过时,我总是加快脚步,从不朝它多看一眼。这座宅子一年到头都是阴沉沉的。最好的房间没有一间临近路边;它那种窗身狭窄、窗框厚笨的老式窗户,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敞亮,现在窗门都关得紧紧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更显得冷落凄凉。宅内有一条走廊,穿过铺石的小院,通向一个从来不用的入口;楼梯侧面的墙上有一个圆形小窗,它与众不同,是唯一没有用窗帘遮着的,但也同样给人以荒废、无人之感。我不记得整座宅子什么时候有过灯光。要是我是个偶然经过的路人,大概会想,一个无儿无女的人死在里面了。要是我对这地方有幸一无所知,而又时常看到它那一成不变的样子,我敢说,我一定会想入非非,尽量来满足我的想象力了。
由于知道实情,所以我就尽量少去想它。可是,我的思想没法像身体那样,经过之后就把它撂在后面了,往往会引起一长串默想。特别是在我说到的那个晚上,它让我想起童年的桩桩事情和后来的种种梦想,半未成形的希望的幽灵,朦胧可见的失望的残影;加上当时我想的是工作,与此有关的经验和想象,混合为一体,因而它引起我的联想,大大超过平时。我一面走,一面都想得出神了;突然,我身边的一个声音,使我吃了一惊。
喊我的还是个女人。不消多久,我就想起这是斯蒂福思母亲家的客厅小女仆。以前她帽子上总是扎着蓝色缎带,现在已经拆掉,换成一两个暗淡素净的褐色花结;我猜想,这是为了适应那一家变化了的景况吧。
“对不起,先生,能请你进来跟达特尔小姐谈谈吗?”
“是达特尔小姐打发你来叫我的吗?”我问道。
“今天晚上没打发我叫,先生,不过反正也是一回事。前一两个晚上,达特尔小姐看到你打这儿经过,就叫我坐在楼梯上干活,要是看到你又打这儿经过,就请你进来,跟她谈谈。”
我转身往回走。当我们一起走着时,我顺便问我的领路人,斯蒂福思太太可好。她说,她家老太太不太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里。
我们来到那座住宅后,女仆告诉我,达特尔小姐在花园里,要我自己去见她,让她知道我来了。她正坐在露台一头的一个座位上,这儿可以俯视全城。这是个阴沉沉的夜晚,天空露出死灰色的亮光;看到远处那森然的景色中,一些高大的景物星星点点地在阴沉的光线中矗立,我心里想,这景色跟我记忆中这位凶悍的女人相伴,倒是不能说不匹配哩。
她看到我朝她走去,起身站了站,算是迎接我。当时我想,她比我上次见到时脸色更苍白了,身子更瘦削了,闪烁的眼睛更发亮了,那个伤疤也更明显了。
我们的见面,丝毫没有热情。上次我们是不欢而散的;现在她的脸上还有着不屑的神情,而且一点也不想加以掩饰。
“达特尔小姐,听说你想跟我谈谈,”我手扶椅背,站在她跟前说道,谢绝了她示意要我坐下的邀请。
“对不起,”她说道,“请问,那个女孩找到了吗?”
“没有。”
“可她已经逃走了!”
当她看着我时,我看到她那两片薄嘴唇在动,好像急于要把咒骂加在艾米莉身上似的。
“逃走了?”我重复了一句。
“是的!从他身边,”她冷笑着说,“要是这会儿还没找到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了。她可能已经死了!”
我朝她看时,她那副得意洋洋的残忍表情,我从来不曾在别的人脸上看到过。
“巴望她死掉,”我说,“也许是一个跟她同属女性的人,对她所能表现的最大慈悲了。达特尔小姐,时光使你变得温和了这么多,我真高兴。”
她没有屈尊给我回答,而只是冲着我轻蔑地一笑,说:
“这位出色的受害年轻女士所有的朋友,都是你的朋友。你是他们的捍卫者,全力维护他们的权利。你可想知道有关她的情况?”
“想。”我说。
她面带令人厌恶的笑容,站起身来,朝不远处一道把草坪和菜园隔开的冬青围篱走了几步,然后提高声音喊道:“过来!”——好像在叫一头不洁净的畜生。
“你在这儿当然会捺住性子,不会露出捍卫者的身份和报仇的念头吧,科波菲尔先生?”她回过头来,脸上依然带着同样的表情,冲着我说。
我低了低头,不懂她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她又喊了一声,“过来!”在她回来时,后面跟着那位体面的利提摩先生。这位先生的体面不减当年,他向我鞠了一个躬,随即在达特尔小姐身后站定。达特尔小姐靠坐在我们中间的一张椅子上,注视着我,样子那么恶毒,神气那么得意,但是说也奇怪,其中依然不乏某种女性的动人魅力,真抵得上传说中那位残忍的公主。
“现在,”她没有看他,只是摸着她那似乎在颤抖的旧伤痕——也许这次她感到的是快意,而不是疼痛——神气活现地说,“把逃走的事告诉科波菲尔先生。”
“詹姆斯先生和我,小姐——”
“别对着我说!”达特尔小姐眉头一皱,打断了他的话。
“詹姆斯和我,先生——”
“请你别对着我说。”我说。
利提摩先生一点也没有心慌意乱,只是微微地鞠了一个躬,意思是说,凡是我们感到最满意的,他也就最满意;他就又重新说:
“詹姆斯先生和我,自从那个年轻女人在詹姆斯先生保护下,离开亚茅斯后,就带着她一起去了外国。我们到过许多地方,去过不少国家。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实际上,几乎是所有地方。”
他望着椅背,像是冲着它说话似的,两手还轻轻地抚弄着椅背,好像在弹一架无声钢琴的琴键。
“詹姆斯先生非常喜欢那个年轻女人,打从我为他当差起,很久以来,我从没见他的心情这般安定过。那个年轻女人很堪造就,她学会了说好几种外国语,谁也看不出她就是以前的那个乡下人了。我注意到,不论到哪儿,她都受到大家的称赞。”
达特尔小姐一只手撑在腰上。我看见利提摩偷偷地朝她瞥了一眼,暗中微微一笑。
“那个年轻女人,的确到处都受到大家称赞。由于有漂亮的穿着,由于有美好的空气和阳光,又有大家捧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她的长处也就真的引得大家注意了。”
说到这儿,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这时,达特尔小姐的眼睛,烦躁不安地在远处的景象上乱转,牙齿咬着下嘴唇,不让那张嘴乱颤乱动。
利提摩把双手从椅背上放下,把其中的一只握在另一只里;他把自己的全身都稳支在一条腿上,两眼下视,体面的脑袋略微前俯,有点歪向一边,接着说道:
“那个年轻的女人就这样过了一阵子,只是偶尔有点无精打采。后来,她总是那么无精打采,而且老爱发脾气,我想,这样一来,就惹得詹姆斯先生对她厌烦了。大家就都不愉快了。詹姆斯先生又开始心神不安定起来。他越不安定,她也就越糟糕。我得说,自己夹在他们两人之间,日子确实很不好过。不过情况还是得到了弥补,这儿修修,那儿补补,一次又一次的修补,总算还维持着;我敢说,谁也没有料到能维持得那么久。”
达特尔小姐把目光从远处收回,又用先前的神情看着我。利提摩先生用手掩住嘴,体面地轻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换一条腿支着,然后接着说:
“到后来,总而言之,他们话也多了,指责也多了。于是,一天早上,詹姆斯先生离开我们住的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因为那个年轻女人很喜欢海),顾自走了。詹姆斯先生离开时,假装说一两天就回来,可暗地里交代我,要我到时候对她捅明,为了各方面的幸福,他这一去,”——说到这儿,他又短促地咳了一声——“不再回来了。不过,我得说,詹姆斯先生的为人,确实是十分光明磊落的;因为他出了个主意,要这个年轻女人嫁给一个很体面的男人,那个男人表示对她过去的事,可以完全不作计较;而且,他至少比得上那年轻女人通常能不能高攀得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她的出身非常低下呀。”
他又把腿换了一下,润了润嘴唇。我深信不疑,这个坏蛋说的体面男人,就是他自己,我从达特尔小姐的脸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话也是詹姆斯先生交代我说的。只要能让詹姆斯先生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不管什么事,我都愿意去做。再说,老太太那么疼他,为他受了那么多苦,为了能使他们母子俩和好如初,我也应该这么做。因此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我把詹姆斯先生一去不回的消息,对那个年轻女人捅明时,她一下就昏过去了。待她醒过来后,她那股泼辣劲,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她完全疯了,非用强力把她制止住不可。要不,即便她弄不到一把刀子,或者到不了海边,她也会拿自己的脑袋拼命在大理石地板上撞个不停。”
达特尔小姐后背往椅子上一靠,脸上现出一片得意之色,好像差一点要把这家伙说的一字一句,全都爱抚一番。
“可是当我把交代我办的第二件事捅明后,”利提摩先生不自在地搓着双手,说,“那个年轻女人不但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番好意,应该表示感激,而是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像她这样蛮横、凶暴的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她的行为真是坏得吓人。她就跟一段木头或者一块石头一样,没有感情,没有耐心,不懂感激,不懂道理。要不是我有所防备,我相信,她非要了我这条命不可。”
“凭这一点,我倒更敬重她呢。”我愤怒地说。
利提摩先生只是低了低头,好像在说,“是吗,先生?不过你还嫩着哩!”跟着又说了下去。
“简单地说吧,有一阵子,凡是她能用来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的东西,都得从她身上拿开。还得把她紧紧地关在屋子里。尽管这样,一天夜里,还是让她给跑掉了。有一扇窗户,是我亲手钉死的,可她使劲把窗格给弄开了,顺着蔓生在墙上的藤萝,攀滑到地上。打那以后,据我所知,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的踪影,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她也许死了。”达特尔小姐笑着说,仿佛她可以朝那受害姑娘的尸体,踩上一脚似的。
“她也许投海自杀了,小姐,”利提摩回答说,这回他抓住对一个人说话的借口了,“很有可能。要不,她会得到那些船夫,或者是船夫的老婆孩子帮忙的。她喜欢跟下等人在一起,在海滩上,坐在他们的船旁跟他们聊天,达特尔小姐,她已经非常习惯。詹姆斯先生外出时,我曾看见她成天跟他们在一起混。她告诉那些小孩子说,她也是渔家女,许久以前,在她自己的国家,也像他们一样,在海滩上跑来跑去玩耍。这事有一次让詹姆斯先生知道后,惹得他很不高兴。”
哦,艾米莉!你这苦命的美人啊!我眼前不觉出现了一幅画面,只见她坐在远方的海滩上,坐在一群跟她当年天真烂漫时一样的孩子中间,一面听着他们细小的声音——要是她做了穷人的妻子,会叫她妈妈那种细小的声音——一面听着大海的呼啸,总是喊着“永远不再!”
“当事情已经很清楚,什么办法也没有时,达特尔小姐——”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你不要对着我说吗?”达特尔小姐声色俱厉,颇为不屑地说。
“对不起,小姐,刚才是你对着我说了,”他回答说,“不过服从是我的职责。”
“尽你的职吧,”她答道,“把这件事说完,就走!”
“当事情已经很清楚,”他鞠了一个躬,表示服从,然后体面十足地接着说,“她是再也找不到了,我就去了詹姆斯先生跟我约定的那个通信的地方,见了詹姆斯先生,向他报告了发生的事情。结果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我觉得,为了维护我的人格,我不得不离开他。我本可以受詹姆斯先生的气,一直以来受得够多了,可是这一次,他把我侮辱得太过分了,伤了我的心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母子之间不幸有了分歧,也知道她心里十分焦虑,于是我就大胆地回了国,向她报告了——”
“因为我给了他钱。”达特尔小姐对我说。
“正是这样,小姐——向她报告了我所知道的情况。我想不起,”利提摩先生想了一会儿说,“还有别的什么了。我现在已经失业,很想有个体面的事做。”
达特尔小姐朝我看了一眼,好像是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当时我脑子里正好想起一件事,于是便回答说:
“我想问问这——家伙,”我实在没法勉强自己说出更好听的字眼来,“他们是否截留过艾米莉家里写给她的一封信,或者他是否认为她已经收到了那封信。”
他一直保持着镇定和缄默,眼睛盯着地面,右手的每个指尖灵巧地抵着左手的每个指尖。
达特尔小姐轻蔑地把脸转向他。
“对不起,小姐,”他突然从出神中惊醒过来说,“虽然我得听从你的吩咐,可是我也有自己的身份,尽管我只是个仆人。科波菲尔先生跟你,小姐,是不同的。要是科波菲尔先生想要从我这儿打听什么,那恕我冒昧,我要提醒科波菲尔先生,他可以把问题向我好好提出来,我也有人格要维护的啊。”
我好不容易按捺住性子,过了一会,把眼睛转向他,说,“你已经听到我的问题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就把它看成是对你提出的吧。你怎么回答呢?”
“先生,”他时不时灵巧地把指尖分开又抵拢,回答说,“我的回答,得有所保留;因为,把詹姆斯先生的秘密告诉他母亲,这跟对你泄露,完全是两码事。我认为,会让人造成情绪低落和增加不愉快的信,詹姆斯先生大概是不会让她多收的;再多的话,先生,我就希望避而不谈了。”
“要问的全问了吗?”达特尔小姐问我道。
我表示,我没有别的什么要问了。“只是,”我看到他要离开时,补充说,“既然我已知道,在这桩坏事里,这个家伙所扮演的角色,我是一定会把这一情况告诉艾米莉从小就认他做父亲的那位老实人的,所以我要提醒一下这位干坏事的人,公共场所还是少去为好。”
我一开口,他就站住不动了,带着他往常的那种镇静态度听着。
“谢谢你的好意,先生。不过,请你原谅我说的话,先生;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人们是不许不顾法律,私自用武力报复的。要是他们敢那么做,我相信,那不是给别人招灾,而是给自己惹祸。因此,我得说,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先生,我一点也不害怕。”
说完这番话,他恭恭敬敬地对我鞠了一个躬,又对达特尔小姐鞠了一个躬,接着便从冬青围篱中间的一个拱门进去了,他就是从那儿出来的。达特尔小姐和我默默地互相看了一会;她的态度,仍跟把利提摩叫出来时完全一样。
“他还说过,”她慢慢地撅起嘴唇说,“他听说,他的主人正沿着西班牙海岸航行;这次航行完了,他还要去别的地方,去过他那份航海的瘾,直道玩腻了为止。不过,这事你是不会关心的。他们母子两人,都很骄傲,现在。他们之间的裂痕,比以前更深了,已经很少有弥合的希望。因为他们两个,实质上是一样的人;时光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傲慢。这事你也是不会关心的。不过,由此引出了我要说的话。那个你看成天使的魔鬼,我指的是,他从海滩污泥中捡起来的那个小贱人,”——说到这儿,她的一对黑眼睛直盯着我看,她的食指激动地朝上举着——“也许还活着——因为我相信,有些贱东西,一时是死不了的。要是她还活着,那你们一定是想找到这颗无价的明珠,并且把她保护好的。我们也希望那样,使得他不会有机会再次落入她的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我才派人把你请来,让你听听你刚才听到的那些话;对于这样恶劣的一个小贱人,要是想让她吃到苦头,本来我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她脸上的表情变了,我知道我身后有人来了。原来是斯蒂福思太太。她把手伸给我时,神情比以前更冷淡了,态度也比以前更威严了。不过,我也看出,她还记得我曾对她的儿子爱慕过,一直没有磨灭掉这种旧情——这使我颇为感激。她已经大大地变了样;她那原本笔挺的腰板,远不如以前挺了;她那端庄俊秀的脸上,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她的头发也几乎全白了。不过,她一坐在椅子上,依然是一位端庄的美妇人;她那明亮而高傲的目光,我很熟悉,因为在我上学的年月里,它曾是我睡梦中的指路明灯。
“全部情况都告诉科波菲尔先生了吗,罗莎?”
“都告诉了。”
“是听利提摹亲口说的?”
“是的;我把你为什么想要让他知道这些情况的理由,也告诉他了。”“你真是个好女孩。科波菲尔先生,我跟你从前的那个朋友,曾通过几次信,”她转对我说,“但是并没能使他回心转意,来尽一尽孝道,或者尽一尽天职。所以,关于这件事,除了罗莎说的之外,我并没有别的用意。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带到这儿来过的那个正派人宽心(我只替他感到难过——此外没有别的可说了),能让我的儿子不再落入存心害他的那个仇人的圈套,那就好了!”
她挺直身子,坐在那儿,两眼笔直朝前看着,遥望着远方。
“夫人,”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明白。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曲解你的用意的。不过我得说,就是对你也得说,我跟受害的这家人从小就认识,这个女孩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要是你还认为她没有受到残忍的欺骗,现在还肯从你儿子的手中接过哪怕是一杯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她宁愿死上一百次,也不肯那么做的。”
“得啦,罗莎,得啦!”斯蒂福思太太看出罗莎想要插嘴,便说,“没关系,随它去吧。听说你结婚了,先生?”
我回答说,我结婚已经有一些日子了。
“你干得很不错吧?我现在过着清静的生活,听不到什么消息,不过我知道,你已经渐渐有名气了。”
“我只是运气还好罢了,”我说,“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时,给了一些称赞。”
“你母亲已经不在了?”——她用了一种柔和的声音。
“是的。”
“真可惜,”她回答说,“她要是还在的话,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的。再见了!”
她尊严而又冷漠地伸出手来,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我的手中显得很平静,仿佛她的内心也很平静似的。好像她的高傲能使脉搏静止,能为她脸上遮上平静的面纱,她坐在那儿,透过面纱,笔直朝前看着,遥望着远方。
我沿着阳台离开她们时,禁不住朝她们再看了看,只见她们两人坐在那儿,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的景物;暮色越来越浓,渐渐地把她们笼罩。一些亮得早的灯火,星星点点地在远方的城市中闪烁。东面天空中惨淡的霞光还在徘徊。但是,横隔在这儿跟城市之间大片的宽阔低谷里,一片雾霭正像大海似的升起,和暮色混为一体,仿佛汇聚成的一片汪洋,要把她们围困。我永远记得这番情景是有道理的,而且想到这就毛骨悚然,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朝她们多看一眼,那汹涌的海涛,已经翻滚到她们的脚下了。
听到这消息后,经过琢磨,我觉得应该告诉佩格蒂先生。第二天晚上,我就到伦敦市区去找他。他一直抱着寻回他外甥女的唯一目的,在到处寻访。不过在伦敦的时候,比在别的地方要多些。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深更半夜,在街上走过,从那些在这种时刻还在外面游荡的少数人中间,寻找他害怕找到的那个人。
他在亨格福特市场一家小杂货店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这地方我已提到过不止一次。他的寻找行动最初就是从这儿出发的。我就朝那儿走去。到了那儿,我向小店里的人一打听,说他还没有出门,上楼就可以找到他。
他正坐在窗前读着什么;窗台上还养了几盆花草,屋子里收拾得非常整洁。我一眼就看出,这儿时刻都准备着迎接艾米莉的到来;每次外出,他总认为他有可能把她带回来的。我敲门他没有听到,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时,他才抬起头来。
“大卫少爷!谢谢你,少爷!你特意来看我,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你请坐。你来我欢迎极了,少爷!”
“佩格蒂先生,”我说,一面接过他递过来的椅子,“我听到了一点消息。不过你别抱太大的希望!”
“艾米莉的消息!”
他两眼直盯着我,神情紧张地把一只手放到嘴上,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根据这个消息,还没法知道她在哪儿,不过她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
他坐了下来,神情急切地看着我,屏声敛气地听着我告诉他一切。当他慢慢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一只手支着前额,双目下视坐在那儿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那张坚忍庄重的脸上,有着一种尊严,甚至是美感,使我非常感动。他没有插一句嘴,自始至终只是静坐在那儿倾听着。他似乎正凭着我的话在搜寻艾米莉的身影,一切别的形象,他一概放过,仿佛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我说完后,他捂住脸,依然不出一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又看了看那几盆花草。
“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大卫少爷?”后来他终于问道。
“我想,她还活着。”我回答说。
“我不知道。也许这第一棍打得太重了,要是一时想不开——!以前她时常说到蓝色的大海。这么些年来她老是想到大海,难道因为那是她未来的坟墓!”
他一面琢磨,一面惶恐不安地低声嘀咕着;还在小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
“不过,”他又接着说,“大卫少爷,我总觉得她一定还活着——不管我睡着时,还是醒着时,我都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她——一直以来,指引着我,支撑着我的,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决不相信我会受骗。不会!艾米莉一定还活着!”
他坚定地把手往桌子上一放,他那晒黑了的脸上露出果断的神情。
“我的外甥女儿艾米莉,一定还活着,少爷!”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打哪儿听说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听说的,不过我确实听说,她还活着!”
他说这话时,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个受到神灵启示的人似的。我等了一会儿,直到他能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来,然后才对他讲起我昨晚想到的可以采取的稳妥办法。
“你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开始说道。
“谢谢你,谢谢你,好心肠的少爷!”他双手紧握住我的一只手说。
“万一她要是来伦敦,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她想要隐姓埋名的话,哪儿还有比这座大城市更方便的啊。再说,要是她不愿回家,除了隐姓埋名躲起来之外,她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她不会回家,”他插了一句,一面伤心地摇着头,“要是她是自愿离家的,那也许会回来;可实情不是那样,所以她是不会回家了,少爷。”
“万一她要是来到伦敦,”我说,“我相信,这儿有一个人,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更能找到她。你还记得——你要拿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听我说,你得想到你的大目标!——你还记得玛莎吗?”
“我们镇上的那个?”
看他的脸色就够了,我不用再作别的回答。
“你知道她在伦敦吗?”
“我在街上见到过她。”他哆嗦了一下,回答说。
“可是你不知道,”我说,“艾米莉从家里出走以前很久,就用汉姆的钱接挤过她。你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相遇,在路那边的那间屋子里谈话时,她就在门口偷听来着。”
“大卫少爷!”他吃了一惊,回答说,“就是下大雪那天晚上?”
“是的,就是那天晚上。打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她。那晚跟你分手后,我本想回去同她谈谈,可是她已经走了。当时我不愿对你提起她,现在我也还是不愿意。不过她可就是我说的那个人,我想我们应该跟她取得联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太明白了,少爷。”他回答说。这时,我们已经放低了声音,几乎像在窃窃私语了;往下我们就这样低声谈着。
“你说你见到过她。你看你能不能找到她?我自己只能盼望碰巧遇上她了。”
“我想,大卫少爷,我知道上哪儿去找她。”
“天已经黑了。我们既然碰在一块儿了,要不要现在就出去,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找到她?”
他表示同意,准备和我一起去。我没有露出注意他在做什么的样子,只见他仔细地把小房间收拾了一番,把蜡烛和点蜡烛的东西都放好,整理好床铺,最后从抽屉里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些衣服中,取出一件(我记得艾米莉穿过这件衣服),还取出一顶女帽,把它们放在一张椅子上。有关这些衣帽的事,他只字未提,我也一样。毫无疑问,这些衣帽已经在那儿等了她好多好多夜了。
“以前,大卫少爷,”我们下楼时,他说,“我几乎把玛莎这女孩,看成是艾米莉脚下的泥巴。求上帝宽恕我,现在可不一样了!”
当我们一路走去时,我向他问起了汉姆的情况,这一方面是为了找话跟他谈,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佩格蒂先生的说法,几乎跟以前一样,他说,汉姆一切照旧,还是“拼命干活,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大伙都喜欢他”。
我问他,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罪魁祸首,汉姆的心里有些什么想法?他是不是认为会有出事的危险?比方说,要是汉姆跟斯蒂福思遇上了,他认为汉姆会怎么做?
“我说不上来,少爷,”他回答说,“我常常想到这件事,可是不管我怎么想,我都没能想出什么来。”
我提醒他,叫他回想一下艾米莉出走后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在海滩上的情景。“你可记得,”我说道,“他望着远处的大海,脸上有着一种异常的神情,还讲到‘结局’什么的?”
“我当然记得!”他说。
“你想,他是什么意思?”
“大卫少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一直找不到答案。还有一件怪事——那就是,尽管他那么讨人喜欢,可是要想摸透他的心思却不易,这事我心里挺不放心。他对我说话,一向要多恭敬有多恭敬,现在也没有两样。不过他心里可绝不是浅水一滩,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儿深着哩,少爷,我看不到底啊!”
“你说得对,”我说,“这事有时让我担心。”
“我也一样,大卫少爷,”他回答说,“说实话,他这样,比他不顾死活更让人担心哩,虽说这两点都是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知道他都不会动武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两人别碰在一起。”
我们穿过圣堂栅栏门,来到城内。现在他已不再讲话,在我旁边走着,把自己的全副精神,都倾注在为之献身的唯一目标上;他朝前走着,默不作声地集中起全身的所有官能,从而使得他在人群中也显得旁若无人,孑然一身。当我们走到离黑衣教士桥不远处时,他突然转过头来,指着街对面一个匆匆走过的独行女子。我立即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穿过街道朝她追去。这时我忽然想到,要是我们离开人群,在一个较为僻静、没有什么人看到的地方,跟她交谈,她也许会对我们这个迷途的姑娘,多一点女人的关切。所以我就劝我的同伴,暂且别招呼她,先跟着她走。我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模糊的想法,想知道她去什么地方。
佩格蒂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就远远跟着她。既不让她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决不走得离她太近,因为她时时都在朝四下里张望。有一次,她停下来听一个乐队演奏,我们也停了下来。
她往前走了很远,我们依然跟着。看她那走路的样子,显然她要去一个固定的地点。由于这一点,加上她一直没有离开喧闹的大街,大概还有像这样跟踪一个人的特殊神秘趣味,使得我们一直坚持着最初的主张。到后来,她终于拐进了一条冷僻昏暗的街道,这儿,喧闹声和人群都听不见、看不到了。这时,我说,“现在我们可以跟她说话了。”于是我们就加快脚步,朝她赶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