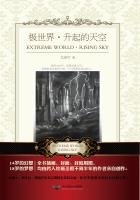独自占有一座高高的城堡,把外面的那道门一关,就像鲁滨孙进入自己的堡垒后把梯子扯起一样,实在是件十分舒心的事。口袋里放着自己房间的钥匙,在城里四处闲游,知道可以邀任何人来家做客,相信只要对自己没有什么不便,就决不会对别人有什么不便,这是件了不起的美事。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完全由着自己,用不着跟任何人关照一声,有事时把铃一拉,克拉普太太就得气喘吁吁从地底下上来——当她愿意上来时——这也是件很愉快的事。所有这一切,我说,都是舒心愉快的美事,不过我也得说,也有非常寂寞无聊的时候。
在早晨,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白天,我自由自在,生活很新鲜。在灿烂的阳光下,生活则更加新鲜,更加自由自在。可是一到太阳西沉,这种生活似乎也就随之消沉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烛光之下很少有美好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很想有人跟我谈谈话。我想念爱格妮斯。没有那个微笑着倾听我心声的人儿在场,我感到眼前一片可怕的空虚。克拉普太太则离我似乎有千里之遥。我想起了前面那个死于烟酒的房客,真希望他活得好好的,不要用死来惹得我孤寂烦恼。
才过了两天两夜,我却觉得好像已经在那儿住了整整一年了。我未见有什么成长,仍和往常一样,为自己的年轻幼稚而苦恼。
斯蒂福思仍未露面,我担心他一定病了。第三天,我就提前离开博士公堂,徒步前往海盖特。斯蒂福思太太见了我很高兴,她告诉我说,她儿子跟一个牛津的同学一起,去看另一个住在圣奥尔本斯附近的同学去了,不过她估计他明天就能回来。我实在太喜欢斯蒂福思了,我觉得,我都妒忌起他那两位牛津同学来了。
斯蒂福思太太硬要留我在她家吃晚饭,我也就遵命留下了。我相信,那一天我们没谈别的,净谈斯蒂福思的事。我告诉她说,亚茅斯的人有多喜欢他,他是个多么令人愉快的伙伴。达特尔小姐作了许多委婉的暗示,还提了不少诡秘的问题,对我们在那儿的活动很感兴趣,老是问,“可这是真的吗?”这话说了多次,把她想知道的事,全从我嘴里给套出来了。她的外表,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所描绘的完全一样。可是跟这两位女人相处,是如此令人愉快,使我感到非常舒畅自然,我却觉得有点爱上她了。那天整个晚上,特别是在夜间走回寓所时,我禁不住几次提到,要是她能在白金汉街和我做伴,那该多美好啊。
早上,在去博士公堂前,我正在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卷时——我不妨在这儿顺便提一句,克拉普太太放的咖啡那么多,可那咖啡却那么淡,想想真让人觉得奇怪——斯蒂福思突然走进我的房间,这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亲爱的斯蒂福思,”我喊着说,“我开始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啊!”
“我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斯蒂福思说,“就让人给硬拉走了。嘿,雏菊,你在这儿是个多么少见的老光棍啊!”
我极为得意地带他看了我的这套房间,连那间食具间也没漏掉。他看了后大加称赞。“我告诉你吧,小老弟,”他补充了一句,“我要把这儿当成我在城里的下榻处,除非你对我下逐客令。”
我听了这话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对他说,要是他等我下逐客令,那可得等到世界末日哩。
“不过你得先吃点早饭!”我说着,把手放在拉铃的绳子上。“克拉普太太会给你新煮点咖啡,我给你在这儿的光棍用的荷兰烤炉上烤点咸肉。”
“不,不!”斯蒂福思说,“别拉铃!我不能在这儿吃!我要去跟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一起吃早饭,他住在科文特加登的皮阿艾旅馆。”
“那你会回来吃晚饭吧?”我说。
“不成,我说的是实话。能来你这儿吃晚饭,我真是再高兴也没有了。不过我得跟他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三个明天一早就要一块儿上路。”
“那就把他们两个也带来这儿吃晚饭吧,”我回答说,“你想他们会来吗?”
“哦!他们跑着来还来不及哩,”斯蒂福思说,“不过这会给你添麻烦。你最好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哪个饭馆吃一顿吧。”
我怎么也不能同意他这个建议,因为我本来就想到,我一定得搞一次小小的乔迁宴会,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这套房间经斯蒂福思一称赞,我更引以为荣了,极想把它的效能大大发挥一下。因此我硬逼他全权代表他那两位朋友,保证答应前来赴宴,我们把宴会的时间约定在六点钟。
斯蒂福思走后,我拉铃叫来了克拉普太太,把我这不顾一切的计划告诉了她。克拉普太太说,第一,不能指望她亲自来伺候,这一点大家当然都很清楚,不过她认识一个伶俐的小伙子,她想她能够劝说他前来干这个活,酬劳大约五先令就行,小费可以随意。我说,我们当然要用他。其次,克拉普太太说,她一个人不能同时分身在两个地方,这是很明显的(我也认为这很有道理),所以食具间里少不了得有个“小丫头”,给她点上一支卧室用的蜡烛,让她在那儿不停地洗碗洗盘子。我问用这么个年轻姑娘得花多少钱,克拉普太太说,她料想,十八个便士既不会让我富起来,也不会使我穷下去。我说,我也认为不至于那样,于是这件事也就这样说定了。克拉普太太接着说,现在再说说晚宴的菜吧。
给克拉普太太打造厨房炉灶的铁匠,实在缺乏远见,明显的例子是,她的这个炉灶,除了能烧排骨和土豆泥外,什么菜都不能做。至于说到煎鱼锅,克拉普太太说,行啦!你是不是只消去厨房看一下就明白了?她不能说得比这更清楚了。我是不是去厨房看一下?我即使去看了,也不见得能明白多少,所以我就推辞了,同时说,“那就不要海味了吧?”可是克拉普太太却说,别这么说,这会儿牡蛎正当令,为什么不来道牡蛎呢?于是这道菜也就定下来了。接着,克拉普太太说,她的建议是这样:两只热烤鸡——从食品店里买,一盘炖牛肉,外加蔬菜——从食品店里买,两只小配碟,如一只发面馅饼,一碟腰子——从食品店里买,一道水果馅饼,再加一道果子冻(如果我喜欢的话)——从食品店里买。这样,克拉普太太说,她就可以不受牵制,把精力全都集中在土豆上,以及她但愿能做好端上桌面的干酪和芹菜上了。
我就按照克拉普太太的意见办理,亲自到食品店订购了各种菜肴和点心。过后从斯特兰德大街经过时,我看到一家火腿牛肉铺的柜窗里,摆有一种坚硬的、上面有斑点的东西,看上去像大理石,而标签上标的是“仿海龟”,我就进去买了一大块,我一直以来有理由相信,那块东西本来是够十五个人吃的。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克拉普太太,把它热一热,可是等端上来时,全化成了汤,竟缩得这样厉害。我们发现,正像斯蒂福思说的,四个人吃都“相当紧张”了。
各种菜点总算准备齐全,我又在科文特加登的市场上买了点水果甜点,还在附近的酒类零售店里订购了不少酒。当我下午回寓所时,看到食具间的地上,酒瓶摆成了方阵,竟有这么多酒(虽然还少了两瓶,把克拉普太太弄得很不好意思),简直都把我吓了一大跳。
斯蒂福思的朋友,一个叫格兰杰,一个叫马卡姆。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欢快、活泼的小伙子。格兰杰比斯蒂福思稍微大一点,马卡姆看上去很年轻,我看还没过二十。我发现,马卡姆说到自己时,总是用不定式“一个人”,很少或从来不用第一人称单数。
“一个人在这儿,可以过得很好,科波菲尔先生,”马卡姆说——他这是指他自己。
“这儿环境不错,”我说,“房间还真宽敞方便。”
“我希望你们两位把胃口都带来了。”斯蒂福思说。
“说实话,”马卡姆说,“伦敦这地方让一个人胃口大开。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觉得饿。一个人得一直不断地吃东西。”
一开始,我感到有点尴尬,觉得自己太年轻,做不了主人,所以晚餐开始时,我硬要斯蒂福思坐在主人位子上,我则坐在他对面。一切都很好,我们都敞开喝酒;斯蒂福思当主人当得好极了,他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使得席上的一切无不尽善尽美,欢乐的笑声一刻也没有间断。但是在整个晚宴中,我自己并没有尽到我希望尽到的东道之谊,因为我的座位正对着门,我的注意力常常被那个伶俐的小家伙吸引,他老是溜出房间,随后他的影子便映在门口的墙上,嘴巴对着酒瓶。那个“小丫头”也弄得我坐立不安,倒不是她不尽本分,没洗盘子,而是她老是敲破盘子。原因是她生性好奇,不肯待在食具间里(像事先吩咐她的那样),不断地朝我们的房里张望,但又怕被我们发现,有好几次她吓得往回缩时,都踩到了她自己仔细地摆在地上的盘子上,踩坏了不少。
不过这些都是小小的憾事,当桌布撤去,摆上甜点水果时,这些事很快就忘了。到了这时,我发现那个伶俐的小伙子,已经舌头僵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悄悄对他说,要他去找克拉普太太,同时把那位“小丫头”也打发到地下室去,这样我自己就可以尽情享乐了。
我开始觉得愈来愈高兴,心情变得越来越轻松。各种各样大半忘记的可谈之事,全都涌上我的心头,使我的话不同寻常地滔滔不绝。听了自己的笑话和别人的笑话,我都纵情大笑。由于斯蒂福思不肯把酒递过来,我对他大声发出警告。我说了不止一次,要跟他们一起去牛津,还当众宣布,打算每周都来一次这样的宴会,如有变更,另行通知。我发疯似的从格兰杰的鼻烟盒里吸了那么多鼻烟,结果不得不跑进食具间,偷偷打了十分钟的喷嚏。
我继续这样胡闹着,酒递得愈来愈快,没等一瓶酒喝完,就又拿起瓶塞钻打开另一瓶。我提议为斯蒂福思的健康干杯,说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童年时代的保护人,壮年时代的伴侣。我说,能为他的健康干杯,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还说,我欠他的情,永远也还不清,我对他的敬佩,永远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我提议为斯蒂福思干杯!愿上帝保佑他!万岁!”我们敬了他三次三连杯,后来又来了一次三连杯,最后又干了一大杯作为结束。我绕过桌子去跟他握手时,打破了我的酒杯,我一口气对他说,“斯蒂福思,你是我一生的指路明星。”
我说着,说着,突然发现有个人在唱歌,正唱到一只歌的中间。唱歌的是马卡姆。他唱道,“当一个男人心情烦恼苦闷时,”唱完后他提议为“女人!”干杯。我反对他的提议,不许他这样做。我说,这样干杯不恭敬,在我家里决不允许这样干杯,要是说“夫人”“小姐”,那就当别论了。我对他火气很大,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斯蒂福思和格兰杰在笑我——或者是笑他——要不就是在笑我们两个人。他说,一个人不能听别人的指使,我说,一个人得听别人的指使。他又说,一个人决不能受别人的侮辱,我说,他这话倒说对了——在我家里,绝不会有这种事,这里的家庭守护神是神圣的,敬客的礼数在这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说,承认我是个极好的人,并不损害一个人的尊严。我听了这话,马上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有人吸烟。我们就全都吸烟。我也吸起烟来,同时使劲忍住想要颤抖的感觉。斯蒂福思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演说,我听着听着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我对他作了答谢,同时希望在场的几位朋友,明天、后天都再来跟我一起吃晚饭——每天五点钟开始——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一长夜相聚、交谈的乐趣。我觉得我应该提出一个人来为之干杯。我对他们提出了我姨婆,于是我们为女性中的杰出人物,贝特西·特洛伍德小姐干杯!
有个人从我卧室的窗口探身出去,把前额贴在阳台冰冷的石栏杆上,一面感受拂在脸上的微风。这个人就是我。我对自己叫了一声“科波菲尔”,并且说,“你为什么要学抽烟啊?你原本就该知道,你是不会抽烟的呀。”这时,有个人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照镜子。这个人也是我。镜子里的我,面色煞白,两眼失神,头发——只有我的头发,没有别的——看起来喝醉的样子。
有个人跟我说,“我们去看戏吧,科波菲尔!”我眼前没有了卧室,只有上面杯盘狼藉的桌子,还有灯。格兰杰在我右边,马卡姆在我左边,斯蒂福思在我对面——我们全都坐在雾中,而且相隔得很远。看戏去?好极了,是该看戏去。走啊!不过我要看着大家先出去,他们得让我最后一个走,我得把灯熄掉——以防火灾。
由于在黑暗中有点慌乱,门不见了。我一直在窗帘那儿摸索,想找到门。斯蒂福思笑着搀起我的胳臂,把我领出门外。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楼。快到底下时,有个人跌倒了,滚下了楼梯。另外有个人说,跌倒的是科波菲尔。我听了这句胡说八道的话,大为恼火。后来我发现自己仰卧在过道里,才想到,这句话也许有点根据。
那天晚上雾很大,街上的路灯都有个大圈圈!有人含含糊糊地说,下雨了。我却认为这是霜气。斯蒂福思在路灯柱子下给我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我的帽子整理好。这顶帽子,不知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又瘪又皱的已经完全不成样子,而我原来是没有戴帽子的。这时,斯蒂福思说,“你没事吧,科波菲尔?怎么样?”我对他说,“再熬(好)也没有了。”
有个人,坐在一个鸽子笼似的窗洞里面,朝外面的雾气中看着,他不知从什么人的手里接过钱,问我是不是跟付钱的先生是一起的。他显得有点犹豫的样子(我瞥了他一眼时看出),是不是要收下给我买票的钱。一会儿工夫,我们来到热气腾腾的戏院里一个很高的地方,朝下看有个大坑,我觉得坑里好像正在冒烟。坑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一点也看不清楚。还有一个大舞台,比起刚才见到的街道来,干净光滑多了。台上有人,正在说着什么,可是一点也听不懂。有很多明亮的灯,有音乐,下面的包厢里还有女客,此外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整个房间好像都在学游泳,我想要它稳住时,它却作出那样莫名其妙的样子。
按照不知是什么人的提议,我们决定转移到楼下有女客的礼服包厢。一个身穿大礼服的绅士,伸腿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具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从我眼前移动而过,移动而过的还有我自己在镜子里的整个身影。接着有人把我领进一个包厢。我就坐的时候,听到自己说了一句什么,我四周的人就对着一个人喊“安静”!女客们都愤愤地看着我——还有——哎呀!没错!——爱格妮斯,也坐在这个包厢里,就坐在我前面的位子上,身旁有一位女士和一位绅士,我都不认识。现在我又看到她的脸了,我敢说,比当时看到的还清楚。她掉过头来看着我,带着令人难忘的痛心和惊诧。
“爱格妮斯!”我口齿含糊地叫她,“哎呀呀!爱格妮斯!”
“别嚷嚷!我求你了,”她回答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让我叫她,“你打扰了别人啦。看台上吧!”
听了她的话,我尽量想把目光盯在台上,想听一听台上都在说些什么,可是白费力气,渐渐地我又朝她看,发现她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还用戴着手套的手按着前额。
“爱格妮斯!”我说道,“我怕你不太苏(舒)服呢。”
“没事,没事,你别管我,特洛伍德,”她回答说,“听我说!你一会儿就走吗?”
“我一贵(会儿)就斗(走)吗?”我重复了一遍。
“是啊。”
我有一个愚蠢的念头,想回答她说,我要等在这儿,送她下楼。我现在想,当时我不知怎么的总算把这表达出来了,因为她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后,好像明白了,然后低声对我说:
“要是我对你说,我这话是非常认真的,我知道,你是会听我的话的。现在就走吧,特洛伍德,看在我的分上,请你的朋友送你回家吧。”
她的话使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因为这时我虽然生她的气,但是心里觉得很羞愧。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再淹”(我的意思是说“再见”),就站起身来走了。他们跟在我的后面。我一脚跨出包厢的门,便进了我的卧室。这时只有斯蒂福思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了,他帮我脱了衣服。我告诉他说,爱格妮斯是我的妹妹,并且恳求他把瓶塞钻拿给我,我好再开一瓶酒。
有个人躺在我的床上,一整夜做着乱七八糟的梦,这些梦反反复复做着,说着互相矛盾的话,做着互相矛盾的事——那张床则成了波涛起伏的海洋,永无静止!那个人,慢慢地变成了我。我开始感到干渴,我浑身上下的皮肤,好像都成了硬邦邦的木板,我的舌头像用久生垢的空水壶壶底,像在慢火上烤干似的;我的手掌像灼热的铁板,冰也没法使它冷却!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清醒过来之后,我在思想上感到多么痛苦,多么后悔,多么羞愧!我犯了上千种我已记不清的过失,而且再也无法补赎了——我想起了爱格妮斯朝我看时那令人永远难忘的神情——没法跟她联系,使我痛苦不堪。我真像个畜生,不知道她怎么来到伦敦,也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这间行乐欢宴房间里的景象,看了让我作呕——我的脑袋疼得要裂开似的——难闻的烟味,狼藉的杯盘;不要说出不了门,就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唉,那是怎样的一天啊!
唉,那天晚上,那是一个怎样的晚上啊!我坐在火炉旁,面前放着一盆浮满油星的羊肉汤。我心里思忖,我就要重蹈前一个房客的覆辙了,不但接住他的房间,还要承袭他悲惨的身世了,我真想立即前往多佛,坦露这一切!那是一个怎样的晚上啊!当克拉普太太来撤掉汤盆,端上一个用干酪碟子盛着的腰子,说这是昨晚宴会剩下的唯一东西时,我真想要伏在她穿着紫花布上衣的胸口,怀着衷心的悔意,对她说,“哦,克拉普太太,克拉普太太,别管什么剩下的东西了,我心里难过极了!”——不过,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怀疑,克拉普太太是不是那种可以对之推心置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