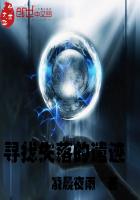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而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个新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1901年成立)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就经济方面来说,即使是一半的奖金,其数额也是很大的。这之后,皮埃尔在物理和化学学校里的教学任务便由保尔·朗之万替代了。朗之万是皮埃尔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物理学家[保尔·朗之万写过两篇关于皮埃尔的生活与事业的长文,一篇登在《物理和化学学校校友联谊会年鉴》上(1904年),另一篇登在《当月》杂志上(1906年)。——原注]。皮埃尔还聘请了一位教辅人员,帮助他搞实验研究。
然而,这幸福的大事由于媒体的宣扬立即让我们不堪重负,因为我们既不习惯又无此心理准备。每天来访者不断,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又是约稿,又是邀请作报告,应接不暇,浪费了时间,又弄得人困马乏。皮埃尔又是一个和蔼的人,不喜欢一口回绝别人的请求,但是他也很清楚,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不光他的身体吃不消,而且头脑的清醒、研究的思绪全都被搅和了。他在写给纪尧姆的一封信中说:“他们一个劲儿地要我写文章,要我作报告,如果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即使那些请我写文章作报告的人也将惊讶地看到我竟然年华虚度,什么也没有干。”
在这同一时期,他在写给古伊的几封信里也发出了这种哀叹;古伊把这些信转交给了我,对此,我应向古伊表示诚挚的感谢:
如您所见,此刻幸运眷顾了我们,但是,这幸福的来临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我们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得安宁。有些天,我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可我们都是曾经梦想着远离人群,在荒郊野外生活的呀。
1902年3月20日
亲爱的朋友,我早就想要给您写信了。请您原谅我(吕特福最近利用α射线的内在能量把某些原子击碎,例如氮原子。——作者注)这么拖拖拉拉的。可您要知道我此刻过的是多么荒唐愚蠢的日子,您就不会责怪我了。
您已经看到了,现在镭成了热门话题。这使我们一时间获得种种好运,声名鹊起,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摄影师到处跟着我们,他们甚至把我女儿同保姆的谈话都当作新闻来炒作,连我们家的黑白花猫也成为新闻明星了,此外,还有不少人请我们捐款。索要签名者、势利者、上等人,有时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家也都找上门来,弄得我们洛蒙街的家也不像个家了。
而且,在实验室里也没法安心地工作。每天晚上还得回复大量的信。我真是不胜其烦,整天昏昏沉沉的。要是这么一番闹腾,让我获得大学的一个教席和一间实验室,那还算说得过去。可说实在的,教席之事尚在计划之中,而实验室一时半会儿也还是个没影儿的事。我倒是宁愿先有实验室,但里亚德院长却认为应趁这个热乎劲儿先建立一门新课程,而且先列出明确大纲,与法兰西学院的某一门课相似。这样一来,我年年都得编教材,那就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
1904年1月22日
我不得不放弃瑞典之行。您都看到了,我们已完全违反了瑞典科学院的规定。说实在的,我的身体实在太差了,稍稍多累一点都受不了。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同我一样。我想都不敢想过去进行研究工作时那些繁忙的日子。
说到研究工作,我现在什么也没做。每天讲课,指导学生,安装仪器设备,应付找上门来却又没什么要紧事的人,弄得我虚度日月,没干成一点有用的事情。
1905年1月31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非常遗憾您今年没能前来我们家,但愿10月能见到您。一个人如果不时常见一见最要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最后就会失去他了,只好去见其他一些不相干的人,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容易见到。
我们仍旧是忙忙碌碌,但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搞研究了,可我也没有一刻半会儿是属于自己的。很明显,我尚未找到防止我们的时间给弄得支离破碎的办法,可我们必须找到它。从理性上来看,这可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05年7月24日
我要讲授的课程明天正式开始,可实验室尚未充分准备好,所以心里挺不痛快的。上课的地方在巴黎大学院内,可实验室却在居维埃街。另外,还有几门其他课程也在同一课堂上,只有一个上午的课,我可以利用这间教室好好地备备课。
虽然尚未卧床不起,但健康状况却不很好,老觉得浑身无力,连实验研究也搞不了。我妻子则不一样,她倒是活蹦乱跳的。除了照顾两个女儿之外,她还得跑到塞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去教课,另外,还要到实验室做实验,真够她忙的。她每天有大半天的时间在实验室里指导实验和自己做实验,比我强得多。
1905年11月7日
总的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外界干扰,但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仍同以往一样简简单单、离群索居。1904年年末,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成员,二女儿艾娃·德尼斯在我们的克勒尔曼大街的寓所里诞生了。皮埃尔的父亲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来往的朋友也不多。
大女儿在长大,开始成为她父亲的一个小伙伴。皮埃尔也很关心对她的培养教育,而且一有空闲总要带着她去散步,特别是在假日里。他常常跟她正儿八经地交谈,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很高兴她的小脑袋瓜越来越开窍。
随着皮埃尔在国外的声望越来越高,法国人民对他的崇敬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是到来了。四十五岁时,他名列法国科学家的前茅,然而,在教学岗位上,他的地位仍然很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引起公众的哗然。趁着舆论的这股力量,巴黎科学院院长里亚德提出在巴黎大学创建一个新的教席。在1904至1905学年间,皮埃尔被授予巴黎大学理学院的正教授头衔。一年后,他正式离开了物理和化学学校,由保尔·朗之万接替了他的位置。
巴黎大学新设的教席开始时困难不小。开始的计划是只设讲座而无实验室。皮埃尔认为接受了这个新职位就有可能失去现在他所使用的聊胜于无的实验室,而又不可能有新的实验室给他,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他便给上级写信,决定不接受新职,仍留在P.C.N. 教师职位上,由于他的态度坚决,他获得了成功。巴黎大学除创立了一个新教席以外,还给他划拨了经费,以创建实验室和聘请人员。实验室的编制是一名主任、一名助教和一名实验室杂役。实验室主任由我担任,皮埃尔对这个安排也颇为满意。
我们在物理和化学学校尽管条件艰难,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起做科学实验的幸福日子,现在一旦离开,不免有一种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那间木棚实验室尤其让我们割舍不下。这座木棚又存在了几年,但日益破败不堪,我们有时还去看一看它。后来,为了修建物理和化学学校的新校舍,不得不把它给拆掉,不过我们还是留了几张它的照片。在它被拆毁的那一天,忠实的佩蒂通知了我。唉!我独自一人跑去凭吊了它。黑板上,曾经是这个实验室的灵魂的那个人的笔迹仍留在上面,角角落落都留有他的印迹,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
往事如烟,恍如南柯一梦,我真想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想再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尽管大学委员会通过了创办新讲座的决议,但是并没有考虑同时创建一个实验室,而实验室却是进一步研究放射性这个新的科学发现所不可或缺的。皮埃尔仍旧留着P.C.N. 的那个小实验室,并且还借用了学校里的一个独立的大教室,又在院子里搭建了两个房间的小屋和一个工作间。
一想到这是法国对皮埃尔的最后的照顾,不免让人唏嘘。一个二十岁便崭露才华的法国一流科学家却连一个可供其进行实验研究的好实验室都没有,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他迟早会拥有自己满意的工作条件的,但是,他英年早逝,到了四十七岁时,却仍然未能如愿,这难道不让人痛心疾首吗?一个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因为条件所限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科学梦,岂不令他抱憾终生吗?国家的巨大财富——它的优秀的孩子的才华、毅力和勇气——就这么无可挽回地浪费掉了,让人回想起来好不痛心!
皮埃尔脑子里一直想着能拥有一座好实验室。1903年,当他声名大噪,他的领导们迫于压力,要求他接受荣誉骑士团勋章时,他坚持己见,婉言谢绝了,他像上次写信给物理和化学学校校长谢绝教育棕榈奖章一样,写信谢绝了荣誉骑士团勋章,其态度始终一成未变。我把他这封信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请代为向部长表示谢意,并请转告部长先生,我不需要任何的奖赏,只求能给我一个我所急需的实验室。
皮埃尔被聘作巴黎大学教授之后,需要准备开一门新课。讲课内容由他自己确定,范围很广,他有充分自由对教材进行选择。他利用这一良机回到了自己所喜爱的课题上来,把一部分教材内容选定为对称性定律、矢量和张量场研究,并把这些概念运用到晶体物理学中。他想充实自己的讲课内容,使他的这门课能够成为晶体物理学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因为在法国这一课题尚乏人问津,所以更为有用。除此以外,他还讲授放射性,并阐述在这一新领域里的科学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带来的科学革命。
他备课十分繁忙,加之身体欠佳,可他仍旧继续在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室的组织管理在日益好转。由于地方扩大了点,他可以接收几个学生一起研究。他与拉波尔德合作,研究矿泉水以及泉水中释放的气体的放射性,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份研究报告。
此时,他的才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非常钦佩他对物理学理论的见解之深邃和精辟,以及他演绎之中肯和对基本原理理解之透彻。在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进行观察时,他天生地具有超凡的能力,再加上他毕生在从事实验研究,导致他有着令人叹服的独到见解。他像艺术家似的对待他试制的精密仪器,乐此不疲,欣赏有加。我有时因此取笑他,说他半年不弄出个新仪器就心痒难耐。他天性好奇而又富有想象力,这使得他能够同时涉足不同的领域,改变研究课题时得心应手,其他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要发表研究报告时,他极其诚实、严谨、一丝不苟。他的研究报告即使十分完美,他仍旧要以审视的目光改来改去,字斟句酌,对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必须弄得无可挑剔才能罢手。下面是他在这一点上的说法:
在对未知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先作一些一般的假设,然后根据实验去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这种按部就班的和稳妥可靠的办法当然是效果缓慢的。相反,我们也可以作出一些大胆的假设,先确定现象的机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设想某些实验,特别是可以有利于推论,使之通过一种图像变得不那么抽象。反之,通过实验结果来寻找一个复杂理论,那是很难想象的。精确的假设虽然有着一部分真理,但必然又存在着一部分错误。而这一部分真理即使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一般性见解的一部分,有一天还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
尽管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些假设,但在证实无误之前他是绝不会提前发表的。他讨厌仓促地发表研究报告,喜欢找很少的几位研究人员先平心静气地讨论讨论再说。当放射性研究处于高潮时,他却想到要暂时放一放这一方面的研究,重新拾起他中断了的晶体物理学的研究。另外,他还想要对一些不同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皮埃尔讲课时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他认为无论是对课程的一般标准的要求还是讲课的方法,都应该以与实验和大自然的接触作为基础。当学院教授委员会成立时,他想让同仁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发表声明:“科学教育应该是男中和女中的主修课程。”但是,他又说:“这么一个动议是不会获得通过的。”
这是皮埃尔生命中的一段大出成果的时期,可惜接近了尾声。正当他可以期盼今后的工作年月不再会像先前那么举步维艰时,他的辉煌的科学生涯却戛然而止。
1906年,皮埃尔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不适,于是我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前往什弗勒兹山谷过复活节假期。这是美妙温馨的两天假期,太阳暖融融的,加之在亲人们的身边休憩,皮埃尔心情放松、舒畅,他领着两个女儿在草地上戏耍,与我谈论着当前与未来。
回到巴黎,他前去参加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和晚餐会。席间,他坐在亨利·普安卡雷身边,同他就教学方法谈了很久。当我们徒步回家时,他仍旧在继续大谈他理想中的文化,我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他显得很高兴。
第二天,1906年4月19日,他参加了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他同教授们诚恳地交谈了委员会应采取的方针。开完会出来,他正穿过多菲纳街,从新桥方向驶来一辆运货马车,把他撞倒在地,车轮从他头上碾过,脑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个卓越的人就这么逝去了,人们寄存在他身上的科学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在他的书房里,他从乡间采摘回来的水毛茛依然鲜艳,主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节### 民族的悲痛 成为圣地的实验室